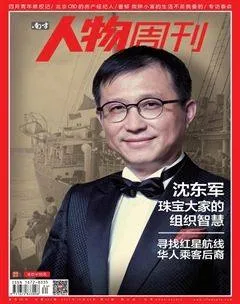城镇化大跃进




在中国广袤的农村,生活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年代久远的村庄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农村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被改造的除了土地之外,还有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命运。
未来的十余年内,预计将有超过两亿中国农民移居到新建的城镇中。政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耕地建设,高楼大厦取代了小户农家,快速城镇化的过程可能会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但也可能引起漫长的后遗症。
如今,建筑狂潮席卷了诸如重庆、山东聊城等城市。雨后春笋般的高层建筑包围了聊城,这座文化古都逐渐变成华北平原小麦种植户的聚集地。在那些超过二十层的楼宇里,居住着失去了土地的农民。

新的生活令人眩目——他们获得了免费的住房、高额的征地补偿金,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笔钱用完后他们将何去何从。那些进城工作的年轻人,每个月能拿到约1200元的最低保障工资,得以维持生计;但还有很多人,终日在桌球吧和电子游戏厅消磨青春。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迁徙运动中,政府大举投资,兴修道路、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教育、医疗和新市民的退休金。诚然,许多人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失业等社会问题依然严峻。
河北省43岁的田伟(音)原来是小麦种植户,他如今在一间工厂担任夜间保管员。他坦言,城市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世界”,“我这辈子都在地里干活,教育水平哪里赶得上城里人?”
新城镇无法为昔日的农民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工厂的雇主们想要的是年轻的员工,让不少45-50岁的新城镇居民难以适从。
“对于我们这样的老年人,没有能做的事情了,”陕西安康市45岁农民何世芳(音)说。“在山里,我们一直在劳动,养猪养鸡。而在这里,我们无所事事,人们只能打麻将。”
那些放弃了土地的农民,再回到家乡已然没有了可耕种的田地,也意味着失去了收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在国家养老金计划内,这无疑加重了亲人的赡养负担。
为了解决城镇化中的诸多问题,政府的方案是固定地向农民提供收入,结果有好有坏。在成都南部的双流县,农民将土地出让给国企用来建草莓实验园,不仅能获得分红,还可能得到工作机会。但在成都市郊,农民土地被征用于修建道路,没有合理的回报。
绝大多数农民尚未并不能体会政府加速推动城镇化的深意——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原始动机是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从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内需为基础的增长模式。
他们所能感知的,是从村庄搬进了高楼,告别了赖以生存的田地和劳动方式。他们开始购买食物,在城市工作和消费。农民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的破裂,被寄予刺激中国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厚望。
当农村城镇化不可逆转地到来,有的人对新的生活感到惶恐,因为征地补偿金不足以维持长久的生计,而自己本身并无一技之长,难以在城市中谋得生路。另一些人却开始享受离开农田之后的新生活——城市里有新的社交环境和新的工作,可能意味着更艰辛的劳动,以及更体面的收入。
中国社科院的2013年《投资蓝皮书》指出,未来20年是中国城乡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届时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
7月30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指出,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仅为42.2%。到2030年,全国大约有3.9亿农村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约1.9亿,增量达两亿多。据测算,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达到13.1万元,要解决3.9亿人的市民化问题,政府公共成本需要支出约51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