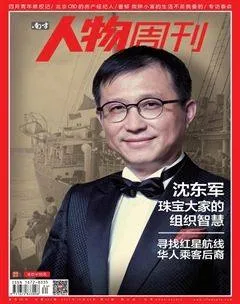来信
逝去的,失去的
这期封面做得很软,抒情多于针砭,怀旧多于前瞻,字里行间或多或少,让我们提前感到深秋的萧瑟,那一股来自蒙古高原的凛冽寒风,此时此刻正穿行在老北京所剩无几的胡同中。
卷首语说:当这座城市坚固的记忆随着推土机的轰鸣消散,那些活着的历史也在慢慢消逝。
坚固的记忆和活着的历史慢慢消逝,但天空的雾霾厚厚的,很多时候,天安门城楼只剩下模糊的轮廓。
还以为会有华新民大声的呼吁,却不料连这一点余地和空间也如此吝惜,原本应探究的广场文化,更是惜墨如金。
即使是二环内的老北京,能留给人们的记忆也所剩无几。
三朝都城之后,共和国首善之区,逝去的,失去的,不可复制,难以复原。
逝去的,失去的,唯有叹息。
《恋恋老北京》
十几年前,就住鼓楼大街,骑车下班总是带本书在后海边坐会儿,没人,安静,清凉,还有胡同口大爷5毛的肉串和一块二的啤酒。后来看着河沿老房子拆掉,看着一圈说不上新旧的泥瓦新房建起,安静的后海就慢慢被糟蹋成尿盆了。
刚在飞机上看这期,非常有感觉,北京胡同的消失和广州小街小巷骑楼的变迁很类似,面对传统和发展冲突的心态尤为传神。希望观者不要简单符号化为拆迁、城管、政府无能等硬邦邦的标签,里面可以回味和思考的很多。
这文章写得着实好!让我想到了很多,让我明白我为什么那么爱看《王府井》、《卤煮》、《离婚》这样的京味话剧,因为我只能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寻回旧日的北京魂,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看戏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心中不断重复一句话“怎么全都变了呢”?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想要离开,这里不再是我家。
“文革”的时候北京的六千多处古迹就被破坏了四千多处,故宫都是周总理保下来的,如果这几十年不那么急功近利,北京真的会是个很有味道的城市呢,现在只能意淫一下咯,没见过清纯小女孩的见了大俗丫头也觉得还不错哇。
《宗庆后 富豪不安全》
区区一个闲汉,就对一位巨富产生如此大的人身威胁,这个问题,让人困扰啊。看完稿子,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富豪不安全,像宗庆后都被砍了。但其实,富豪又很安全,毕竟像宗庆后被砍这种恶性事件,发生几率极低。像曾成杰这种情况,就真的是“不安全”。中国人仇富么?这个问题不重要。宗庆后女儿宗馥莉说过,如果为富施仁,这个社会就没有那么多仇富现象。就富人本身而言,他们是否通过正义的渠道获得财富,获得财富后如何对这个世界进行回馈,才值得人们关心。
《一套书与一个国家的科普史》
家中有一套“文革”版,小时候曾经仔细阅读过,好在当时年幼的我就已对“资产阶级大毒草”之类的“革命语录”极为嗤之以鼻,没被“荼毒”。不过如今回想起来,这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语体,也恰恰见证了这个民族曾经自“愚”自乐背后的无奈与苦难。
京城的浮萍
本刊记者 冯寅杰
关于老北京的选题,在前期的讨论中,我负责的题目是:胡同里的外地人。原本想要采访的是现在生活在胡同里的外地人,以及生活在五环以外的北京人。在采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人,有在胡同里居住的外地人,也有住在五环外的北京人,虽然他们并没有全部出现在我的文章中。但是我想,我所选择的这3位人物,已经足够我想要表达叙述的了。我把外地人3个字加上了引号,是有原因的。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那些单薄的、呈线形的对象的生活不够打动我。真正打动我的,是那些复杂的、立体的、定位模糊的角色。你很难说清楚他们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在南锣鼓巷开店的李宁,已在北京10年,读书,工作,在胡同里开了5年店,从五环外搬到了胡同里居住,成为锣鼓巷商会的副会长。他认识巷子里大部分的人,不管是同样开店的还是原住民,他为锣鼓巷的经济带来增值,为锣鼓巷的一砖一瓦操心,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他也确实是个外地人,但除了户籍,在事实上,他早已成了一个胡同人。
杨璞,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胡同孩子,从小在胡同里踢球长大。但他被迫搬进了楼房,一家人不习惯,又搬回四合院,最终还是因为拆迁搬出了五环外。一方面他舍不得胡同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又因为踢球,还去过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他能理解政府拆迁的动因,他也能说出有得有失的话来。如今,他负责青少年足球培训,看着楼房里的孩子缺乏运动,怀念自己小时候无拘无束的胡同生活。他也的确是个北京人,可他的思维却是国际化的,对他来讲,外地孩子还是北京孩子,胡同还是高楼,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把球最终踢进球门里去”。
韩女士,她是个北京人吗?我不能确认,我与她交谈的过程中,能感觉出她自己也有相当的怀疑。她的母亲是河南人,父亲是北京人,她自己在东北插队了十几年。她一辈子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最终却面临无片瓦遮身。她是北京那一小撮最贫穷的人之一,住在18平米的危房里,搬也不是,不搬也不是。她住在北京绝对的正中心,在天安门前种菜过活,这和“国际化大都市”的称谓相比,就是一种巨大的落差。她惟一的希望是她的儿子和往昔插队东北的故事。她会搬到哪儿去?一定是五环外,她再也听不到升国旗的声音了。她是北京人吗?是给人的印象当中骄傲于皇城根的北京人吗?(她住在前门大街,比任何人都有资格称自己是皇城根的北京人)我很怀疑。在我和何雨珈看来,她和我们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这座城市里的浮萍。
其实文章当中的人物不止他们3位,我,何雨珈,喝大碗茶的一家人,踢球的孩子们,大家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我写下这些天来所看到一些景象和人,尽量让自己不要下某种判断,希望评论性的东西让读者去下,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我也不过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