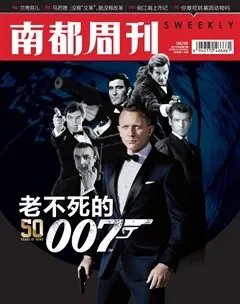张爱玲的蛤蟆酥
说实在的,我谈不上是张爱玲迷,虽然我也跟同辈许多前文艺青年一样,在生命中某段时光,特别爱读她的作品,边读还会边惊叹:居然有人聪慧至此,对人世与爱情看得冷然剔透至此,文笔却又如此从容而鲜丽。可是我对这位民国女子始终也止于欣赏而己,并没有到“痴迷”的地步。
我很小就看过张著。真的是小时候,当时我还在念小学六年级,因为早读一年的关系,十一岁还没满,却已是个酗文字的文艺少女,不,文艺儿童。不论什么书,只要里头印了有密密麻麻的字,拾起便看。实在看不明白的,好比什么尼采哲学之类,看不到半页就撂在一边,再找别的;看得懂的、好看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就手不释卷,邻居在纱窗外叫我出去玩也不理。
有一天,在床头柜上发现妈妈看完以后顺手搁下的《流言》。张爱玲这名字我是听过的,妈妈是台湾文艺杂志《皇冠》的长期订户,我从三年级起就是忠实的小读者,自然知道张爱玲是《皇冠》旗下的大作家,只不过不知怎的,之前竟然没看过张爱玲的作品。我翻开书,第一篇看到是《童言无忌》,光篇名就引起我的兴趣,我还是儿童嘛。
张爱玲从用钱、赚钱这件事讲起,然后说到“穿”。老实讲,她讲的那些多少是“大人”的事,我并不完全心领神会,却已被流利至极又有风格的文字吸引,紧接着,她谈起“吃”,说她自己“和老年人一样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分的‘肉食者’。”
没出息的我不由得吞了口水,因为我也像个小老太婆,爱吃炖得烂烂的菜肴,而且张爱玲不爱的腌菜、酱萝卜也喜欢,还是个吃鱼高手,最嗜食刺多又小的红烧鲫鱼,有鲫鱼上桌,我就不吃白饭,索性将鱼当饭,一人吃上一整条。
只是,这蛤蟆酥是什么玩意?真的也“脆薄爽口”,好不好吃呢?我把这些问题藏在心底,等晚上爸爸回家后问他。爸爸老家江苏,住过上海,果然知道:“就是一种饼啊,绿绿的,颜色像蛤蟆。那东西干干的,没什么吃头。”
可是我还是好奇得很,以后只要跟爸妈上江浙点心店,就要左转转右转转,看看有没有蛤蟆酥可买,可我始终也没找着,遂始终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点心。一直到很多年以后,读到张爱玲较晚期写作的《谈吃与画饼充饥》,里头较详细描述蛤蟆酥,说是“一种半空心的脆饼,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状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绿底子上,绿阴阴的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画像。那绿绒倒就是海藻粉。想必总是沿海省分(份)的土产,也没包装,拿了来装在空饼干筒里。”
传奇才女的形容是比不拘小节的爸爸仔细且生动,我仿佛可以想象蛤蟆酥的模样,甚至它脆酥的滋味──尽管我还是没见过、没吃过,因此也就不知道到底有没“吃头”。
其实,就在这吃吃看或吃不到的过程中,我早该明白,自己虽然一直以为文学是伟大的艺术,大学时主修的也是西洋文学,然而儿时的我看了张爱玲作品后,佩服归佩服,却没有“见贤思齐”,从此发奋练笔写作,反而热衷于学着人家吃吃喝喝,这不已预示着,我终究会了解到自己毕竟不是当纯文学作家的材料,并且在三十岁以后总算接受现实,转而写起似乎更适情适性的饮食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