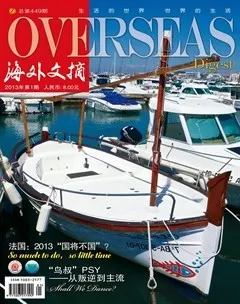漫漫回家路
只是一条小河漫过水坝,但在5岁的萨鲁眼里,它就像个瀑布。每当萨鲁赤着脚在“瀑布”下玩耍时,火车就从不远处“轰隆隆”地驶过,直到夜幕降临,萨鲁才依依不舍地走2英里路回家。
萨鲁的家是小小的泥砖房,屋顶是铁皮的。他和母亲卡玛拉、两个哥哥古都和库卢,以及妹妹舍基拉住在里面。早在萨鲁三岁时,他父亲就抛弃了家庭,那时大哥古都才9岁,已经扮演了家里男子汉的角色。离家不远有个火车站,古都每天在来往的客运火车上捡拾乘客偶然丢失的硬币,有时会接连好几天不回家。
一次,古都带萨鲁走了很远的路,去到一个陌生的工厂,他听说在那里可以偷到鸡蛋。兄弟俩从鸡圈里用衬衫包了很多鸡蛋出来,不料还没走多远,工厂的保安就追上来了,兄弟俩被迫分开逃跑。5岁的萨鲁不识字,连从1数到10都不会。他不知道他居住的那个小镇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但萨鲁的方向感很敏锐,而且非常留意周围的环境。他根据自己的回忆往家的方向跑,跑过街上的牛群、汽车,跑过数不清的街区,终于气喘吁吁地跑到家门口。怀里的鸡蛋早破了,蛋汁从衬衫里渗出来,但幸运的是,他终于到家了。

手足分离
有了这次经历,萨鲁有信心冒险去更远的地方。一次,他被很多流浪狗追赶,摔倒在地上,前额被石头磕破了;还有一次,他爬市中心的一个喷泉,腿被篱笆割开了深深的一道伤口。
一天傍晚,古都带着萨鲁去火车上捡钱。他骑着车,萨鲁则坐在“吱呀”作响的自行车后架上,30分钟后,两人到了火车站,混上了开往布尔汉布尔镇(大概2小时车程)的一列火车。列车一开两个人就开始在地板上找钱,乘务员早已见怪不怪。到了布尔汉布尔镇,两人跳下火车,萨鲁累了,跟哥哥说:“我想睡一会儿。”古都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一个长凳边,说:“你就在这儿睡,我要去做点事情,你别乱跑。”可当萨鲁醒过来时,没有看到哥哥。他茫然地走上了一列停着的列车,以为那列车会驶回家,车厢里人很少,萨鲁认为哥哥很快会找到他,于是找个位置躺下去,很快又睡着了。
当萨鲁再次醒来时,阳光渗进窗户,火车正飞快地驶过郊野。萨鲁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他从凳子上跳起来,车厢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外面是模糊的草地,看不出来到了什么地方。他大声叫着哥哥古都的名字,但没有一点回应。火车在急速前进,他无法进入另一节车厢,他没有食物,没有钱,不知道已经离家多远,也不知道正在去哪里。
萨鲁不得不又等了几个小时,火车才到下一站。5岁的小家伙从来没有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离开过他的小镇,现在,却独自一人到了一个熙熙攘攘的火车站。他看不懂站台上的标记,焦急地向周围的人求助,但他讲的印地语(印度北部的一种语言)大家都听不懂。
最后,萨鲁又爬上另一列火车,希望它能把自己带回家,但那列火车却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后来他知道那是加尔各答)。又一个夜晚来临,萨鲁回到了繁忙的火车站,成为无家可归人群的一员。他又怕又迷糊,蜷曲在一排凳子的下面睡着了。
流浪生活
接下来的十多天,萨鲁爬火车反复地离开加尔各答又回来,希望终点就是他的家乡——但只是发现自己到了更多陌生之地。他靠乞讨和从垃圾堆里捡的食物生活。终于,在又一次无果而终的火车旅行后,萨鲁放弃了寻找家乡的打算,回到加尔各答火车站——他的新家。
小萨鲁在街头露宿了几个星期,直到一个会说一点印地语的好心人可怜他,把萨鲁送进了收容所。印度赞助与收养社团(The India Society for Sponsorship and Adoption)是一个非营利性儿童福利组织,经常寻找适合收养的少年儿童。由于没有人对社团发布的萨鲁走失公告作出回应,萨鲁被添加到了待收养名单,转到孤儿院。半年后的一天,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本红色的相册,对他说:“+c59VFHyfb1Pi3L7GmybNsjp8UI/LAuEEWM290FhwfI=这是你的新家,他们会爱你,会照顾你。”
萨鲁翻开相册,一对微笑的白人夫妇立刻印入眼帘,女人有头红色的卷发,男人有点秃头,穿着一件运动上衣,系着领带。另一张照片上是一座红砖房子,男人在花圃附近的前门廊里招着手。孤儿院的管理员为萨鲁翻译每张照片下的英语说明——“这个房子将成为你的房子,你的父亲欢迎你的到来。”萨鲁翻过那页,看到一张坎塔斯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天上飞的照片,管理员说:“这架飞机将把你送往澳大利亚。”
全新开始
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南端,其港口霍巴特风景秀丽。刚到达那里时,萨鲁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其中一个就是“坎特伯里(Cadbury)”。坎特伯里在霍巴特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巧克力工厂。跟养父母第一次见面,从来没尝过巧克力的萨鲁第一次尝到了巧克力。
约翰·布赖尔利和苏·布赖尔利是一对诚实的夫妇,虽然他们可以自己生孩子,但却选择了收养一个孤儿作为回报世界的方式。约翰说:“世界上需要家的孩子很多,我们想让失去家的孩子重新有一个完整的、温暖的家。”
布赖尔利夫妇有一艘船,他们驾着船带着新儿子萨鲁在塔斯曼海上航行,在这片海里,萨鲁学会了游泳。萨鲁也很喜欢自己的新房间,里面有空调不说,还有树袋熊玩偶、帆船图案的床罩,墙上还贴着一张印度地图。尽管新的生活令萨鲁震惊,但他很快适应了,长成了人见人爱的少年。在养父母家无疑是幸福的,但萨鲁私下里总是怀念自己神秘的过去。“尽管我爱我的新家人,但我仍然想知道我的妈妈、哥哥、妹妹他们现在怎样了,我能不能再见到他们?晚上睡觉前,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亲生母亲的面容。”
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萨鲁进入一个网站工作,他觉得是时候寻找回家的路了。萨鲁打开电脑,登录了谷歌地球,在这个卫星影像和航空拍摄的虚拟地球上,只需轻点鼠标,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任何城市和街道的鸟瞰图。他说:“我在谷歌地球上像超人一样飞到印度上空,努力地放大每一个看到的城市。”
对于自己成长的那片广袤的乡野,萨鲁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了。他真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开始搜索
对萨鲁来说,寻找回家的路比之前他做过的任何事情都难。他5岁走失,不知道自己出生城市的名称,而且他已经不会说印地语了,他只能在谷歌地图上找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和物体。“家附近有一个火车站,还有一个水坝,每当雨季之后水从坝上倾泻而下,就像瀑布一样。还有一个喷泉,有一次我的腿被喷泉的围篱割伤了。还有,在与哥哥分离的那个火车站附近有一座桥,以及一个工业用的大水罐。”可是,当印度的种种建筑和地标出现在屏幕上时,他又傻眼了:该从哪里开始呢?
萨鲁用他能想出的最符合逻辑的方法:沿着加尔各答的铁路线往外找。从加尔各答出发去别的城市有好多条铁路,像蜘蛛网,在乡间纵横交错。就这样在谷歌地图上断断续续地沿着铁路找了三年,还是没有什么结果,萨鲁有点泄气了。他意识到不能再漫无目的地找下去,要缩小寻找范围。萨鲁想,如果他在天刚黑时躺在火车上入睡,天亮到达加尔各答,很可能已经过了12个小时。如果他知道火车的速度,用速度乘以时间,就可以得出走过的路程大概有多远,然后在谷歌地球上相应的范围内搜索。
萨鲁打听到了上世纪80年代印度客运列车的大概时速——每小时80公里,那么他睡着的那个车站离加尔各答大约960公里。
他打开编辑程序,在印度的卫星影像上慢慢地画出了以加尔各答为圆心、半径大约为960公里的一个圆。然后,他意识到还能把范围缩得更小,可以去除那些不说印地语的地区和天气寒冷的地区,他记得自己的家乡很温暖,最终他决定把搜索重点放在那个圆的东部。

可是,剩下的范围内还是有很多弯弯曲曲的铁路线,萨鲁每天晚上要花数小时仔细地沿着铁路沿线搜索。有一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时,萨鲁终于看到了熟悉的东西:在一个火车站附近有一座桥,桥的附近有一个大型的工业用蓄水罐。他放大了那张图片,发现了那个城镇的名字——布尔汉布尔!那一刻,萨鲁好象被什么击中了一样,是它,那天就是在那个车站他跟哥哥分开了。萨鲁继续在谷歌地图上越过树梢、楼房和田野,找到了下一个火车站,他的目光落在它旁边的那条小河上,河水流下水坝——看起来像个瀑布。
萨鲁感到有点昏眩,但他没有停下来,他把自己想成赤脚站在水坝下的5岁小男孩,“我对自己说。好了,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你要找的地方,那么你得证明给自己看,从这道水坝回到市中心。”萨鲁靠着模糊的记忆移动鼠标走过那些街道:这里左转,那里右拐,直到看到了市中心的那个喷泉,25年前他爬那里的围篱,给自己的腿上留了一个疤。
萨鲁盯着屏幕上那个城市的名字——克汉德瓦。接着,萨鲁登陆了脸谱网,找到一个名为“我的家乡克汉德瓦”的群,在群里,他发了这样一条信息:“有谁能帮我吗。我想,我是克汉德瓦人,我已经有25年没见过那个城市了,我很想知道,在那个城市的电影院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大喷泉。”那晚,群的管理员回复他说:“在电影院的附近是有一个花园,但那个喷泉没有多大,而且那个电影院已经多年不开放了。我们会上传些图片,希望你能重拾些东西。” 萨鲁又发了一条信息:“谢谢你,我知道了。还想请教一下,如果我坐飞机到印度,怎样能最快到达克汉德瓦?”
回家,回家

2012年2月10日,萨鲁又一次俯视印度,但这次不是从谷歌地球上看,而是从飞机上。地上那些树木越近,他的脑海里闪现出的童年回忆越多。他说:“那些苦难的回忆那么清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虽然养父约翰鼓励儿子去寻找故乡,但养母苏却害怕萨鲁会伤心。她怕萨鲁关于自己走失的记忆不那么准确。或许,当年他的家人是故意丢弃他,那样,他们就少一张嘴吃饭了。
临上飞机前,萨鲁有点犹豫不决。这是他决心要完成的一次旅行,但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如果真的见到亲生母亲,他要跟她说什么?但现在,他知道了,他会问她:“你们找过我吗?”
20多个小时后,萨鲁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向克汉德瓦驶去。克汉德瓦市跟澳大利亚的霍巴特很不一样,街上灰尘很多,满是缠着腰布和戴着头巾的行人,流浪的狗和猪在赤脚的孩子们身边漫步。萨鲁发现自己到了克汉德瓦火车站,25年前,他和哥哥正是从这个火车站出发。
他在克汉德瓦火车站下了出租车,从这里开始,他决定步行回家。背上背包,萨鲁站在火车站旁边,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告诉自己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
向前走的每一步都像两部电影交叠,一部电影是小时候的模糊记忆,一部电影是眼前清晰的现实。萨鲁走过小时候曾在里面卖过茶的咖啡店,走过曾经在那里割伤了腿的喷泉,现在这些地方好象比他记忆中小多了。尽管标志性的建筑还在,但这个城市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最后,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熟悉的泥砖墙、铁皮屋顶的小屋前面,萨鲁僵住了,记忆中的画面汹涌而来。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跟哥哥在附近放风筝,夏天一家人睡在屋外纳凉,他靠在母亲身边数星星。萨鲁不知道自己在小屋门前站了多久,直到一个矮小的印度女人走出来,用一种他再也听不懂、更不会说的语言跟他说话。
萨鲁指着自己,用带有浓重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说:“萨鲁。”然后他指着那房子,说出了家人的名字,“卡玛拉、古都、库卢、舍基拉”。他拿自己小时候的相片给她看,最后,那个女人用蹩脚的英语说:“这些人已经不住在这里了。”萨鲁的心一沉,想着:“天啊,难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很快,另一个好奇的邻居走过来,萨鲁重复了那一串名字,并让邻居看他的照片。他拿过相片,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告诉萨鲁说他离开一下,马上就回来。几分钟后,那人回来了,把相片还给萨鲁,说:“走吧,我带你去见你母亲。”
萨鲁茫然地跟着那人转过街道拐角,几分种后,来到一个泥砖砌成的房子前,那里站着三个穿彩色长袍的女人。那人说:“这是你母亲。”
“哪一个?”萨鲁心想。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女人,她们也有点吃惊,呆站在那里。萨鲁看过一个,心里说:“不,不是你。”然后看下一个,心里想:“可能是你。”又想了一下,在心底肯定地说:“不,不是你。”最后,他的眼光落在中间那个苍老的女人身上,她穿着淡黄色的印花长袍,头发白了,被染成橙色,用发髻挽在脑后。
那女人什么都没说,走上来一把抱住了他。那一刻,萨鲁不会说话,不会思想,除了伸手回抱她,已经别无选择。然后,他的母亲拉起他的手,把儿子领回了家。
悲喜相聚
萨鲁的母亲现在皈依了穆斯林,有了个新名字,叫法蒂玛,她独自住在一个有两个小房间的房子里。她和儿子语言不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只是互相看着微笑、流泪。法蒂玛说:“我心里的喜悦比海深。”很快,一个黑色长发、穿棕色长袍的年轻女人含着泪进来了,她伸出双手拥抱了萨鲁,她和萨鲁相似的长相让在场的人一看便知,那是萨鲁的妹妹舍基拉。然后进来一个留着胡子的男子,头上的黑发里已夹杂着几丝斑白,那是萨鲁的二哥库卢。来的人越来越多。法蒂玛一直拉着萨鲁的手,高兴之余,也有人怀疑,问法蒂玛,“你怎么确定这是你儿子?”法蒂玛指着萨鲁额头上那次被狗追赶留下的伤疤,说:“这伤口当时是我包扎的。”
在一个会说英语的朋友的帮助下,萨鲁向人们讲述了25年前他那次不可置信的旅行。之后,他看着母亲的眼睛,问:“你们当年寻找过我吗?”法蒂玛回答说她找了好几年,沿着铁路找,就像他这次寻找回家的路一样。
萨鲁已经到家有一会儿了,这时,一个问题闯进了他的脑海,他意识到少了一个人,他问:“古都呢?”
法蒂玛的眼泪涌出来,说:“你大哥,他已经不在了。”原来,在萨鲁失踪一个月后,人们铁轨上发现了古都断成两截的尸体。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家只觉得萨鲁的母亲实在命苦,几个星期内失去了两个儿子。
现在,最小的儿子又回到身边了,法蒂玛开始给他准备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菜,咖喱羊肉。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沉浸在似乎不可能的梦境里。
在发给澳大利亚父母的一条短信里,萨鲁写道:“我想问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我的家人是真实诚恳的,正如在澳大利亚的你们一样。我的生母谢谢你们,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把我养大。我的生母、哥哥和妹妹都充分明白,你们是我的家人,他们不想以任何方式干涉。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对我最重要,这是永远不变的。我爱你们。”苏在回复给萨鲁的短信里说:“亲爱的,这真是个奇迹。我们为你高兴,你要保重。我们真希望能在你身边给你支持。”
萨鲁在克汉德瓦呆了11天,每天都和家人在一起。他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为难的情况也出现了。法蒂玛试图说服儿子留下来,但他告诉她,他的生命在塔斯马尼亚。萨鲁答应每个月寄100美元当法蒂玛的生活费,但法蒂玛对这个用钱来代替距离的主意浑身不舒服。然而,毕竟那么多年不见面了,他们都不想让不同意见破坏了这新建立的关系,以前,就算在电话中问个好都是无法想象的。
在离开克汉德瓦之前,萨鲁还有一个地方要去。一天下午,他让哥哥库卢开摩托车带他去看了那道水坝。他坐在后座上,指出这里向左拐,那里向右拐,直到他们站在河边,站在那个像瀑布的水坝前。
[译自美国《名利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