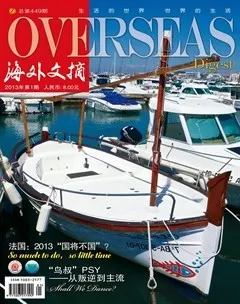喀布尔 生之痛
他们曾是五兄弟,来自石头裁缝街的五兄弟。他们和父母一起住在喀布尔老城区的一居室中。妈妈每年生一个男孩,直到她生下最小的那个之后去世。然后,战争开始了。
和这五兄弟中的老四法胡定喝一杯清茶,就足以了解他们的故事。如果问起长兄,他会说,萨布尔死于反对圣战者的斗争。老二呢?苏库尔死于支持圣战者的斗争。老三呢?沙普尔死于反对塔利班的斗争。老四呢?老四是我,我在手榴弹袭击中失去了一条腿。老幺呢?那是法哈德,他还好好的,只想离开这个国家。
法胡定的眼神几近绝望。可以说,这不只是他家史的总结,也是整个阿富汗历史的缩影。

战争像章鱼海怪,吞噬着这个家庭
法胡定·巴德里是一个强壮的人,脸上满是战争的刻痕。他赤脚坐在他的小作坊——位于喀布尔裁缝区的“兄弟裁缝店”中。又停电了,工人没有来,他继续缝制一件白色的传统阿富汗长袍。法胡定为圣战者、塔利班和美国人做衣服,如果接下来塔利班掌权,他还会继续做下去。他做衣服,因为他喜欢色彩,也因为缝制衣服保证了他的生存——这是长达33年的战争中惟一的恒量。
裁缝法胡定是战争方面的专家。他出生于1978年,正是苏联袭击阿富汗的前一年。自那以后,战争就一直笼罩着这个国家。但是对他来说,战争不只是战争。他能够对它们进行更加细微地区分。他经历过小规模的游击战和内战,多战线战争和解放战争,了解突击步枪的不同声音和散弹的气味。可以这样说:裁缝法胡定也是个战争专家,能够区分各种不同的战争,就像植物学家能够区分20种郁金香。
一般来说,孩子们要经历不同的生长期,法胡定经历的则是不同的战争期。他认识到战争会一再发生,就像季节交替循环,是自然的法则。对法胡定来说,战争就像章鱼海怪,无情地夺去了三个哥哥和他的一条腿,他的学校、房子和朋友,他的童年和梦想。
在阿富汗,巴德里一家的故事很普通。如果不是1994年摄影师西姆斯·穆尔费偶然被困在喀布尔的石头裁缝街上,它不会为人所知。当时正是内战的高潮期,苏联撤军之后,国家陷入混乱,民兵组成的军队从小山丘上炮轰喀布尔,这个有着3000年历史的文化都市瞬间千疮百孔,满城尘土让人不能呼吸。几乎所有居民都逃离了老城,只有退休的制图员萨米·巴德里和他的儿子们留了下来。他们没有流亡所需的钱,没有人愿意给这位鳏夫提供居住地。他们在残破的房子里向摄影师穆尔费打招呼,这个爱尔兰人在这里待了几个晚上,从此以后就再没有真正离开。他一年年地回到巴德里家里,拍下照片。最初家里还有五个大小伙子,后来三个,最后两个,战争像贪得无厌的怪物一样吞噬着这个家庭。
首先是老大萨布尔的去世。他是一个安静、敏感的少年,像很多阿富汗人一样在冷战中充当苏联的炮灰。萨布尔在路加省被圣战者枪击而死,是在苏联占领期内死亡的130万阿富汗人之一。
紧接着,战争夺去了法胡定的腿。那时,14岁的他正在买面包,手榴弹在面包店爆炸,把他的腿撕裂了。一个老人把他和另外四个受害者扔进牛车中时,他的脚趾头还能动。但是医院没有时间做旷日持久的治疗,医生给他锯了腿,以便给等待着截肢的另200个病人空出位置。直到六个月后,他化脓的截肢伤口才痊愈。
说着这些的时候,法胡定异常冷静,如同一个局外者。他难道不为医生的决定感到愤怒吗?“没有,他们是为了救其他人。”,可他本来不是可以不失去腿的吗?他有些奇怪地看着我,“能在战争中幸存就已经是福气。”
在喀布尔,除了参加民兵组织,已经没有其他工作可做。只有一个行业永远繁荣,那就是杀戮。老二苏库尔决定为家里赚钱,他要去圣战将军马苏德手下当兵。父亲反对,因为长子正是死于圣战者的枪火,但苏库尔还是去了。“他是我的榜样。”法胡定说,“他严肃、认真,想成为工程师。”几周后,一个绿眼睛的军官带来消息:苏库尔死了,他死于塔利班枪下。
老三沙普尔是个有趣的年轻人,热爱自由,是家里的开心果。像很多阿富汗人一样,他在苏联接受教育;也像很多阿富汗人一样,为了赚钱,他参军了。悲剧重演。父亲又抗议,儿子又前行,最后回来的又只有绿眼睛军官。他宣布沙普尔也死了,也是死在塔利班枪下,成为1991到1996年内战中失去生命的40万阿富汗人之一。
现在,法胡定突然成了老大,他感到自己有责任照顾家人。但是,作为一个截肢者,一个独腿民兵,他能做什么呢?食物紧缺,老父亲虚弱不已,他们搬进地下室,以躲避攻击。在那里,他们就着烛光读《可兰经》,用收音机收听波斯语BBC新闻。父亲让法胡定许下诺言——再也不能拿起武器。另外,他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挖出尸骨,卖给巴基斯坦肥皂生产者。于是,法胡定每天都会跛行着穿过废墟卖胡萝卜和土豆。如果绿眼睛军官路过,父亲就会和他一起吸大麻,以确定他不会让他心爱的儿子们入伍。
1990年,喀布尔有200万居民,六年后缩减到20万,到今天又有了450万。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喀布尔那样,在战争的节奏中膨胀和收缩。街头的买卖又繁盛起来,穿着长袍的战争寡妇乞讨着面包。生活好像恢复了平静,但是人们没有建起漂亮的建筑,只是稍微修补老房子,好像这个城市不相信未来。
剩下的父子三人不愿意住在石头裁缝街的老房子里。“每天提水的时候,我们都从尸体旁经过”,法胡定说,“我鼻子里还能闻到人们身上的血腥味,看到几只狗在街上玩一个人头。”他们从不谈论战争,没有什么好回忆,回到恐惧的地点只会增加创伤。弟弟法哈德有些痛苦地笑了,他说,我们试着快乐。法胡定没笑,他的目光中有无法抹去的悲伤。
他的反抗是安静的,就像针刺
正是在危机中,在那狭窄的地下室里,法胡定学会了缝纫。是一个老裁缝教会他的。最初他缝纽扣,然后帮忙熨衣服,填塞,量尺寸。在破败不堪的喀布尔,已经没有警察、老师和政治家这样的职业,但即使在战争中,人们也需要穿衣服。他的手非常灵巧,起早贪黑地做衣服,用微薄的积蓄买米面。18个月之后,他有足够的钱买一架自己的缝纫机了。后来,他也教会了法哈德缝纫。
1996年,塔利班入主喀布尔,对法胡定来说最糟糕的战争开始了。这是野蛮人反对自己人民的反人类战争。他适应了新的法令。缝制深色衣服,过膝长袍,过脚踝长裤,但是从来不为女人做衣服。他像所有男人一样留着胡须,如同法令第三条中“促进美德抹去罪恶部”规定的那样。
他是一个裁缝,不跟风巴黎时尚,不迎合传统潮流,只是听从政权的指示。但是,法胡定对杀害了哥哥们的新当权者进行了无声的反抗。他没有遵守法令第10条的“英美发型禁令”,而是留了长发。他从来不去看公开处死,播报员像是为马戏团表演报幕一样报着死者的名字。塔利班占领这个城市时,他亲身经历了他们怎样阉割老总统纳什不拉,之后又在阿丽亚娜广场当众绞死他。他发誓他没有为这帮野蛮人效过一点力。
那时候,法胡定希望他的父亲能够活到塔利班灭亡的那一天,然而他在一天夜里突然去世了。塔利班甚至夺去了这位老人最后的快乐——吸烟。他不能听BBC和音乐,也不准吸大麻和打牌,即使是有摄影师穆尔费参与的全家照片也不允许挂在墙上。法胡定说,父亲是被塔利班害死的。
2001年美军入驻之后,这个裁缝认为看到了和平的端倪,这是一种安宁的自在。对他来说,北约战争是到目前为止最大快人心的战争,一种解放战争。贸易恢复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庆祝,他拄着拐杖走过街道,静听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他缝制更加紧身的衣服,重新使用多彩的日常色调——蓝色、米黄色和白色。他拒绝了内务部的一个大订单。我只为自己工作,他说,不为政府。他不喜欢腐败政治家,他的反抗斗争是安静的,就像针刺。
法胡定不记得停火时间有多长,大概几个月吧,也可能有一年。城里的斗争停歇了,却出现了自杀式袭击和爆炸案。它们摧毁了购物中心、洲际酒店和印度使馆。2004年爆发了新的战争,炸弹隐藏在衣服下,死亡从天而降。敌人不再站在山头,而是隐藏在身边的人群中。
33年的时间中,战争主导了法胡定的生命,把他塑造成一个全新的人。战争训练了他的思维、感觉和整个存在。这天早上,信息传来,四个自杀袭击者正前往喀布尔,法胡定决定避免出现在特定场合和路线。作为卷入战争中的人,他可以对身边的人作准确的预估,端详爆炸云所在的地平线,小心地绕过死亡,就像其他人绕过堵车。他静听的不是鸟的歌唱,而是作案者的脚步。
和平,一定是淡绿色的,它是救赎的色彩

父亲死后,法胡定结婚了,建立了一个家庭。他在城市边缘建起一栋小房子,裁剪出紫色的窗帘,给房间刷上杏色,在床边摆上粉红色的塑料玫瑰。日子越阴暗,他对色彩和温暖就越渴望。
一个周五,法哈德和他的两个孩子前来拜访。那时,法哈德已经放弃了裁缝行业,改作婚纱摄影,他觉得这更有趣。法胡定希望他的孩子会读写,不能像他自己一样。儿子们应该上大学成为工程师,那女儿费鲁扎呢?他思考良久:“她应该上完高中。”不能更久了吗?“不,已经够了。”
不久,几个裁缝过来打牌。他们坐在地毯上,法胡定坐在中间。按照塔利班的法令,赌博应该判处一个月监禁。他们说着塔利班的黄色笑话,就像英格兰人说苏格兰人。一个瘦瘦的男子给他们送上茶。这样八个男人坐在一起欢闹,仿佛在自由中享受最后的日子。
我只是一个小裁缝,法胡定强调。但是,他熟悉自己的祖国,对于未来他很悲观。很多阿富汗人都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最初可能想参与家乡的重建,但是现在他们离开了这个国家。
来自联合国和北约的500亿欧元流进了政治家和官员的腰包,他们在新德里和迪拜建起房子。他们抢夺现在,以逃避未来。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每个文明社会的支柱——教育和知识。对法胡定来说,他们和那些一直把阿富汗看作自己欲望领地的英国人、苏联人、伊朗人和巴基斯坦人没有什么不同。
你会逃到哪里去呢?
我能去哪儿呢?他问,指指他的截肢。我会为活下来的人做衣服,但是不为塔利班做。
法哈德呢?
他是最早走的那一批中的一个,不管是去哪里。
那法胡定,你就是五兄弟里惟一的一个了。
那我就是最后一个,我不走。
在死之前,法胡定非常愿意感受一下和平。他33岁了,还从来没有认识过它。他想象过和平的颜色,一定是淡绿色,那是救赎的色彩。如果要缝制和平,他会用淡绿色的材料缝制整个阿富汗的地图。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认识这种和平,他说,听起来就像要和某个来自远方世界的神秘陌生人会面。
[译自德国《明星》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