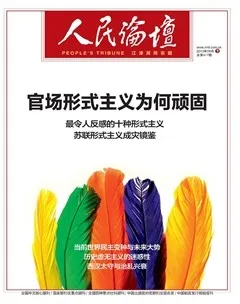舆论市场的自由与调节
编者的话
互联网无孔不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使得任何一种媒介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都远远不能和网络相提并论。公众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可以各种各样的身份,隐藏在虚拟网络之后,尽情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描述社会生活的新闻事件,由此,与之相呼应的新闻自由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薛蛮子事件使得互联网时代下新闻自由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媒介由宣传工具逐步回归到传播工具,新闻控制已日益被打破,网络时代新闻自由与舆论引导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
新闻出版自由不是某个人的天才发明,不是天赋的人权,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群的聚合,信息交往达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一种人权需求。1922年,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刊物《向导》的发刊词,实际上就简述了这一人权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刊词写道:“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就提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号召人民起来主动争取自由的权利,无数革命先烈为此奋斗了一生。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行调节的过程
我们现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章,谈得最多的是美国新闻出版自由的发展过程,其实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文献,主要出现在当时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英国。为什么19世纪是新闻出版自由理论提出和得到丰富的时期?就在于那个时期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对新闻出版自由的需要,而且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的大众传播业也已经形成规模,新闻出版自由是这个行业生存的前提。当时有两句话比较典型: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行调节的过程。
观点的自由市场,即把经济领域的竞争自由直接搬到思想意见领域。自行调节的过程,也是市场经济的观念,即假冒伪劣的产品会通过市场的自然筛选而被淘汰。然而,约百年的新闻实践证明,思想意见领域的东西不像物质产品那样会被自然淘汰,很多教唆犯罪、诽谤他人的东西被接受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地扩散,因为大众传播业本身亦是资本控制,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益,而不会为道德和法律承担责任。传媒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一种权力,没有制衡机制是无法保证其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
一个偶然的事情,造就了一个文件,即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这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的老板亨利·卢斯出钱请一批文化人做的一个关于传媒的报告,意在自我夸奖。不料以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为首的这个委员会发现了很多传媒的问题,他们坚持要写出来,卢斯停止资助,但他们依然克服资金困难,把事情做完了。他们在此前新闻界流行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两句话基础上,补充了第三句:传媒的社会责任。在肯定新闻出版自由的前提下,委员会提出并强化了传媒自律的问题。这个文件指出:新闻业享受“自由”同时必须担负“社会责任”;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是基本人权,而新闻自由(美国意义的)仅为传媒发行人的权利,所以对这种新闻自由的过分保护,并非符合个人和社会利益;所以,要鼓励推行新闻自律,维护新闻的自由流通,以及意见表达的公正性。文件建议建立新闻评议会,使受到新闻业伤害的个人、团体有申诉的机会。
当时这个文件受到美国多数传媒的抵制,然而数年以后,这个观点逐渐被国际新闻界接受,传媒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在世界新闻业界的协会、在较大的传媒集团内部得以形成。这是以自律的方式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一种良性制约性质的保障。
自由在行业圈内需要有职业道德和规范的监督
而在我国,这些法理仅存在于法学学术研究和新闻法研究的层面,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我国传媒人对新闻出版自由、国际公约的表达自由的认识,多数停留在字面上。传媒领导机关对此的了解也微乎其微,简单的批判式思维遮蔽了对新闻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学理的深刻认识。
在我国的传播实践中,随意发出禁止的指令已成习惯,较少考虑法律依据和如何依法行事。而传媒人一方,特别是关于利益冲突的某些报道,不遵守职业规范,随意使用手中的报道权,站在冲突的某一方而不是站在第三方,造成报道失实并引发不理性舆论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国目前的新闻体制,一方面存在很多对传媒不合理的控制,另一方面我们的传媒在某些报道领域则拥有比西方媒体更大的自由度。因为实际上不存在明确的这方面道德要求和具体规范,也没有真正的行业评价(仲裁)组织对各种违规的行为做出公开谴责和处罚。
我国很少有传媒主动更正报道差错和向受众道歉,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报道比西方传媒更真实,而是因为我们报道出了差错很少公开承认,更不要说更正和道歉了。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几乎所有传媒,都报道了母爱短信的故事,可直到现在,没有一家传媒为此假新闻向受众作出更正。1951年联合国出版自由委员会通过了两项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国际公约草案,同时还通过了传媒更正与答辩的国际公约草案,目的就是平衡自由与责任。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不少利益冲突事件,每次读来都会令人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其煽情的文字水平,可谓炉火纯青。但当笔者看到比较全面的事实时,不能不感到传媒的报道太随意,有意站在某一方,不是陈述事实而是有意掩盖某些事实,有意把矛盾推向势不两立的境地。自由在行业圈内需要有职业道德和规范的监督,不能超越道德和规范。
核实事实是新闻的工作规范,然而在相当多的冲突性报道中,记者只听一方的陈述,忘了“罗生门”教导我们的人天生具有的弱点,而关于另一方的说法,不是缺项就是被断章取义。例如相当多的关于拆迁钉子户的报道,只看到当局如何要他们搬,采用了何种暴力,但他们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始终不得要领,即使含糊地报道了,也令人感到不合逻辑,因为似乎不高的要求不可能造成钉子户的现实结果。如果我们的传媒人如此“自由”地运用手中的发稿权,那实在是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曲解。
自由始终伴随着责任。我们在实践新闻出版自由的时候,确实遇到了一些不该有的不自由的限制,但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我们是否滥用了人民赋予的新闻报道自由的权利?我们对自己的报道遵循了职业道德和规范了吗?承担了社会责任了吗?在中国特有的新闻体制下,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大于西方国家,因而过去毛泽东说的“政治家办报”在新形势下需要讲一讲。我们不是总理,但要站在总理的角度把握大局,我们不是总书记,但要在总书记的角度全盘考虑问题。我们的报道如果公开了会造成怎样的社会效果,是解决了问题还是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有些报道可能事实本身是真实的,但站在全局角度看,若在有限的范围内能解决问题,就不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开展示。这里涉及的不是知情权而是策略把握。例如今年3月1日电视台关于糯康死刑执行前两小时的“生命倒计时”现场直播,除了直接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不得示众的规定外,主持人也缺少对全球死刑格局的全盘政治考量。在全球139个国家废除死刑的情形下,我们的传媒如此大张旗鼓地直播一个死刑犯的“生命倒计时”,会有怎样的国际传播效果?我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的目标会陷入怎样的境遇?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的选择,不该从政治角度通盘考虑吗?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责编/徐艳红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