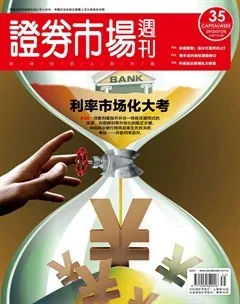存量如何盘活?
近来,“盘活存量”一词热度颇高。这一概念揭示了现实经济运行的诸多不合理现象,有助于纠偏之前的某些错误政策。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盘活存量”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含糊性,如果理解错误,其带来的正面效果甚至不如它可能带来的误导。
表面上,中国经济运行的一大特征是货币过多,增速过大。货币供应量已达104万亿元,是GDP规模的两倍。一个自然的诊断是,存在着“货币空转”现象,没能拉动经济增长,也催生了房地产市场泡沫。未来,不能再寄望于以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来推动经济,而必须盘活已经存在的货币信贷存量,让大量停留于低效率项目、无法拉动经济增长的资金重新活起来。
这一诊断不能说错,但并未切中问题的根本。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有效资本存量快速提升的结果。投资有两类,一类是对被识别的发展机会的实现而配套的投资,称为有效投资,它令生产可能性边界得以扩张;另一类是竞争性投资,其效果是提升了过剩产能,这一类投资可以归类为无效投资。投资是否有效事先很难确定,事后却可以通过资本回报率来定义。不能挣取合格投资回报率的投资被定义为无效投资。林毅夫强调只有投资而不是消费才能推动经济增长,这一命题只对了一半,它应该被修正为“只有有效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增长”。无效投资可以推升当期GDP,却无法推升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以过剩产能的形式形成经济中的肿瘤。
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近年来一直高达48%左右,如此之高的投资依赖居民储蓄与企业利润提供融资。事实上,后两者之和甚至大于50%,多余部分以贸易顺差形式转移为对外国的融资。从形式上划分,投资资金来源可能来自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前者不会额外增加货币量而后者则直接参与货币信贷量的创生。如果间接融资比例较大,则货币增速较快。银行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不论银行运作如何复杂,其功能仅限于此。换言之,不是货币推升投资,而是投资推升货币;是投资过多导致货币过多而不是相反。在投资与货币的关系中,前者主动,后者响应。
如此,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核心是投资过多,导致过剩产能堆积。过度投资有其深刻的体制背景,而投资是否过多,不应该以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与美国资本存量的对比来衡量,而必须看资本是否能够获取合格的资本回报率。中国投资过多的证据随处可见,从数据上看也十分明显。以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例,资本回报率(ROA)从2007年的8.9%跌至2013年一季度的3.5%,下滑了60%;与此同时,过剩产能率目前已经超过31%,达到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如此低的整体ROA表明,许多企业依靠融资而不是利润维持生存,沦为所谓的僵尸企业。而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恶化了过剩产能情况,压迫别的公司也难以获得利润。这样,融资规模越大,过剩产能越严重,投资回报率越低,反过来导致融资需求越庞大,这构成了恶性循环。这一机制,在持续升高的债务比例与持续降低的ROA中得到了鲜明的印证。
因此,问题很明确,需要盘活的信贷货币存量在实体层面对应的是无效投资与过剩产能;要盘活货币存量,就必须化解过剩产能。要达到这一目标,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不能简单粗暴地收紧货币政策,否则融资支持的支付承诺链条一旦断裂,天量呆滞账与企业破产潮可能自我强化而引发金融危机;不能误以为可以通过金融魔术就神奇般地令过剩产能消失。
第二,唯有依靠民营小企业富有活力的探索,才能找到新的有效投资机会,带动经济进步。
第三,不能再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与一般认识相反,目前的基础建设投资如同制造业投资一样已经出现了过剩;其资本回报率在大部分省份都低于制造业,在西部省份尤低。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消化过剩产能是在堆积更大规模的过剩产能与更大的金融风险,不过是让推迟的危机以更大的规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