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正当时
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社区、微营销、微旅行、微生活、微民……一系列“微”特征的文字体系、艺术形式、生活方式以不可阻挡之势,润物细无声地介入当下生活,可谓无“微”不至。无论你是否接受,新媒体环境下以短小精炼为传播特征的“微时代”已经来临。140个字也可以完成一篇紧凑的小说,三分钟即可成就一部从现实走向梦想的电影,每一个人只需要一台DV甚至一部手机、一个想法、一点创意,就可以用影像来展现大千世界和所思所想。这是一个用“小身躯”完成“大承载”的时代,笔者且以“微电影”透视这个“微时代”。
“微风”盛行
“微时代”的显著特征,是以微信息、微社区、微媒体为代表的信息处理方式。现今信息的传播方式和手段已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掌上电脑、手机等方便快捷的小型高科技介入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如果说互联网是对传统媒体的一次革命,那么微时代的各种产品就是对互联网的一次革命。
在媒体多样化的当下,人们的关注习惯经历了明显的碎片化过程,有更多的年轻用户流入网络,中国已有超过4亿用户通过移动设备和电脑看视频的时间多于电视。2011年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达3.25亿,网络视频观看时间的增速是上网时间增速的4倍。如今,80后、90后群体是视频网站的核心用户,这批网络群体有着自己的生活需求,快节奏的步伐使他们没有大块的空余时间,而同时又具有追求精致与品位的需求。于是,“微小说”、“微营销”、“微生活”、“微电影”等微媒介,以“短、小、精”等特点快速被这批用户接受。

微电影就是“微时代”媒介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电影模式。在时间日益碎片化的当下,人们的时间被分得越来越散。微电影的时长、投资、制作规模都比传统电影短小,又制作精良,开创了一种网络影视叙事的新模式,更适合受众在碎片时间移动观看。在全媒体整合、信息碎片化、文化快餐化的今天,微电影从入市就被寄予了厚望。动辄几个小时的传统电影和影院模式的观看方式,无法吻合网络视频用户“碎片”时间的需求,而高强度的生活依然需要感动和滋润,微电影的网络崛起成为必然。
2010年秋天,一部名为《老男孩》的网络短片红遍中国,影片主创“筷子兄弟”是一对名不见经传的业余视频摄制组合,他们几乎用自己的经历和感慨,讲述一对 “老男孩”笑中带泪的追梦之旅和青春悼念,这部42分钟的短片,创造了16天破4600万的点击率。影片中那份蓦然回首青春已逝的感伤和小人物酸甜苦辣的梦想追逐,引发70后、80后的集体回忆,“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模样……” 经典旋律戳中泪点,让广大网民含泪共鸣。“筷子兄弟”一度成为“青春”、“梦想”的代言人。一部小成本、小制作、零大牌、无造势的网络短片成为2010深秋的一匹网络黑马,也催生了国内“微电影”概念的提出。
也是在2010年,微博在中国落地生根,这一媒介正在改变当下中国的媒体传播环境,在公共事件中,微博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时尚,也体现着一种社会变革的方向。每个人以微小的力量融入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转型之中。整个互联网都加速向“微时代”迈进,“微小说”、“微营销”、“微生活”、“微简历”、“微旅行”等“微”名词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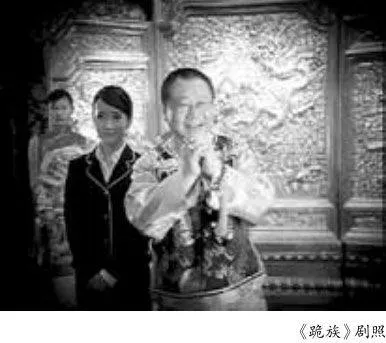
微电影的“前世今生”
“微电影”的界定还没有明确学术划分,但已有一些被公认的特性,比如“微时长、微制作、微传播、微投资”,数十秒至数十分钟的放映时间,几天或数周的制作周期,平民亦可承受的投资规模,完整的剧情构架,在网络等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适合在移动状态下观看等等。
在《老男孩》之前,具有微电影特质的网络短片已经初见端倪,2005年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微电影的雏形,这部带有恶搞性质的短片重新剪辑了电影《无极》和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栏目《中国法治报道》,对电影原作进行颠覆和解构,已具有微电影的基本特质,但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真正原创的微电影模式。也是在这个时期,DV、单反相机、智能手机等数码产品广为流传,扩大了视频制作的圈子,不少电影爱好者自行学习剧作、剪辑、导演,越来越多的网络短片诞生于互联网。可以说,微电影正是兴起于这些来自相机、DV、手机的各种参差不齐的“小短片”。
与此同时,不少专业人士制作的“电影广告”也开始具备微电影特征,比如2006年冯小刚、陈凯歌和张纪中联合为雅虎中国拍摄的广告《阿虎》《跪族》,都具备了完备的电影制作团队、完整的故事架构、商业元素的整合等这些微电影元素。个人自拍的随性表达,加之专业人士和机构的介入,才逐渐造就了登堂入室进入“电影”层次的真正的“微电影”。
2010年,由中影集团联手优酷网策划“11度青春”系列,《老男孩》爆红网络,成为微电影的成功典范。同年12月,中影与凯迪拉克联手,推出改编自微小说的首部“巨制微电影”--《一触即发》,微电影的制作班底由专业团队组成,仅用短短90秒创造紧张刺激、环环相扣的情节以及类似007风格的宏大制作,也为凯迪拉克完成了一次很成功的广告营销。《一触即发》既是第一部大制作的网络微电影,又是一次成功的微电影营销案例,是一部具有微时代里程碑意义的微电影。2010年网络微电影、网络门户自制剧以及各大电视台的自制剧呈现出爆炸性增长,很多人将2010年称为 “微电影元年”,紧接着2011年有不下2000部微电影问世,微电影几乎是在一年内乘风而起,发展之快令人措手不及。
近几年涌现的优质微电影作品也遍地开花,如《66号公路》《看球记》《爱疯时代》《我爸》《线索》《赢家》等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叙事完整,贴近当下,在网络上的点击率节节攀升,在传播效果上远远超越其它媒介。在这种潮流趋势下,除却个人化的作品,许多有组织的微电影行为也陆续出现,各大视频网站纷纷投入自己的微电影制作中,包括优酷、土豆、56视频、腾讯视频和搜狐高清等在内的主流视频网站纷纷在各自微电影领域暗自发力。
微电影的兴盛并不单纯是中国现象,国外微电影创作也已经非常成熟,奥斯卡、戛纳等顶级电影节每年都有一大批的优秀微电影参展,而品牌赞助的广告性质的微电影也大行其道。像Vimeo经典励志微电影《3*3》,法国悬疑微电影《调音师》,盖里奇广告微电影《走向传奇》,Christopher Kezelos历时几年完成的定格动画微电影《零》等,都是近年来享誉世界的微电影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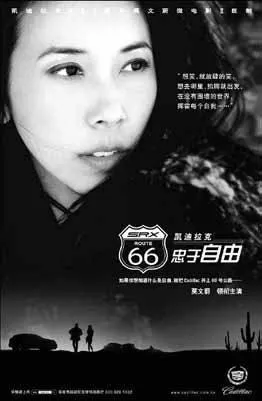
“微时代”的草根盛宴
“微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为草根和平民提供了展示平台。“微”媒体有一个共同点:门槛低,成本低,互动性强,几乎是人人都可参与的“草根秀”舞台。当下中国,微媒介普及之广,囊括了几乎所有阶层,上至文化精英、名人高官,下至出租司机、打工一族,都将“@我”,“加关注”,“朋友圈”,“互粉”等“全民新词汇”挂在嘴边。“微时代”为所有人群提供了表达和展示的机会。
以微电影为例,当前国内的“大电影”市场整体上走大制作、高投入、大场面、明星制的华语大片路线,票房回收依赖大牌导演和大牌演员,因此,很多年轻导演想在中国大银幕上杀出重围实现梦想,可谓困难重重,而电影创作之路又必须依赖实践磨练。微电影的制作过程,囊括了剧本、资金预算与筹备、建组、选演员、采景、中期拍摄、后期剪辑、制作、发行等一整套完整的电影制作流程,而在成本、时间、人力的投入上则远远低于大银幕电影,也是在这种态势下,微电影成为承载年轻导演和非专业电影人电影梦想的新空间。“大电影”是“孔雀”,光彩夺目,但也因为“养殖”成本过高,不是每人都可以参与。而微电影是“麻雀”,虽然小但是生命力极强,每个人都可以揽入怀中,“飞入寻常百姓家”。
微电影打破了传统电影创作中“精英”与“草根”的界线,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电影创作对专业学院训练的依赖逐渐减弱,电影创作不再是知识精英的特权。这是“微时代”显著的文化现象,如同网络作家之于传统作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最终发展成精英与草根、专业与业余多元共生的形态,各自发展并交融影响。德国当代艺术大师波伊斯提出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正在被广泛实践。
时至今日,除了草根族,明星、名导、名企也纷纷试水微电影。华语知名导演顾长卫、蔡明亮、姜文、王家卫、彭浩翔、许鞍华、王小帅、陆川等都纷纷“触电”微电影。彭浩翔在一个访谈中表达了微电影对这些成名导演的吸引力:“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故事,需找到另外一个媒体去自由表现,一个没有时间控制的地方,70分钟可以,30分钟也行,而网络媒体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发挥自己的空间。”从整体上,微电影的创作还是保持了草根和大众的特质,校园微电影、社区微电影、企业微电影等,都在互联网上遍地开花,渐成燎原之势。
微电影在题材和形式上的自由度,是其发展和壮大的显著优势,相对于国内大银幕院线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微电影的“自由表达”空间较大,可具有更鲜明的个人化特征。中国的电影发展到现在,已很难再找寻一个统一的发声群体,而是以个体创作表达不同的价值诉求。电影可以不再是严格的90~120分钟的制片厂体制下在电影院播出的作品,而可以是时长不固定的、极其个人化的、在网络上随意点击就可收看到的片段。王小帅、顾长卫等导演都表示,微电影的平台诱惑在于创作自由度。
“微时代”提供了诸多让平民自由表达的平台,把分散无名的“微”个体彰显出来,并给了这些“微”个体一个凝聚起来展现自身力量、发出自己声音的场所。再以现今如火如荼的微博为例,正是因为在一个个“微”背后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和一股股鲜活的力量,这些微小力量、微小进步逐渐累积,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其实,所有“微”形式的创作都是一场考验,俗话说:长文章,好作;短文章,难攒。在“移动”状态、“超短时间”限度和“休闲”特征的模式下,“蒸馏”出精品,拍出引发共鸣的微电影,写出扣人心弦的微小说,发出掷地有声的微言论,都绝非易事。
“微时代”自由表达双刃剑
“微时代”传媒的本质,是将一切可以利用的碎片时间最大限度地不断开发,让注意力经济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微”媒介成为精明商家拓展地盘的新领域,这也意味着微媒体会有更多的广告植入、话题制造以及商业营销。比如微电影在全民“自由表达”的诱惑背后,又潜藏着微电影的赢利和回报的问题,这成为微电影当前发展的软肋。微电影的时长限制和网络特性注定不可能在电影院院线生存,与广告的联姻成为必然选择,其实微电影从诞生之初就已经具有浓重的广告“基因”,目前微电影制作的主要资金来源于企业赞助,有很大比重的微电影都是以品牌为核心来讲故事,微电影似乎逃离不了品牌塑造的商业使命。而当微电影跟品牌勾连,所谓创作自由还能在多大限度存在?宁财神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直接表达了对微电影“创作自由度”的疑虑:“品牌给钱,怎么会不把关呢?视频网站也得考虑到播放尺度。”品牌既成全了微电影的创作,也会变成悬在微电影创作头顶上的斯巴达之剑。
此外,“微时代”碎片化的表达方式,让人们能最充分地利用碎片时间获取信息,并享有快捷、浓缩、即时的讯息来源与艺术体验,这种便利与趣味的轻易获得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唾手可得的便利和群体传播的迅速,也容易滋生浮躁、惰性、偏激等问题。现在的人们置身海量微信息和时刻“刷屏”的节奏中,“知情权”得到极大满足,“信息量”也空前暴涨,但也越来越没有时间和耐心去认真读一本书,或者深入思考一些严肃复杂的问题,可谓更多表达,也更多浮躁。
“微时代”简单化、浅表化、平面化的信息传播,自由匿名的表达形式,带来信息真实性的难以确证和偏激情绪蔓延的可能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过:“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这正是微时代各种媒介的“基因缺陷”。时至今日,微博、微信等媒介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舆论正义的伸张,对真实民生的表达,大家都有目共睹,而大量网民的空虚、盲从、偏激、易怒的心理特征也显而易见,不理性的泄愤,别有用心的谣言,商业利益的恶炒,都夹杂其中甚嚣尘上。“微时代”的硬币两面,都为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烙下深深的痕迹。
微时代,且自由,且放恣,且探索,并不完美,却风华正茂,依然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