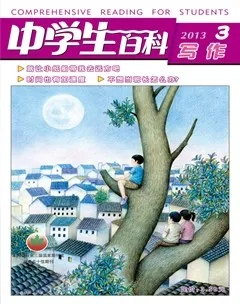一树繁华
一
简生六岁时,跟着卓安回到了拉萨的这个镇上。
据卓安说,这是简生出生的地方。至于到底是不是,简生就不清楚了。她只记得,在更早的记忆里,有个男人抱着自己,轻声唤,国国。有些沙哑有些干瘪的声音里,缱绻着淡淡的烟草味。而这个宽阔温暖的,环抱和缥缈的烟味,某一天的下午,在简生的生命线里戛然而止,那时简生是四岁。
之后简生的梦中总会重复这样的画面——卓安面无表情,面无表情地流着眼泪,一只手拉着灰布的大衣箱,一只手紧紧攥着简生的手,一直走。简生频频回头,看到身后村口的那棵好几人也合抱不过来的老杨树,像是没有根的浮萍,竟一路相随,渐近渐远。
简生记性一向不好,一直都在怀疑,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但如同一枚钉子被血淋淋地钉进身体里的是,六岁那年的那个下午,当她们来到这个石墙砖房的小镇,在红砖裸露的街巷里,在载歌载舞的人们的喧闹中,简生什么都听不到,却清晰地记住了卓安对自己说的话——简生,爸爸不在的时候,不要叫我妈妈!
简生忘了卓安说这句话时的表情、语气,忘了之后她又说了什么,甚至也忘了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反正,那年那天那个下午之后,简生从未叫过卓安一声妈妈。这让简生有生以来第一次佩服自己的记性。
二
卓安喜欢穿藏青色的裙子,摇曳着暗金色碎花的裙裾,因为简生说她这样穿很好看。这样的穿着,让卓安遮掩了仍旧锐利的稚气与咄咄逼人的艳,总算有几分母亲该有的成熟。
卓安,你真漂亮。长大后的简生常常粗着声音模仿男声调侃。她很自豪,即使从来没有爸爸出席过家长会,但这样一个模糊年龄如同月下鲛人的母亲仍足以让她长脸。她没有任何不满足。
但只有简生自己清楚,她装傻,并不是不在乎自己的父亲,并不是不在乎别人的异样眼光。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简生没有勇气去站在卓安面前替她挡下每一把流言的利刃,她怕自己倒下去后反而会彻彻底底地压倒她。她能做的,就是在卓安面前,从未提起过关于那个男人的一丝一毫。
卓安撇着嘴对简生说,简生,你真早熟,跟我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语气里说不上是傲还是悔。简生没注意,嗤笑一声,当然,针对的只是后半句话。
简生来了初潮,她自己从铜盒的存钱罐里拿了钱,往店铺里柜台前一站,伸手指了指货架的第二层。站柜台的是这家店主的儿子,年龄与简生相仿。他顺着简生手指一看,瞬间红了脸,像被人勒住了脖颈。
卓安后知后觉,几个月后看到简生在洗床单才恍然,哦,原来,女儿已经是和自己一样的女人了。可是在简生眼里,卓安从未被称作一个女人,甚至,从来没长大过。她怀简生时才二十出头,到简生出生,到简生站起来和她一般高,从未有过固定的职业,总是背着块边缘满是油墨铅渍的厚重画板,没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或早出晚归,或晚出早归。
受到母亲影响,简生后来选择了美术,并且在高考填志愿时填了美院。
卓安偶尔能卖出一幅画,会摇曳着藏青色的裙裾,拉着简生去吃夜宵,或者两人一起去酒吧坐坐。拉萨当地的酒吧一如百年前的酒肆,木质的氛围,木质的音乐,喧哗而不奢华。酒水不贵,但简生每次带上自家的青稞酒。简生希望有一天,她可以画得比卓安好,而且是好很多。
每天早上卓安会用一把断了两根齿的木梳,和自己泛黄的长指甲,勾着简生黑硬的长发编成规整的辫子。简生坐在镜子前,卓安站在她身后。简生总会想起有人在一棵胡杨下告诉自己,身后是最危险的地方,除非是最信任的人,否则不要把身后留给别人。
那棵老杨树立在村口,三面环着贫瘠裸露的荒草原,外接灰蓝的天,南面仍旧是草根裸露的矮山坡,树边还有块沟壑纵横的大石块,一面被磨平了,上面刻着一个巨幅的“简”字。这应该是这村子的名字。这村子,也许埋葬了自己六年的记忆,也许也埋葬了卓安的青春。
尽管作为一个母亲卓安再怎么不称职,但有卓安在身后,简生一直都很放心。但简生又知道,卓安不可能一直站在她身后,亦如卓安不能陪她一辈子。
三
高考落榜那一天,简生不敢告诉卓安,不是怕卓安会怪她骂她,她倒宁可让卓安打一顿骂一顿,但她唯一怕的就是看到卓安瘦削的身影在高原昏黄的夕阳中默默落泪。她只在六岁那年看到过,却这辈子也不愿再看到。
她站在通往家门口的古巷口,干热的阳光下,只觉得缺氧,在这片裸土,平生第一次有高原反应的错觉,一身的汗,不敢再迈进一步。
头顶上的经幡猎猎作响。
她挣扎着翻过矮墙,溜进了房间,把珠石胸饰和松耳石全翻了出来,都是在每年生日的时候卓安送的。卓安是从小到大唯一会送她生日礼物的人,也是唯一记得她生日的人。我要走。简生神经质地告诉自己,待职业或学业安定下来了再回来,一定会回来。
她背着麻布包跑到街上,伸手抓狂地挥舞了半天却拦不下一辆车,突然感觉包被人猛地向后拉,简生来不及尖叫一声就踉跄着向后倒,感觉到包似乎已经绞着她的胳膊脱离了她。简生不停地挣扎,虽然知道已经无济于事,但一想到包里面都是卓安在每年生日时送给她的点点滴滴,她不甘心就这么被抢走。
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简生的胳膊,使她稍稍站得住脚,然后手的主人又帮她拉住了包,一拳挥向她身后的人。简生愣在原地,只听见身后一记闷响,和随即响起的呻吟。
一个高大的黑影从她身后走出来,逆着阳光,将她拢在他的影子下。你没事吧。他说,我记得你,你以前总是来我家店里买东西。
简生从他影子下走出,借着阳光总算看清了他,想起来了,是那个店主的儿子。
你给我印象特深刻。他说着说着脸就红了,跟简生初潮时去他家店里买东西时一样。
有那么一刻,简生觉得,代替卓安站在她身后的人出现了。
她问他叫什么,他说,阿措。
在藏语里,措,就是湖和海。可以包容一切的胸襟,可以用温柔从背后将一个人淹没的意象。他也是外乡来的,之所以用“也”,因为她一直都不认为这里是她的家乡。简生带他去了自己和卓安常去的那家古铜木质的酒吧,尽管,简生还是执拗地喜欢叫它酒肆。
那天阿措说,简生,你知道吗,你不会走的,因为你妈妈把你勒太紧,几乎见血,她太爱你,而你把你妈妈抓得太紧了。
那天,简生没走。
四
简生和卓安一样,有一头及腰的长发,只是,简生的更黝黑,黑得越发深邃,如同上了漆却仍流动的漩涡,衬得简生的皮肤跳动着麦色的阳光。卓安从发根,撕扯着梳到发梢,说,简生,你肯定把我的营养都吸走了,看,你头发越长越黑,我的就会越干越黄。
简生调笑,你把你的容光焕发分一点给我会死啊。简生笑得很难看。镜子不会说谎,简生看得出来,弹指一挥间,卓安竟逡巡着老了。简生闭上眼不敢去看镜子。卓安,对不起,我就是一条嗜血的水蛭,我吸走的,不仅仅是你的青春……
那晚,简生将熄灯睡觉,突然看到楼下矮墙外站着一个人,在夸张地大幅度挥手。仔细看了下,发现是阿措后,简生咧开嘴笑了。在阅静中,楼下的男生用口型“喊”,我喜欢你。
原来在这个不是故乡的故乡,自己也可以遇见这么浪漫纯情与美好的事。简生也想回一句,但背着光,怕他看不见,就顺手拿了塑料雨衣,写上,我也爱你。然后高高举起。
突然隔壁卓安房间的灯光亮了,简生就看到阿措匆匆忙忙地跑走了。她马上熄了灯钻进被窝。不出所料,不一会儿房间门被吱吱呀呀地打开了,有人走了进来。
卓安钻进了简生的被窝,搂住了简生的腰,把脸埋在简生的发丝里。简生想刚刚卓安可能一直暗着灯站在窗口看,所以决心装死到底。两个人都没有动静,简生突然感觉后颈一阵濡湿,就再也装不下去了。
卓安对不起,求求你别哭了。简生微微侧过脸说。
我就知道你没睡。浓重的鼻音从简生后脑勺传来。
简生一怔。
简生,高考的事我知道,你们的事我也知道,你想走我也知道,简生,我是过来人。只是我在等,等你什么时候跟我说。
对不起。简生咽了下口水,挤出三个字。
听我一句,简生,我从未要求过你什么。他不会真的对你好的,而且你们现在的情况不适合在一起。懂吗?简生。不要说我自私,简生,你是我的,我只有你。简生,你知道吗?我当初就是这么碰到我的那个“他”的,在跟你一样张狂的年纪,也许更小点,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头也不回地跟他走了,我们到别处一起打拼,我天天等着,做梦都想着两个人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到头来,却是和你,两个人独自回来的。你忘了吗,只有我跟你。
那他呢。第一次听她讲有关父亲的事,简生忍不住问了句。
也许还在。也许不在了。
一阵沉默后,简生干涩地开口说,我自己会管好我自己的。
她终于想起来了,小时候妈妈常拉着她在那棵胡杨树下,等着爸爸回家。
卓安也许真的老了,简生想。她既然都知道了自己和她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就应该知道自己会和当年的她一样做选择。
五
刚走到阿措家,阿措的妈妈看到是简生就猛地关了门。简生站在风里,一时语塞,她上前拍了拍门,喊道,阿姨,我找阿描。
门被隔出一条缝,一个中年女人的脑袋伸出来,扯着嗓子喊,你们一家子甲米都有病是吧,怎么你妈刚来闹过你又来闹!阿措都说不认识你们了还来做什么?
简生听完,突然间,忘了,不,是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做什么了。
她站了一会儿,高空中传来布达拉宫遥远而又悠扬的钟声,震醒了她。
她转身,回家。收拾了衣服,提着灰布箱,穿过戈壁,古老的石层上用明艳的颜色勾画了三只眼睛的图腾,看着简生一步一步登上峰顶,用松柏枝燃起桑烟,撒了一杯卓安最爱的青稞酒,决绝地抓起龙达,像要捏碎似的攥在手里,看着灰蒙蒙的天,使尽全身的力气撒向天空中。
一个人的祭祀,不成文的祭祀,只为你,卓安。我放手了。
卓安,你放心,我不会走你走过的路,因为拜你所赐,我是一个人走的,而你当初是两个人走的。但还是谢谢你,让我有勇气放开你,放开这里。
卓安,卓安,我没长大的妈妈啊,要学会照顾好你自己。最后,谢谢你的爱。
卓安正在买菜,想着最近该怎么给简生补一补让她去复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前面有个人提着箱子很像简生,没有身高优势的卓安不顾淑女形象,踮起脚伸长了脖子,可都是满满当当的人头,只好提起藏青色的裙裾使劲往前挤。刚挤过去,就不见了。
六
简生仍在路上,眼角已经被高原的风吹出了细纹,虽然一开始,她只是把这与沿途的荒芜风景无关的旅行,当成人生的一次蓄谋已久的暴走。
一路跋涉似修行,简生第一次觉得自己生活了这么久的生活有多么浓稠,待身心都从那市井与滞古的阴湿小巷里爬出来,她明白了,为什么那么爱美术的卓安一直画不好画。
卓安从离开种着古杨树的地方开始,就一直都把自己关在小巷这个密闭容器里发酵,由内到外,早已经死透烂尽,卓安要是想复活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从里面出来。
简生背着边缘满是油墨铅渍的画板,到处走,到处画胡杨,希望其中一棵,就是自己梦中的那棵,也是卓安离开的那棵。
她想找到离开前的卓安。
她再次梦到卓安一脸的泪拉着她,一路走,她一回头,那棵老杨树渐行渐远,慢慢变成视野里的一个黑点,最后恍然跌落。醒来时竟也是一脸的泪。
第二天路过一个荒废的村口,裸露的土层中卧着一个风干的树桩,旁边立着一块石头,上面写着一个字“简”。
(指导老师: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