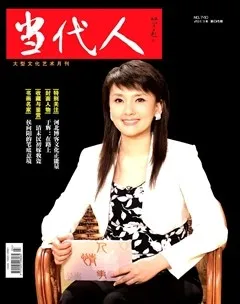汪曾祺与张家口
1958年10月的一天,京包线张家口段一个极小的火车站——沙岭子站,一列暗绿色的客车在甩下十几个乘客后,又缓缓地向北蜗行而去。这十几个乘客下车后,很快便如倦鸟一样各自奔向自己的巢穴,站台上只剩下一个孱弱而忧郁的中年男人。良久,他抬头看了看阴霾的天空,开始背起行李走进候车室,向售票员询问此行的目的地——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随后,他走出候车室,依照人们的指点穿过铁路向农科所走去。
他就是著名作家汪曾祺,那一年,他三十八岁。
汪曾祺一生与五个地方结缘,张家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因为其他四个地方都是他成长、求学、生活、工作的地方,而张家口却是他劳动改造的地方。1958年10月,因为所在的文联系统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被错补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改造。两年后他虽然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改造,但由于原单位不接收,只得暂时留在所里协助工作,直到1962年初才调回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结束了在张家口近四年的特殊生活。
我想,汪曾祺对张家口这个地方的感情一定是颇为复杂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曾祺以《受戒》等系列小说开始享誉文坛,而他的散文创作也进入井喷的状态,其中直接抒写张家口的散文就有《随遇而安》、《沙岭子》、《沽源》、《马铃薯》、《口蘑》、《坝上》等多篇。在这些散文中,他以一种悠闲甚至是轻松的笔调描摹张家口的自然风物,考证马铃薯的种类流传,叙写口蘑的品类口味,即使是那些直接写劳动改造生活的文字,也很难看出“右派”大山重压下的那种紧迫的心态,传达的也并非都是沉重和苦闷。
对于在张家口近四年的生活,他在《自报家门》中写道:“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在另一篇散文《随遇而安》中,他甚至表示“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因此,他感激张家口三年多的时光对他的给予。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天真地以为汪曾祺当初的生活会是如此轻松。事实上这不过是事过境迁之后的一种轻松回望,是苦难过后成为财富论的一种翻版罢了。当年处于苦难中心时的汪曾祺断然不会有如此轻松的心态。正如他在《随遇而安》中所讲“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戗。”这样的转变不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是不行的。虽然他事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颇引以为自豪地称“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跳。”对于汪曾祺来说,比之肉体脱胎换骨的痛苦,精神上的郁闷和无助更沉重百倍。1959年3月,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去世。汪曾祺手捧弟弟妹妹发来的电报,心急如焚,悲痛难耐,泪流满面。父亲生前他没能床前尽孝,他多么想回家与父亲见最后一面,送父亲最后一程。但不久前发生在一个被改造同伴身上的事,让他踌躇不定。这位同伴家中的亲人死了,想回去奔丧,便向领导报告。领导却说:“死了。死了也好嘛,你可以少背一点包袱。”得知逝者已埋了以后,这位领导竟然冷酷地说:“埋了就得了———好好劳动。”汪曾祺明白,自己同样是戴罪之身,因此他最终没敢向领导提出回乡奔丧的请求。他只能把悲痛埋在心底,在夜色苍茫之际,跪在沙岭子高高的山岗上,面对家乡高邮的方向,一洒自己的思亲之泪,向父亲向家人表达自己深深的哀悼和亏歉之情。
汪曾祺在张家口生活了近四年时间,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他心中的苦楚,是难以与人言说的。尤其是前两年,他右派帽子未摘,一方面遭受着肉体的苦痛,另一方面还要背负着精神的重压。经济上的困顿自不必说,而右派前途的未卜、父亲的去世、故乡亲人生活的悲惨都时时挤压啃啮着他脆弱的心。而在右派帽子摘除后,他虽然有一种轻松感,但由于原工作单位不接收他,他只有继续呆在农科所协助工作。在《马铃薯》一文中,他曾记录下当初他的那种情绪:“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可以谈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右派生涯结束后,他原本可以回京与家人团聚,但没有单位接收,他便只能还如失群的小鸟一样,孤单地在张家口飘零了一年多。个中的滋味,肯定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寂寞可以形容的。
1983年,汪曾祺应张家口市文联之邀,给当地青年作家讲课,期间重返沙岭子,然而时隔二十年,一切已是面目全非。“这不是我所记忆、我所怀念的沙岭子,也不是我所希望的沙岭子。然而我所希望的沙岭子又应是什么样子呢?我也说不出。”而对于他生活过几个月的沽源县,在《沽源》一文中,他心情复杂地表示:“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机会到沽源去了。”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再能回去过,沽源在他的印象中永远停留在马铃薯、口蘑、低矮的城墙与多变的天气上。
往事或许并非不堪回首。张家口作为汪曾祺生活过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对于他来讲已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融有他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的,留有他生命气息的一块生命之地。在这块土地上,他犹豫过、彷徨过、悲伤过、失落过,他也思索过、感受过、憧憬过,他一生最坎坷的几年是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张家口因此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分量最重的一部分。
尽管这片土地在他的生命中,往往是与苦难与坎坷与命运的不济相连,但恰恰是这块土地接纳了他、包容了他、陪伴了他、慰藉了他,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曾是复杂的是爱恨交加的。而当时光的荏苒使历史成为云烟,曾经的苦难终成为一种人生的财富时,张家口这个地方也最终化作一种坚硬的血液融合到他长流的生命和文学的血脉中。
张家口其实距离北京仅仅有二百公里,是庇护北京的后花园,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许多京、津、冀的游客都把之作为休闲度假的首选之地,在他们的眼里,张家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一个能够消解他们疲倦焦虑情绪的地方。汪曾祺笔下只有罪犯“发往军台效力”的沽源也以五花草甸等优美的自然景观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人。以汪曾祺在张家口生活的年代计,历史的册页已经翻过去了半个世纪。回首过往岁月,汪曾祺曾发出过“我只觉得这一代人都糊里糊涂地老了。是可悲也”的感叹,也曾发出过“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的希冀。社会发展了,时代前进了,我想,如果作家本人还活着的话,能够重回张家口,一定会感触良多。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历史可以重写,我多么希望汪曾祺与张家口的缘不再是由于沉重的政治风暴,而是出于这个地方固有的善和美,正如现在那些来张家口休闲度假的人们一样,所感念的是这片土地粗犷、辽远、包容、大气的美!
(责编:郭文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