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蔚萝川上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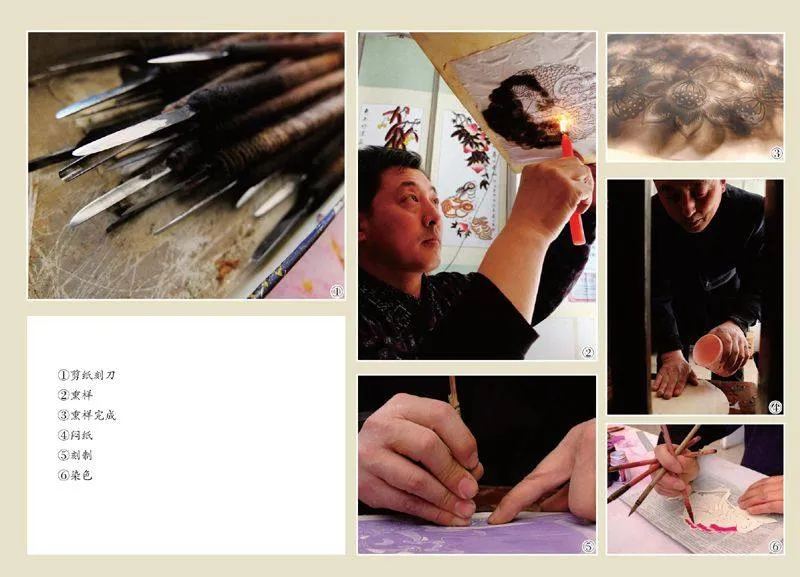
2012年腊月年尾,我在第一次前往蔚县的客车上,翻开了一本看上去很枯燥的理论书籍《壶流河畔的点彩窗花文化》。只是想临时抱佛脚,建立起对蔚县剪纸的大概认识,连作者名字都懒得瞟上一眼。
未曾想到,从翻开第一页开始,我的目光就被紧紧地拽住了。任凭汽车在山路上颠簸,光影明灭,都不舍得停歇分毫。作者用独特的视角,从蔚县自然环境造就的特色物产,到蔚县历史中文化冲突和交融形成的独特个性,再回到这方水土养育的人们的生活,讲述了蔚县剪纸特色形成的渊源。整本书视野宏大,脉络清晰,资料详实,并且文采飞扬,非常好读。既有知识的厚重,又不乏文学的优美,让我印象深刻。这本书带给我的激动,也转化为对作者强烈的好奇,合上书,我记住了这个名字——田永翔。
经过一番寻找,机缘巧合,我们找到了田永翔老前辈,并在他简陋的房屋里倾谈了一个上午,听了一节颇为震撼的课。
中央美院的薄松年教授在给冯骥才先生等人的信中曾经说过:“田永翔对蔚县剪纸的研究,其水平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他的研究远不是在书桌前抓脑袋琢磨出来的,而是耗尽一生精力,扎扎实实地到民间收集大量一手资料得来的。他先后三次,进行了蔚县剪纸的普查。到过一百多个村庄,采访过七八百位艺人,收集几千幅剪纸作品,写下几十万字的笔记。这些,后来成为蔚县剪纸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蔚县窗花》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国家示范本的《中国剪纸集成·蔚县卷》以及《壶流河畔的点彩窗花文化》等专著。
如果只对剪纸进行研究,或许给不了他如此广阔的民间文化视野。他不仅关注蔚县剪纸,还于1988年编辑完成66万字的《蔚县民间故事卷》,1999年编辑完成了15万字的《蔚县歌谣卷》,2000年编辑完成《蔚县谚语卷》和《蔚县楹联卷》,2008年发表了21万字的《蔚县地方剧种概说》。2012年,编著出版《中国蔚县民俗文化集成》(10卷本)。蔚县这片民间文化的厚土,成就了田永翔在蔚县剪纸研究中所达到的高度。
理论研究是件非常讲究逻辑的工作,所以,在学术性和可读性两者之间便很难平衡。这也是极少有理论书籍既专业又好读的原因。而在田永翔广博的爱好里,还有份对文学的热爱。他曾经一人连办三份文学刊物——《壶流浪花》、《蔚县文艺》和《今日蔚州》。在后期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到处求人,筹措经费,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坚持办了18年之久,发刊100多期,直到1999年他病倒在报社。他像园丁一样,浇灌了蔚县这片险远荒凉土地上无数灿烂的文学花朵。
为蔚县文化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田永翔的一生却是坎坷艰辛的。他从张家口艺专戏剧系编导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剧团,不久剧团解散;分到报社,报社撤编;分到学校教学,专业不对口。各部门拿他踢皮球,最后只好回家务农。拿笔的手,从此攥起锄头,与祖母相依为命,为稻粱谋。村里照顾他身体孱弱,给他份“拾粪”的轻差,从此与街上的骡马粪便“相见欢”。他说:“拾到一担粪时的那种惬意和快感vC06nn2o8zl9Q0BtelON/A==,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个中辛酸,常人无法想象。1979年结婚时,他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只好和妻子到西门外护城河边,在城墙根下,用捡来的破城墙砖垒了两间小房。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一家还住在那个房院里,房子在政府帮助下已经翻修,但周边环境之差,却比当年更甚。他住的地方,多给出租车钱,司机都不愿去。
后来,田永翔的才华被发现,重回文化岗位工作。然而,他的研究著述,依然是一条寂寞而艰辛的路。《蔚县窗花》,历时23年才得以出版;《蔚县民间故事卷》,一度缺乏印刷经费,田永翔为了筹措资金,想尽一切办法。他说:“这不只是工作任务,而是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能留下几个浅浅的脚印。”蔚县的一位干部说:“田永翔令人尊敬,但他走的路谁也不愿走了。”
初次到他家见面的时候,七十五岁高龄、身体孱弱的田永翔走在前面带路。在满是烂泥的曲折小巷里,他颤颤巍巍蹒跚前行,留下一串细碎的脚印。这脚印不止为我们指引了方向,也踩出了我们心中的榜样——一种对民间文化事业的热爱和担当。
他一直住在破败但坚固的城墙外,而这高墙外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土地。或许,田永翔一生经历的苦难,都是为了让他从生他养他的蔚萝川大地上脚踏实地地走过,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