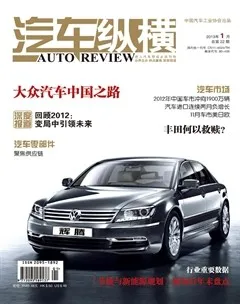《车记 亲历·轿车中国30年》节选十一
“今天的新闻便是明天的历史”。连载近一年的《车记》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即将圆满划上句号,但汽车中国的故事还在续写。2013年,距离中国汽车工业1953年发端于一汽倏忽60载。从敲敲打打造出自己的第一辆“解放”卡车到成为世界汽车第一大市场,这些年中国汽车的一切变化得太快,太突然,《车记》用文字载着我们对岁当甲子的中国汽车业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站在历史的节点上,展望汽车业的方向。

“站在地上的那条腿”
一本书写到最后一节,似乎该谈谈中国汽车做大做强的愿景。但是想到那是一个“未来时”,并非我所能够预见。关于未来,还是国家汽车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最具权威,我在这里只给中国汽车的发展提几个忠告。
2009 年6 月,我应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之邀参加花都汽车论坛,花都论坛当年曾经因为两位权威人士何光远和龙永图的“何龙之争”而备受业内关注。这次论坛,我是被邀请作主题发言的三个嘉宾之一。就在这次发言中我第一次提出,在电动车成为举国体制的热潮中,绝不能放弃在传统汽车技术创新方面对全球领先水平的追赶。
发言中,我大声疾呼:新能源车研发和传统汽车的优化,是中国汽车业做大做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新能源车的研发是抢占明天科技制高点的前哨战,是必须迈出去的一条腿;优化传统汽车,对节能减排最立竿见影,我们必须靠这条腿站在地上。
真理有时候就是如此简单:如果依靠“汽油直喷+ 涡轮增压”等技术降低油耗20% ,以中国年产汽车1000 万辆计,不就等于每年生产了200 万辆零能耗、零7jUQZE64dL9HVl3sORkiTw==排放的汽车吗?社会效益之大是任何新能源车在可见的未来难以实现的。
而由政府层面大张旗鼓主导的电动车热,无疑冷落了中国汽车业在传统汽车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国家863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第一批课题的4.13 亿元中,用于节能环保高效内燃机的研发费用仅为1600 万元。
历史是一面镜子。制定发展战略要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大轰大嗡的结果,往往是时机的丧失和资源的浪费。
上世纪80 年代初,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煤炭的运力低下,造成沿海地区电力供应短缺,工厂一周“开三停四”。而当时石油炼制中产生的大量重油没有出路,于是由国家经委出面,调拨技改资金,在全国大搞锅炉“煤改油”技术改造。有专项资金撑腰,各地争着把燃煤锅炉改成烧油。谁知不到一年,重油从无人问津变得供不应求,电力和动力行业又成无米之炊。结果又是国家掏钱在全国搞了一次“油改煤”的折腾,损失至今无法计量。

近一点的例子是1998 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谈到吉林等产粮省大量陈化粮无法处理,主持会议的国务院领导人当场拍板,进行用陈化玉米制造乙醇代替汽油的试验。我当时在场,还写了报道。试验取得成功,陈化粮积压得到化解,玉米造乙醇却在全国产粮区遍地开花,堪称一次小的“新能源”革命。然而乙醇产量大了,却引发了人与汽车争食玉米的窘境,甚至成为一场社会伦理的危机。玉米乙醇终被叫停,大量生产设备建成即告闲置。
刚刚看到一则报道,2011 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拉闸限电此起彼伏,煤炭净进口已成定局。我就有些担心,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划,2015 年中国生产150 万辆电动车,脆弱的电力供应如何能够承受?
中国汽车企业的主力是国企,政府的态度就是风向标。如果官方押宝电动车,加之巨额补贴,企业从趋利的本能出发,势必会忽视传统汽车节能减排的自主创新。一旦国外厂商新一代低成本、低油耗的汽车称雄全球市场,中国汽车再次拉大和全球汽车业的技术差距,痛失得来不易的市场主导权,那才是中国汽车的悲哀,甚至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保护”是个坏东西
就在这本书写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新浪汽车的编辑打电话告诉我,某官员在一次论坛上提到,应该考虑逐步放开对汽车合资企业50% 对50% 的股比限制,请我谈谈看法。
第二天上网,对放开股比一片喊打之声。批判者中有汽车业官员、国企人士,也有长期关注汽车的“意见领袖”。批判的主旨不外乎:中国自主品牌还在初创期,国家应该给予保护与扶持;放开股比底线,中国汽车将受重创;更有人惊呼:中国汽车危在旦夕。在新浪电话采访的人士中,我是唯一无保留的支持者。
其实,这种反应在中国汽车业中也是一种常态。撇开民粹思潮影响不说,对于在国民经济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汽车业来说,保护的大旗曾经高高举了几十年。出发点光明磊落,实行得也十分彻底,观念绵延至今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中国汽车的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保护”是个坏东西。“保护”出“弱质”,竞争出强手,依赖“保护”,中国绝对成不了汽车强国。对于“股比限制”这一制定于1994年的汽车保护措施,我以为早该冲破。目睹中国汽车30 年,对“保护”的弊端体会得特别深刻。从诞生之日起,汽车产业就纳入国家的“一级保护”之中,进口轿车严格审批,还要征收最高达220% 的进口关税。结果,直到1984 年,年产两三千辆的上海牌,发动机功率与整车水平也与被拷贝的50 年代奔驰车相去甚远;年产不到300 辆的红旗,因耗油高、性能差,而被中央下令停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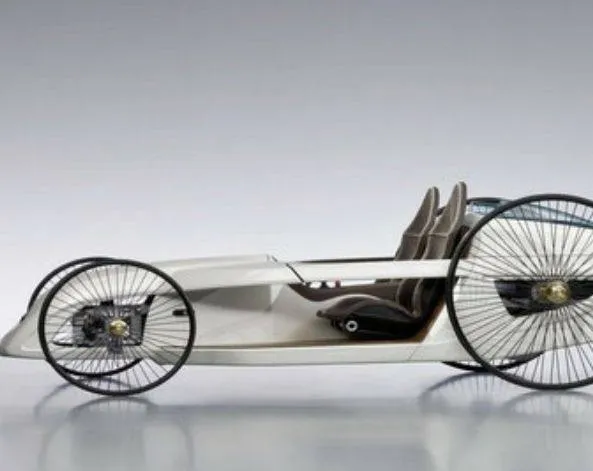
上世纪80 年代初,把外资引入中国汽车业,在当时的决策部门看来是严重犯忌的事。如果不是邓小平拍板“轿车可以合资”,借用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从头再造中国轿车工业,谁也迈不过“保护”这道坎。上世纪90 年代末,国家发文“重点扶持”三大轿车合资企业,并设立行业“准入”的高门槛,保护的结果是合资产品车型陈旧,价格居高不下,却依然供不应求。被挡在门外的吉利、奇瑞、华晨等自主品牌长期拿不到“准生证”,命悬一线。当时业内人士公开说,“回去补竞争的课,时间搭不起,国有资产输不起”。为保护“国家队”,连“陪练”也要斩尽杀绝。
2001 年,中国入世前,汽车业笼罩着一片即将“全军覆没”的愁云。入世谈判历时15 年,一个最艰难的话题,就是给30岁的中国汽车业以“幼稚产业”的地位,从而获得“缓冲期”的保护。入世十年中国汽车的巨大飞跃,揭示了一个朴素的哲理:每一次主动,或者被迫放弃“保护”,脱下一层沉重的“防弹衣”,中国汽车业就迎来一片光明,涌现出一批禁得起摔打的成功企业。

允许合资,中国轿车业才跨上国际水平的高标准,缩短差距20 年;不是冲垮自主品牌的“准入”门槛,恐怕今天自主创新也提不上日程;不加入世贸,和跨国公司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与合作,成为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甚至连想也不敢想。说到汽车合资50%∶50% 的股比,最早起源于中外双方的博弈,甚至磨合。有趣的是,上世纪80 年代,合资企业前途未卜,摸着石头过河,都希望对方多担一份责任和风险。上海大众建立之初,德方曾主动放弃销售权。50% 对50% ,是双方达成的一种平衡。在外方看来,股比再高,没有中方的支持,企业也无法生存。几个外国人面对几千中国人,规避“大象踩了小老鼠”才是当务之急。50% 对50% 的股比,后来被1994 年第一版《中国汽车产业政策》固化,也作为后来入世谈判中中方坚持的对中国汽车的保护条件。

16 年过去了,中国汽车工业和全球汽车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讨论放开股比,甚至允许外商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绝非就是“亡国”大事。揣测国外汽车在中国建立独资企业的意愿就是绞杀自主品牌,我看大可不必。“阴谋论”看起来好像是打人家,实际是打自己,是挖自己的墙角。PSA 亚洲区总裁奥利维就表示赞同放开股比限制,他的理由是:50% 对50% 的股比对合资企业来说,效率是最低的,在战略制定、决策等方面都要反复讨论、摩擦,会因此错失市场良机。对于这种思路,我看不出有什么阴谋。
我以为,一个企业的投资运营,自有它的逻辑和选择。有趣的是,戴尔、西门子、诺基亚、宜家在中国独资设厂,中国的电脑、电子、手机、家具业并没有全军覆没,竞争力反而蒸蒸日上,为什么汽车业还非要撑一顶股比保护伞呢?
即使近年来,一些国企在国内竞争中表现得体质羸弱,不是国家保护太少,恰恰是保护太多。中国作为汽车第一产销大国,有几个外商独资企业同台竞技,吉利、奇瑞、华晨、长城、比亚迪、荣威、奔腾都绝不会垮台,只有进一步的开放,中国汽车才能在世界杯级别的大赛中成为汽车强国。
且不说,在全球化的市场,吉利百分之百控股地收购了沃尔沃,瑞典人也没有骂政府卖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不再是国内联赛,而是进军“世界杯”,国际规则人人平等。不能只许中国队进球,不许外国队射门。未来的中国汽车业,必然有中资或外资的独资企业,有中外合资企业。合资企业中各种股比并存。对于汽车业这样一个全球化、竞争性产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汽车大国,这应该是合理的格局。不能如此,妄谈汽车强国。
后记
恍若隔世
汽车时代,中国在全世界进入最晚,进程最快。尝试引进合资生产轿车,不过30 年;决策建立轿车工业,只有20 年;政府认可轿车进入家庭,刚刚10 个年头。
今天的年轻人何曾知晓:半个多世纪前,由于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私家车在中国严遭禁绝;直到上世纪80年代,筑起世界最高关税壁垒的中国,全年轿车总产量却不如国外汽车厂一天的产量。
这一切,是30 年前,中国轿车故事的起点。那时候,如果告诉一个中国人,你的孩子们将获得享受轿车文明的权利,中国会成为全球第一的汽车产销大国,似乎百分之百地会被认为是痴人说梦。30 年,真不算长,蓦然回首,却恍若隔世。
一切变化得太快了,来不及沉淀,来不及反思,泥沙俱下,黑白混淆。需要有人从头至今作一个梳理。
我的记者生涯的起点,正好和中国轿车创业的起点重合。一开始,我就得以走近中国汽车业的决策层和骨干企业,亲历了30 年中国轿车发展的诸多节点和全过程,了解到许多外人难以获悉的真相,30 年不间断的参与是一种幸运。
1982 年,中国汽车奠基人饶斌对我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五年前,我开始动笔写这部中国轿车的历史,似乎这是我人生必须要作的一个交代。
我以为,在中国,决策和主管部门的高瞻远瞩成全了轿车产业从无到有的高速发展;同时,这些部门的相互掣肘和屡屡失误,也带来一次次折腾和曲折;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是以成败论英雄,汽车产业终归从一个计划经济的“活样板”, 蜕变为中国最具市场化特色的支柱产业,即使在全球金融海啸最激荡的时刻,也那么给中国经济挣脸。
然而,纠结,贯穿中国轿车业30 年起落的全过程。
是闭关锁国,自力更生;还是抓住国际形势的转折机遇,以开放促发展?在合资企业中,是七斗八斗,同床异梦;还是合作共赢,生成本土技术和开发能力?是高筑国企的围墙,扼杀草根对手;还是放开“准入”门槛,给自主品牌生存与竞争的权利?是满足于在入世谈判中为中国汽车争一个“幼稚产业”的保护地位;还是按照世贸规则,鼓励中国企业在“与狼共舞”中打造航母?是全面跟踪国际节能减排和新能源领先技术,在学习中寻求突破;还是大轰大嗡,搞自欺欺人的“弯道超车”,且不说,“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今天在中国不乏子孙,以引进外资和技术为起点的轿车业,一直是他们施展“大批判”拳脚的功夫场。历史,总是裹挟着大量泥沙滚滚向前。
轿车是什么?在中国,轿车是政治、是技术、是经济、是权利、是财富、是文化、是情人,是成百倍提升出行距离的“飞毛腿”,是社会财富滚滚而来的流水线,是全球化的经典产物,是民粹主义的精神寄托,是污染和拥堵的罪魁祸首,是引领全球新能源的希望,是自主品牌自主创新的体现,是贫富不均官民对立的标志物。中国鼓励轿车私人消费不过10 年,轿车突然以每年1000 万辆的速度出现在身边,爱它、恨它、用它、骂它、鼓励它、限制它,中国人一时还找不着北。
本书以编年史和一章一个主题的结构,记述了不同时期这些纠结的载体——事件、企业、人物的故事。这是一部“私家版”的轿车史,力求还原真相,只是一家之畅所欲言,没有未来官方史写作者所面临的必要的平衡和羁绊。
能够完成这本书,是中外汽车业、媒体界许多前辈、朋友和年轻人鼓励和支持的结果。在写作过程中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回忆、判断、史料和图片,也有琐碎的事务性帮助。这是一个太长的名单,恕我不一一记下他们的姓名。但是我不得不提到一位逝去的朋友,原上海大众公关总监曾家麟,是他推动上海大众出资在《汽车人》杂志连载了本书的初稿,让我在2010 年的一年连载期内坚持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我很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