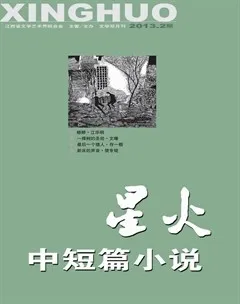一个简单的故事(创作谈)
存一榕,男,哈尼族,上世纪60年代生于云南省普洱(宁洱)县一个名叫南腊的小山村,在《民族文学》《中华散文》《文艺报》《中国散文家》《边疆文学》《安徽文学》《星火·中短篇小说》《滇池》等报刊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作品被收入多种选本。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现居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
一个简单的故事当然不可能达到深刻,但深刻往往是由简单构成的,也可以这么说,具有深度的东西,通常都要用简单的方法来阐述或隐喻。我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勐拉河镇一个叫曼丫大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沟深坡陡,整个勐拉河镇均属于典型的穷乡僻壤。由于国家出台了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政府收缴了当地猎人的枪枝,使祖辈生活在这里的世袭猎人,也只能弃枪从事农耕维持生计。于是,没了天敌的野猪在森林里朝气蓬勃地生儿育女,繁殖极快,总数迅猛增长,它们频繁窜出山林去毁坏当地山民种植的庄稼,给当地山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农民们怨声载道,经常到镇政府,甚至到林业局、县政府抗议,要求政府提高野生动物损害庄稼的赔偿标准。
故事中的主角艾肯特算得是一个世袭的猎人,但他的老父亲,曼丫大山名震一时的猎人艾伦出于对因果报应的迷信,并没有把自己的狩猎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儿子。艾肯特算得是自学而成的一名猎人。在他正值壮年时,由于国家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得不交出了自己手中的猎枪。有一天在接待几个上访的村民时,赵镇长突然想到:既然野猪繁殖这么快,何不把它当作一种资源来加以经营?以保护山民的利益必须合理控制野猪迅猛增长为由头,赵镇长借机获取各种野味,笼络各级部门的领导,获得某些现实利益,以摆脱镇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于是,艾肯特获得了护林员的合理身份,实则是镇政府精心安排的一名专门为镇政府筹措野味的猎人。可以说这是一篇以打猎作为基本载体,围绕着猎人、猎物之间的关系,而营造的一个有关欲望与权力的故事。小说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多重解读,尤其是社会潜规则解读,以展示社会各色人物被欲望驱使的无奈。在这里打猎这一活动构成了一种隐喻,人打猎,猎取猎物,自以为是猎人,但换一个角度,你可能也是别人的猎物。小说肯定要与现实有关,却又不能止于现实。可能,这就是我试图想要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