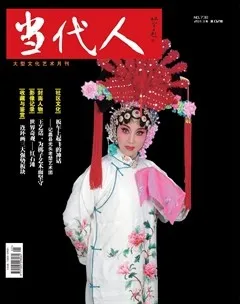水城 古城 太极城


走近广府,水塘便多起来,一滩滩,一处处,水光潋滟,亮得刺眼。走近广府,气息愈发温润起来,水汽蒸腾,呼吸畅快。广府古城杨柳依依;护城河上波光粼粼。水圆城方,占地21.5平方公里的永年洼,环绕和滋润着这座千年古城,使它显得越发古朴厚重。晨光中,太极拳演练者的身影一现,安静的小城便鲜活了起来。
一
说到广府的美,离不开水。
“双水绕城”是广府城的特色,滏阳河与护城河像两条“项链”环绕着广府。此外,这里河网密布,纵横交错,滏阳河、支漳河、牛尾河、溜垒河等汇流于此,因海拔仅41米,使得广府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景色半城湖”的旱地水城奇观,号称“北方小江南”。
同行的广府生态文化园区管委会副书记卢相文,个子不高,文质彬彬,说起广府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我们先到了一个码头,一眼望去,一人多高的芦苇郁郁葱葱,透过芦苇极目远眺茫茫无边的洼淀,大有苍茫云水间的感觉。“上船吧,去感受一下永年洼的魅力。”卢相文招呼着,我们乘上一艘快艇。引擎发动,水声哗哗,芦苇摇曳,恍惚间似乎到了华北最大的湿地白洋淀,又好像来到梦里水乡周庄。“永年洼是华北三大湿地之一,白洋淀因为红色革命历史和孙犁先生的名篇享誉海内外,衡水湖主打生态牌正在开发旅游,我们二者兼备,既有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拥有国内唯一的北方旱地水城的自然环境,广府一定会后来居上。若从春秋时期曲梁城算起,广府有2600多年的历史啦……”卢相文的话语充满了自豪与希冀。船往南行,清风乍起,十里荷塘上,拖着绿裙的“舞女”们,翩翩起舞,美不胜收。“2012年7月份,200多个品种的荷花齐放荷园,一年一届的荷花节场面可大了,千帆竞过,荷香满船。若是想寻静,还可傍晚来,听渔歌唱晚,看落日映荷,月夜泛舟,寻一寻李清照的感觉——‘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听卢相文吟诵着千古名句,闲适悠然之情渐渐在我们心底升腾。
船掉头回驶,又是芦苇荡,令人迷乱,“哪里是方向?何处是尽头?好似迷宫啊!”我心生疑惑,禁不住问出了口。“一会儿上了岸,便会知晓了。”卢相文神秘地一笑,故意把话头儿岔开,“看,那可是广府城最经典的摄影景点啊!”顺着卢相文指引的方向望去,一行白鹭飞起,白水碧苇间,广府古城巍峨的城墙若隐若现,眼前浮现出“水远烟微,一点沧洲白鹭飞”的图景。
船行至芦苇深处,忽见一只翠鸟飞来落在一根芦苇上,婉转而歌,一双眼睛直视着我们,好像特意为我们献歌。“鸟和游人都成了朋友啦。这里生态好,鱼虾多,是翠鸟的首选家园,它们哪舍得走啊!”卢相文说,“绿色生态”已经成为广府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新方向。近几年,许多绝迹多年的野生鸟类陆续飞回来,野鸬鹚、白鹤、翠鸟、野鸭等十多种北方罕见的鸟都来这里栖息生活。据说,永年洼还生活着上千只白鹭,在这里常可观赏“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景色。
弃舟上岸,卢相文m0dz7pWiAoph9pJ2T73f8Q==引我来到一张巨幅照片前,说里面有玄机。后退十几步远观,一个巨大的由淡蓝色水域构成的繁体“龙”字闯入我的眼帘,同行的人说还像一个繁体的“赵”字,争论四起,卢相文却在一旁如智者般微笑着揭开了谜底,“你们都猜对了。历经时代变迁,谁也没有料到天然的芦苇荡,在不经意间把永年洼水域分割成了一个既像繁体的‘龙’字,又像繁体的‘赵’字的巨大的汉字形态。当地人因此称广府是古赵国的龙脉和水脉。”如此神奇的自然造化,给人恍如隔世的感觉,这或许就是道法自然吧!
二
若论广府的“古”,自是离不开广府的古城、古迹、古民居。
广府古城,春秋时期称曲梁城,距今已有2600多年。自西汉起,为历代府郡治所或州县治所。隋末唐初,夏王窦建德曾在此建都,当时为土城,周长“六里二百四十步”。元朝侍郎王伟做郡守时,将土城扩大;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知府陈俎调集九县民工,历时13年,将土城修砌为“九里十三步”(周长4522米)的砖城,即现在广府古城的规模。
自古吊桥遗址上重修的东门桥一路行来,桥旁有一尊石牛塑像,讲述着“水漫广府”的美丽传说。广府古城也称卧牛城,传说四周城墙的拐角处各藏有一头神牛,护卫着广府城不被水淹。有一年,一只老鳖精率领着虾兵蟹将来淹城,四面大水,浊浪滔天,百姓危难。这时四角的神牛“哞哞”大叫,城头呼呼上升,水涨十尺,城高一丈,河水始终漫不过城墙,保护了全城百姓的安全。
神牛护城的传说,流传至今。民间文学运用另一种夸张的形式记录和证明着广府古城的坚不可摧,其实真正护卫古城免遭水灾和战火的,不是所谓的神仙,而是它科学的设计和森严的军事防守设施。约5公里长的护城河,最宽处达一百多米,形成了第一道防线。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知府崔大德为防水患和战事增修城外城——即在四个城门外修筑瓮城,这便是第二道屏障了。只要诱敌深入,关上城门就会上演“瓮中捉鳖”的好戏。此外,在广府长达约4.5公里的古城墙上,防御垛口就有1752处,既可全方位瞭望,也可多点攻击敌人,这可谓第三道防线。广府古城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完备与严密,堪称我国古城中的典型代表。
从东门阳和门入城,首先进入东城门外的瓮城,城高墙坚。东大门有两三米高,一颗颗巨大的铁皮铆钉,定格和记录着历史的风雨。这两扇城门是明代城门,距今已近500年的历史,现在还可以用。
绕过城门,拾级而上,马道上的马蹄印,让人想起古战场上军旗猎猎,金戈铁马的场景。登上城墙,绕城一周,古城全貌尽收眼底,青砖灰瓦、古香古色的民居鳞次栉比。现在城内面积1.5平方公里,人口约2万人,“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道拐拐弯”的街巷格局,依然如故。城外有弘济桥、毛遂墓、西八闸水利工程等遗迹。广府现存18处古宅院,最重要的当属杨式太极拳的创始人杨露禅和武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武禹襄的故居了。
在广府城东不远处,有弘济桥飞架滏阳河上,此桥始建于隋代,堪称赵州桥的“姐妹桥”。千百年来岁月的磨洗让古桥愈发苍劲古朴。桥下,偶遇一老妪,濯衣河边。询问:还记得桥下的繁华吗?回答:儿时,河上船只不断,纤歌此起彼伏,多是往来天津卫的运瓷器的商船。一同来的卢相文说,瓷器易碎,是不好走陆路的,滏阳河蜿蜒近千里融入海河,顺流而下直达出海口天津,定窑、邢窑、磁州窑的瓷器精品,便沿着这条水道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毛冢高峰”是广府“平干八景”之一。战国时期,一代名士毛遂封地于此。后百姓为其筑墓,留下他“脱颖而出”“歃血为盟”“舌战群雄”的历史记录。毛遂墓位于古城西南大堤内,被洼淀包围,我们只能隔水揖拜英魂。“一剑横阶气若何,平原轻侠尽消磨。铜盘热血警蛮楚,锥颖英魂壮滏河。”面对静静的滏阳河,历史的风云起落,终归于平淡。
三
寻广府的“风骨”,当然应属太极。
“太极风骨”是广府的精神。走在广府街头,上自鹤发老者,下到黄口孩童,若论太极拳,人人有奇招。太极,已渗透到广府人的骨子里、生活中了。
广府城外南村有一座清雅的灰砖四合院,这就是一代太极宗师杨露禅的故居。“杨露禅的故居拜谒者遍及世界各地,多是太极武学爱好者。不久前,著名武打演员李连杰也曾来此专门拜祭。”卢相文介绍道。
我对太极拳的记忆,还得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曾有一部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举国上下习武之风盛行。在这股潮流中,另一部电影《神丐》随后走红,电影以太极宗师杨露禅为原型拍摄,又引发了学习太极拳的风潮。其实,我对太极拳最完整的记忆,是来自儿时阅读的一套三本的小人书《偷拳》,小人书图文并茂地讲述杨露禅三下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的经历。历时14年,杨露禅扮乞丐,装哑巴,偷学拳艺,最终感动老师陈长兴,将他收入门下,学习太极拳。回归广府后,杨露禅开创了举世闻名的杨式太极拳。后来杨露禅北上京师,被瑞王府聘为王府拳师,期间挫败了许多来访的较量者和各王府拳师。一时间,杨露禅名震京华,被京城的武术界誉为“杨无敌”。
“手捧太极震寰宇,胸怀绝技压群英”,卢相文指着杨露禅故居正房悬挂的对联解释说,这是清代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观看杨露禅比武后,亲手题写的。翁同龢赞叹杨氏太极——“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之浑圆一体也”。此后,太极拳名噪神州,誉满华夏。
杨式太极拳的第五代传人乔振兴正在故居表演,一袭中式黑衣,一根三米多长的太极枪舞得虎虎生风,一改太极拳稳健静雅的常态。乔振兴称自小追随杨式太极拳大师傅宗元学习拳艺,至今已有47年了,如今他的磕头弟子已达几十人,来自浙江、吉林、湖北、山东等全国各地。“全世界练习太极拳的有两亿多人,其中80%练的是杨式太极。但是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什么人都可拜师的。道德是习武的第一道门槛,也是关键。”乔振兴谈起他所理解的杨式太极的精神内涵是:“和谐”。区区两字,已足以让人领悟到大师的境界。问到杨式太极拳的武学真谛,乔老师指了指祖师爷画像两边的一副对联:“拨千斤不名而自来,动四两不争而善胜”。乔老师示意记者试试,我使出最大力气推出一掌,可打到乔老师身上却绵若无物,反而被自己的力量推出好远。真切体会到,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玄机和太极的奥妙。
武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的故居在广府城内,是一座具有典型晚清建筑风格的深宅大院。迎门是一块开阔的青石铺就的练武场,武禹襄亲手种下的两棵石榴树,历经100多年,红花满树。相传武禹襄与杨露禅交好,常在一起切磋技艺。1852年,武禹襄赴豫拜师,尽得赵堡镇陈清平的真传。后回广府,开创了武式太极拳。与杨式太极舒展大方、刚柔并济不同,武式太极小巧清雅、修身养性。与杨露禅不同,武禹襄为晚清秀才,出身官宦世家,可谓文武兼备。武禹襄注重拳法理论研究,将自己习练太极拳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撰写了《太极拳解》、《十三势说略》等著作,至今仍为太极拳界的经典之作,他书中提到“详推用意今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将以往中国传统太极拳单纯格斗的宗旨上升到强身健体。
一位仙风道骨的拳师,正在院内演练武式太极。一套“中捋架”气定神闲。紧接着是急攻猛进的炮锤,如疾风骤雨,拳、掌、肘、腿、膝、脚,浑身上下,处处为利器。武式太极第五代传人孙建国的表演让人们大开眼界。他坦言自己是位“太极行者”,几十年来走遍全国各地,游历世界多国,传授武式太极拳法,徒弟无数。而他最着急的事还是传统太极的传承问题。“现在的太极拳虽说普及了,但是花架子太多,失去了太极拳的精华,等到老传承人一个个离开人世后,再想恢复传统的太极就是不可能的事了。”他对我说,现在最迫切的是找一帮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把老一辈的真功夫,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这才是永年人、广府人的最大责任”。
古城、水城、太极城,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古城之外有水,则古城有了灵性,古城之内有太极,古城又有了精魂和筋骨。而水城、太极城共同融合在了古城千年的历史里,一如血与脉,灵与肉,让古城生生不息。
(责编:孙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