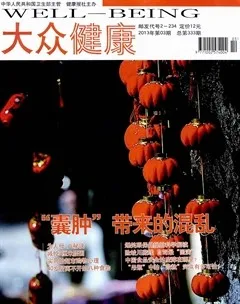你知道的太多了
在医学领域,一切都以结果为最高标准,如果知情权不能导致最佳结果,那还不如干脆不知道。
假如你刚刚登上一架飞机,朋友给你发短信说,一架同样型号的飞机刚刚坠毁了,你会怎么想呢?估计大部分人心里都会有点咯硬吧?但是,不管你心中暗暗祷告了多少回,一旦上了飞机你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所以,你那朋友虽然向你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信息,但却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而让你毫无必要地紧张起来。
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道理:知情权并不是普世价值,有时候知道得太多反而有害。比如曾经有人研究过血糖仪的功效,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对于那些不需要胰岛素治疗的II型糖尿病人来说,使用血糖仪不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让他们更加焦虑,甚至影响了正常生活。
同样的例子还有前列腺癌,这是一种“慢性子”的癌症,虽然很难治,但病情进展也很缓慢,再加上得病的大多数是老年男性,病人往往最终死于其他原因,所以一直有医生反对在普通民众中进行前列腺癌筛查,反正查出来了也不一定治得好,反而降低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更多的案例出现在基因领域。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DNA测序的成本越来越低,这就导致了一种“基因信息焦虑症”,很多人千方百计想知道自己(或者某个感兴趣的人)的基因是什么样的,仿佛知道了一个人DNA顺序就知道了他的一切。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必须警惕。
今年1月10日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就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去年年底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发生了枪击案,凶手亚当·兰扎(Adam Lanza)杀死了30名儿童和6位教师,手段残忍。事发之后,康涅狄格州政府的医疗检察官命令康涅狄格大学的科学家对凶手进行基因分析,试图找出他为何如此残暴的生物学原因。
《自然》杂志为了此事专门在首页发表了一篇社论,大意是说这么做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太大的意义。事实上,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试图从生物学角度寻找犯罪分子的作恶原因。最早是看面相,也就是对比监狱犯人和普通人的大头照,试图找出区别。后来又开始研究大脑,早在1931年就有人研究过一个外号叫做“杜塞尔多夫吸血鬼”的杀人犯皮特·库尔滕(Peter Kürten)的脑组织,试图寻找特殊的“杀人结构”。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末,有个名叫约翰·加西(John Gacy)的杀人犯杀死了33个无辜的人,于1994年被执行死刑,科学家保留了他的大脑,打算研究一下他的大脑沟回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结果当然还是没有区别。
随着DNA测序技术的进步,好奇的科学家们终于把目光转向了杀人犯的基因组。但是《自然》杂志这篇社论指出,科学家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能从基因组里找出点什么,只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这个能力而已。比如康涅狄格大学的科学家们并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也不知道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即使他们真的在兰扎的基因组里找出某个罕见的基因,也不等于说这个基因就是导致他杀人的原因,因为科学家们早就知道,一个人的行为和基因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后天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
比如,以前曾经发现过一个“叛逆基因”,但是这个基因只在携带者童年遭到虐待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表现出来,如果带有该基因的人童年很正常,那么这个基因就和叛逆行为没有任何关联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知道某人携带有这个基因,并因此而对他另眼相待,那就属于歧视。
《自然》这篇社论最后得出结论说,人类行为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绝大部分基因都只有很小的一点点贡献,科学家们当然可以研究基因和行为的关系,但是普通人很难理解这里面的区别,很容易夸大基因的效果,其结果就是:这类基因信息一旦泄露出去,将很可能导致歧视。
基因信息的滥用不但能够导致歧视,还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比如,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杰森·弗莱彻(Jason Fletcher)教授在去年12月5日出版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通过分析美国各州烟草税的不同以及居民基因型的差别,得出结论说提高烟草税对于普通人确实有效,但对于携带某一类基因的人则一点用处也没有,人家还是照吸不误。
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刻被烟草公司用作反对提高烟草税的武器,他们争辩说,基因的差别可以用来解释政府主导的控烟措施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差,因为靠提高烟草税来控烟的政策空间已经穷尽了,现在还在吸烟的都是铁杆烟民,他们的基因型决定了他们从尼古丁中获得了比常人高得多的快感,不会被高价香烟吓跑。
针对此种言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流行病转化学博士研究生苏琪·加戈(Suzi Gage)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弗莱彻的论文严重误导了读者。加戈认为,这篇论文采用统计学方法研究控烟与基因型的关系,这个思路没错,但统计的结果因为预设条件的不同可以有多种解读,比如烟草税到底是逐步提高还是一下子提高的?是否还有其他配套控烟措施?等等。如果不知道这个基因到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烟民的选择,那么这个结论很可能就是错误的,无法反应出真实的情况。
退一万步说,即使弗莱彻的结论是正确的,并不能说明提高烟草税对于控烟没有用处。事实上,政府制定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人,必须从整体效果出发,全面地衡量一项政策的优劣,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仅用基因型来判断好坏是不可靠的。比如在这个案例中,弗莱彻只统计了已经有烟瘾的人,没有把潜在的吸烟者考虑在内。
几天后,弗莱彻教授在《卫报》上做了回应,他说他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只是想探讨加税控烟政策失效的原因,完全没有替烟草公司开脱的意思。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论文没有大问题,但那个基因导致控烟政策失效的结论是否可靠确实有待进一步检验。
加戈则认为,无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都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这只是一个统计概念,从一个人的基因型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推导出他到底会不会成为瘾君子。再加上基因测序毕竟还是要花很多钱的,成本太高了,不划算,不如用另外一些更准确、更廉价的方法判断他是否天生容易上瘾,然后根据这个指标来制定相应的控烟政策就可以了,没必要测每个人的DNA。比如,曾经有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首次接触酒精后的反应很弱,那么他将来更有可能成为瘾君子。用这个指标对潜在的酒鬼进行预防已经被一些研究证明是很有效的,比测DNA可靠多了。
换句话说,在控烟的问题上,基因属于无效信息,不知道反而更好。这类研究的本意虽然是好的,但是研究结果完全无法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而且很容易被误读,反而更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