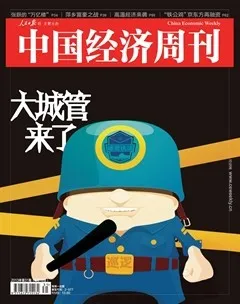城管老队员赵阳和他的 《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

在南京,有这样一位“老城管”,他“把职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办‘城管论坛’、开博客、写微博。他很强调,城管的事,不能寄托于一时一策的‘根治性改革’,而应该‘以十年的周期来看’。他有‘野心’,想做的,是影响全国城管领导群体的观念,进而逐步改善城管问题中的诸多细节”。
他就是南京市玄武区下属街道大队的城管队员赵阳。赵阳坦承:“跟10多年前相比,城管队伍建设和文明执法程度进步了不少,可城管的形象和社会地位,却极度恶化。”赵阳想破解这个难题。
“城管深喉”点评城管
在现在这个岗位上,赵阳已经做了10多年。
2002年12月,赵阳在网络论坛“西祠胡同”上创立“城管行政执法之家”——这是全国第一家由城管执法者自主创办的城管专业论坛。10多年来,赵阳利用网络工具,不断曝光各地城管执法丑闻,点评城管事件,引来众多围观和讨论。
2009年4月,赵阳把北京城管局内部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翻拍下来发到论坛上,这个“城管秘籍”的帖子引发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想象。他所在的单位为此专门开会进行大讨论,讨论中,仅有一半同事表示支持。这让他一度担心自己饭碗不保。
2011年,赵阳在微博上“直播”南京一起拆除违章建筑的执法过程,描述了城管执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而被网络曝光的户主,竟是另一位城管的父母。
他被同行称为“叛徒”、“走狗”,但也被网友誉为“城管深喉”、“城管中的鲁迅”。
如今,打开赵阳在新浪实名认证的微博@桥上人家,从延安城管踩人事件,到最近的北京男子携女儿练摊被城管围殴事件,他都逐一点评,并不给当事的城管留一点面子。“城管不规范执法被捅死,这下连烈士都评不上,纵做鬼,也不幸福!”
“我其实是在走钢丝。”赵阳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作为城管我能做的就两条,第一是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第二是用自己的知名度去做些调查研究,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我们只能服从领导的思路”
城管暴力执法,摊贩暴力抗法,城管与小贩频频爆发矛盾,让社会各界开始思考并呼吁把城管体制改革提上日程,早日解开城市管理的死结,重拾公信力。
也有人开始怀疑城管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但赵阳认为,城管制度不能取消,只能进行改革。他认为,城管问题的根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城管之病”的重要根源是政府制定的城市管理体制和理念存在偏差。
在赵阳看来,城管之病首先是“内病”,“外治”的“药方”是解决小贩问题,并严格规范城管队伍,但这些药方仅是治标不治本。矛盾的根源在于,层层考核下,每个城管都背负巨大压力。各地城市忙碌的“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的评比工作,普遍存在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脱离实际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对小贩占道经营的考核,往往成为激化“管贩”矛盾的导火索。
赵阳曾向媒体剖析了城管与小贩间紧张关系的原因:“比如上级下达任务了,说不能有摊点,但是很难做到的,你怎么办?说是堵疏结合,但一堵就会遇到暴力抗法,压力之下,能不发生粗暴的行为吗?完不成任务,考核就通不过。以我们这里为例,要求不能有摊点的街道,领导下来检查了,发现一个摊点就扣40块钱,我们执法大队的同事一个月最多的扣了五六百块钱。结果是,到了街上(城管和商贩之间)就如同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赵阳在微博中质问:“执法者要反思,立法者更要反思,(出现极端事件后)市长是不是要下台?”但他对此也是有心无力:“作为城管,我们只能服从领导的思路。”
城管制度之弊不仅重伤了摊贩,也刺痛了城管。针对近期因薪酬不高、身份不定导致的城管上访事件,有舆论指出,城管上访戳了体制软肋。
赵阳提醒网民要理性反思。“各地环卫工上访更多,怎么偏偏城管上访就成‘戳了体制软肋’?”他在微博中指出,“是城管法规和小贩过不去,是‘创建文明城市’和小贩过不去,城管和小贩没啥过节。”
8月5日下午,赵阳发表博文——《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建议取消各级“卫生城市”、“文明城市”评比;立法明确小贩“摆摊权”;明确市长是城管第一责任人;限制城管扩权并逐年减负;城管人员以从工商公安等部门选调为主。
然而在文末,赵阳还是附上一句:“以上五条,是歪着斧子乱砍,也是无奈中的乱语。”
对话赵阳:
“城市洁癖”让城管商贩成“天敌”
《中国经济周刊》:你个人怎么看《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引发如此之高的网络关注度?
赵阳:可能是内容比较实在,将空谈具体化。引起关注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观点形成了共鸣,而且有可操作性。比如对小贩,我们一直在讲怎样学习国外的城市管理,就是用立法推进疏导城管工作。但堵疏结合已经提了十几二十年,为何堵也没堵好,疏也没疏好,就是因为从根本上是立法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你们在执法过程中的压力,主要来自小贩还是上级领导?
赵阳:两方面都有。来自小贩的困扰有两点,第一,不要以为小贩都是以摆摊为生,有的小贩不一定靠摆摊谋生,我见过开着宝马来摆摊,有小学生为了体验生活摆摊。富人做兼职,有一些人就是为了体验摆摊的乐趣。所以说,小贩是多种多样的,全部都取缔的话,可能也不太合适。第二个困扰是跟小贩的冲突。不管是打伤了小贩还是小贩打伤了城管,都不是成功的执法,都是悲剧。我们城管有一个共识,就是城管与小贩都是制度的受害者。
领导也会带来压力。我们和小贩之间本身没有矛盾,可能我们城管下班后还会在路摊上买一些东西,前提是不能在工作时间、在所在辖区内认识的小贩那儿购买东西。总的来讲,城管也要在小贩那里消费,我们之间也不是天敌。我们与小贩的矛盾,一是法律职责所在,二是领导的要求,对城管的考核很严,(某些地方)已经到了“城市洁癖”的地步。领导对城管的绩效考核有很大压力,发现一个流动摊点就会对你进行处罚。
还有一个压力是老百姓对我们的不满。老百姓常常问一个很朴素的问题,现在城市里面空间很紧张,划出很多地方给富人停车,却不划出地方给穷人摆摊?这些问题让我们城管也很难回答。而这些归结到一起就是一个城市规划问题,也不是我们城管能够回答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在《对城管改革的五大建议》中为何明确市长为第一责任人?
赵阳:国务院有文件,把城市管理的职责交给了地方人民政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城市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的,那么市长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一个城市如何管理取决于市长的理念,而不是城管局长的理念。城管部门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它的理念完全听从于市长或者市委书记。从行政上来讲,市长是负责任的,包括文明城市的建设等,实际上是市长对城管部门提出要求。
《中国经济周刊》:你近期在网络上提出的一些想法或建议,有没有想过将来自己执法时落实到过程中去?
赵阳:我写的是我在平常工作中发现的、看到的、思考的、总结的,在很多执法实践中提炼出来。大家一开始也不太懂城管。这么多年,不是落实的过程,而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希望将探索的结果,提供给更有智慧的人和更高层参考,由他们来制定更好的适合城管发展的理念,再来落实。
《中国经济周刊》:你从事城管10多年,为什么能坚持如此之久?
赵阳: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不断检讨,也在想自己为何坚持下来。很多人讲,“赵阳你现在在城管系统是一个名人”,但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城管,我的微博认证就是我的姓名、职务、所在地。我反思的是我这些年做了什么,哪些是对社会有意义的,这个才是值得一提的。这些年来,因为个人的能力、自己的平台等种种原因,所做的确实有限,这也是自己非常不满的地方。
作为城管,我能做的就两条:第一点,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第二点,用自己的知名度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所以,办论坛、写微博、上节目,拼命地去做,一直撑到今天,其实也是在走钢丝。努力去做,哪怕一点点成果,都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