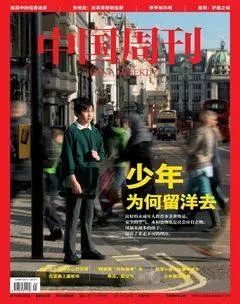信息迷雾中的断桥



在强烈地震中,大部分人除了感觉这世界变得躁动不安,还会觉得熟悉的世界突然变小了。他们的视线会被倒塌房屋带来的大量灰尘遮蔽,这往往会加剧他们的紧张。在那些模糊的影子后面,会有什么危险呢?
即使在狭窄的街道,烟尘也会在几十分钟内基本消散。不过,一阵更浓厚的信息迷雾将长久笼罩在灾区之上。所有的救援者,都要在这迷雾中穿行,才能抵达生命的彼岸。
五年前的汶川地震震中映秀的救援,印证了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论断,他在《战争论》曾用“战争迷雾”来比喻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总和构成战争阻力:
所有的军事行动发生在某种黄昏,像迷雾一样。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战争所依据的3/4的因素或多或少被不确定性的迷雾包围着。指挥官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他的眼睛无法“看见”,他的最佳推断力并不总是很彻底,并且由于环境的变化,他几乎无法洞察周围的环境。
在信息不足,以及缺乏沟通的时候,每个子系统的高效率,反而有可能带来整个系统的低效率,造成救援方向判断失误、交通拥堵、资源不足等一系列压力。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我们是否能在下一次的拯救中更加高效?
一个
误导的名称
2008年5月12日,当地震波的能量开始扩散,来自各地的地震消息也迅速向北京汇集,一个庞大的体系开始被触动。
14时45分,公安部接到中国地震局关于四川汶川地震的通报。在公安部收到报告之前5分钟,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田义祥大校收到了中国地震局发来的短信。
中南海,总理温家宝刚从河南农村考察回来。他后来对新华社记者姚大伟说:“下午2点多,我坐在办公室里,突然感觉晃动。我起初以为是我血压高了,但我很快看到了报告。我马上给刘奇葆(四川省委书记)打电话,他说他正赶往灾区。等我再给他打电话时,就打不通了。”
公安部和温家宝所看到的报告,是由中国地震局发出的震情快报。田义祥大校所收到的,则是短信速报,按照预案,这个短信会在第一时间发给400多名相关人员。这是国家力量开始调动的第一个信息依据,它的内容非常简单:时间、震中、震级。震级此后作了修正,不过,对指挥者来说,这无关紧要。是7.8级还是8级地震,都意味着有极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但是,关于震中的地点,以及地震的名称,一个重大隐患一开始就已经埋下,而且很快发芽、生长。
错误在不经意中一点点形成,在乱哄哄的氛围中,这个细节无人注意。地震一开始表述为在汶川发生,然后被直接称为汶川大地震,最后让许许多多的人,包括负责调动救援力量的指挥者都误认为:汶川县城就是此次大地震的震中。但是,汶川县城根本就不在主断裂带上,全县南北狭长的地理结构让县城远离破裂点。如果以直线距离计,离最初破裂点最近的县级机构是成都下属的都江堰。
震中映秀被遗忘了,即使是在它所处的阿坝州。阿坝州数字地震台网发出的第一份快报称:“5月12日14时27分57.9秒,在我州汶川县漩口和卧龙之间发生了7.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1度,东经103.24度。据各县防震减灾局反映,此次地震我州各县震感强烈,并有房屋垮塌现象。”
州地震局关于地点的表述意味深长:汶川县漩口和卧龙之间。这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地方之间,只有一个比它们人口更多、地位更重要的映秀镇。
无论如何,震中映秀暂时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这里的地震幸存者,必须独自撑过两天。
一个
致命的丢失
下午2点28分,当四川省地震局台网中心速报员陈银发现一部分仪器都被震坏时,他知道这场地震非同寻常。5分钟内,地震三要素——时间、经纬度和震级快速测量出来。电话不通,地震局局长吴耀强和副局长王立分别带着简报赶往四川省委和省政府。
官员们已聚在一起开会,简报让他们知道了需要救援的大致方向,但这个信息太简陋。省长蒋巨峰前往地震局了解详情,同时联系成都军区,让陆航团的直升机做好准备。
震后一小时,省委书记刘奇葆出发前往都江堰,准备经过那里去汶川。他在路上接到温家宝的电话,没讲多久信号就断了。在他的车队前面一点,四川省军区副参谋长向怀树在越野车里不停发送短信。震后40多分钟,他接到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十分清晰的指令:不要坐等,立即出发,边走边报。在路上,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开始直接和他联系。
四川交警总队第一时间也派出了3人工作小组前往汶川。他们走得太匆忙了,没有带上步话机,这让他们离开成都后就与后方失去联系。交警系统的步话机是当时唯一有效的无线通话工具,他们的350兆无线通讯指挥调度系统,只需要一个总机房和几十个基站,这比依赖数千个基站的移动通信网络更能对付灾难。不过,架设在漩口镇白云顶的一个350兆警用通信基站坍塌毁坏,这个关键节点的丢失让阿坝警方脱离了网络。信息中断将比交通断绝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陆航团在震后20分钟内已做好了全部起飞准备,现在,就等省长的到来。
蒋巨峰的车队被堵住了,陆航团又等了一会,下午4点40分,成都军区作战部命令先行起飞,沿着成都、都江堰往山区进行灾情侦查。参谋长杨磊带着照相机驾驶第一架,副团长姜广伟带着摄像机驾驶第二架。天色阴沉,他们降低高度,沿着成都到都江堰的高速公路飞行。他们在都江堰盘旋一圈拍摄,然后顺岷江向山区飞,到达紫坪铺大坝时已开始下小雨。
能见度只有500多米,杨磊在坝顶上方300米左右高度飞行,模模糊糊看到远处横穿水库的都汶高速公路庙子坪大桥断了一截,也看到了大坝一侧的绕坝公路上,灰窑沟那个巨大的塌方体,它前后的公路已经压住了一些车辆。按飞行规则,能见度少于3公里就不允许进入山区。两架直升机拉开距离试图进山,但山峰笼罩在云雾中,始终无法看清,他们不得不返航。回到凤凰山机场后,赶来的蒋巨峰看了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然后带回指挥部。成都军区作战部参谋也将资料带了回去。
这些资料里关于庙子坪大桥和灰窑沟塌方体后方公路的信息,正是四川交通厅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有这些信息,而拥有信息的人也不知道有人需要它。每个系统都在高速运转,只是,在缺乏横向沟通平台的情况下,整个救援体系的效率被大量重复侦察和调动降低了。
几乎与陆航团侦察直升机出发的同时,四川交通厅副厅长张晓燕也乘车前往都江堰查看公路状况。张晓燕的车在灰窑沟大塌方前停下,她无法知道这个巨大的乱石堆后面是什么情况,在会议上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汇报。
其实,交通系统内有一个人知道那边的情况,并传回了简短信息。
都汶高速公司隧道办主任何成检查完映秀的龙溪隧道后返回,地震时正在友谊隧道不远的地方。他马不停蹄向都江堰步行,一个多小时就走到了庙子坪大桥附近。看到大桥的一截已经垮塌,他用手机短信向公司副总经理张广洋报告:“都汶公路沿线受损严重,庙子坪大桥掉了一跨……”
张广洋立即向上级机构四川高速公司汇报。作为交通厅的直属机构,四川高速将获得的各地信息一并报了上去。但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中,庙子坪大桥落梁的细节丢失了。
一个
临时的体系
空军接到执行总理专机飞行任务的时间是下午3点12分,救援指挥在飞机上就开始展开。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与幅员同样辽阔的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没有常设的全国巨灾救援体系,而要成立临时指挥机构,协调原有的行政力量应对灾难。经过1998年的长江抗洪和2003年的“非典”事件,各个行政机构的应急处置能力已经大幅提高,分别建立了应急预案。但是,面对前所未有的巨灾,在综合各方面力量时,除了决策的意志,人力、物力和资源的分配运用还需要极高的专业技巧,这是对每个指挥者的考验。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就在空中成立,温家宝为总指挥,下设8个功能组,这几乎就是飞机上的部长们所辖部门的翻版。功能组直接对应政府各行政部门,这能保证部门内资源调动的高效。不过,行政管理条块分割带来的传统隔阂,在灾害救援的紧急状态下缺少充足的时间来慢慢消除,这使得一些跨部门的关键功能——比如信息汇总——出现指挥空白。这是临时救援体系所要付出的代价。
车队在晚上9点到达都江堰公安局门前的指挥大棚。全城断电,整个都江堰漆黑一片,温家宝走进幸福大街人行道上的这座大棚坐下,他的椅子后面一米是一条小水沟。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人,大部分都站着,刘奇葆打开电脑开始汇报。灯光亮度明显不够,温家宝翻阅地图和文件时,工作人员为他打着手电筒。刘奇葆讲着,军队和武警的高级军官们不时补充情况。
汇报的重点是伤亡和交通。晚上8点左右,各地的伤亡数字已经渐渐报了上来。北川达到了惊人的2000人——这只是最终数字的一小部分,其次是绵竹。至于震中汶川,没有任何消息。这是可怕的沉默,这个让人揪心的地方成了会议的重点。刘奇葆提到了几种选择:南线抢通213国道,同时尝试走紫坪铺水库的水道;北线已在北川阻断,可能性最小;最后是绕道700多公里的遥远西线。
信息不多,汇报很快结束。温家宝简短提了5点要求,首先要求部队立即从南北两个方向向震中前进,克服一切困难,步行进入。其次是争分夺秒抢修一条临时道路。最后要求地震部门抓紧会商,对地震趋势做出研判。
一个
假想的妙招
总指挥部9点会议所做的决定开始让交通系统全面启动。当温家宝前往灾难现场时,国家交通部、四川交通厅、成都交通局及下属都江堰交通局的头头脑脑们倾巢出动,前往213国道查看。灰窑沟的大塌方盖住了约100米长的路面,一边是不断滚石的山坡,一边是悬崖,能够展开作业的机械有限。大塌方后面的情况不明,大部分人感觉这么庞大的塌方是个特例(这一点对了,这第一个塌方也是沿线最大的塌方),后面的道路应该容易清理得多。问题是,怎么打开眼前这个死结呢?
熟悉本地道路的都江堰交通局长高成军想出了一个“妙招”:绕过去!213国道在这段岷江的南岸,他建议彻底转向北岸,那边有市区通向龙池镇的龙池公路。它和已经部分建成的都汶高速公路十分接近,修建紫坪铺大坝留下的一条施工便道可以将它们相连,再通过穿越水库的庙子坪大桥回到213国道。这不仅绕过了大塌方,还绕过了马鞍石隧道,沿213国道前进了一大步。
这个方案让大家兴奋不已,它当即被采纳,由高成军负责实施。
从市区前往紫坪铺大坝及龙池公路的道路也被滚石堵住了,但和大塌方相比,这只是小儿科。高成军迅速调集3台装载机,从岷江南岸穿过坝下的彩虹桥到达北岸,一路清理道路,顺利到达坝顶。
他现在面对开阔的水面,不远处就是宏伟的庙子坪大桥。漆黑的雨夜让他看不了多远,他不知道这桥已经断了一截。都汶高速公司隧道办主任何成的宝贵短信已经被海量信息淹没,高成军对陆航团下午的侦查拍摄更是闻所未闻。他一门心思冒雨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拼命苦干,快速抢通的希望就寄托在他身上。
温家宝的现场视察很快结束。晚上11点40分左右,大棚的嘈杂声消失,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开始。更多的灾情从各地传来,但汶川仍然是信息空白区。凌晨1点多会议结束。此时,阿坝州委书记侍俊即将赶到指挥部。
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在星期一的上午,阿坝州几乎所有主要领导都在成都:州委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多名副州长、军分区政委、纪委书记等,他们与自己的辖区全都失去了联系。地震让他们不约而同聚到了213国道的入口处,做了简单的工作分工后,阿坝州州委书记侍俊开始绕行北线。他尝试多条道路,但无法通过。当他返回都江堰指挥部时,时间为凌晨2点多。
侍俊对汶川的情况也知之不多,但他的到来带来了一个重要改变:开辟水路的方案第一次正式讨论。水路并不能直接到达汶川,它的出发点仍然是绕过灰窑沟的大塌方。不过,与高成军的借道都汶高速公路的绕行方案相比,水路顺着213国道更能往前大大推进一步。很快,武警和消防都接到了准备冲锋舟的命令。
一个
可依赖的人
信息已经成为救援指挥的最大困扰。形势的紧迫让很多指挥者必须立即做出决定。但在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猜测中匆忙选定一个方案。
信息迷雾毫无疑问会带来决策迟疑和失误。人力侦察作为最低效的手段,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国家测绘局获得的前几批卫星图像数据,因为灾区的阴雨天气,导致图像质量差而无法使用。测绘局开始联系国际主要卫星遥感公司,协调了4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调整姿态,对准中国灾区。这番调整要耗费不少时间。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受命协调空军、总参谋部、国家测绘局、商业机构的7架飞机进行航空拍摄。但是,它们大部分要在第二天到达灾区,并因下雨而迟至第三天才能拍摄。
在人力和高技术手段都尚未奏效时,其实还有知识可以依靠。
此刻,那个几乎唯一可以拨开信息迷雾的人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验室里,和他的学生紧张推演判断着各地灾情。
史培军,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国家减灾委员会副主任,拥有一间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重点实验室。它的核心是一个完备的数据库,中国所有县级地区近百年的自然灾害数据全部存在其中,史培军花了20年时间才完成这些研究。当这些数据与地震技术资料相对照,便可在缺乏一线信息的情况下,大致判断出灾情。
不过,史培军还缺乏地震资料。国家地震局公布了地点和震级,但更重要的地震烈度分布图没有下文。晚上8点,他得到了意外的帮助,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在网站上公布了模拟的汶川地震烈度图。这张图清晰无误显示出断裂带地震的特征:损失不是以震中为圆心,一圈圈扩散,而是呈椭圆形,在200多公里长的地带全面展开。史培军知道,灾难将超过想象。当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次正式会议结束不久,凌晨2点,他和学生分析出了这次地震灾害的基本数据。他大致知道了不同等级的灾害分布区域,会有多少人死亡,又有多少灾民需要安置。这正是各级指挥部迫切需要的信息,没有它们,救援资源的投放方向正渐渐偏移。
交通局长高成军这几个小时的进展也不错。第一个小塌方在凌晨2点多被清除,二王庙前的道路在3点多被打通,紫坪铺大坝与都江堰市区之间已经没有障碍。他的“妙招”正在一步步实现,即将在早晨召开的总指挥部第二次会议上,交通部门可以有好消息汇报了。
一个
失望的结局
天亮了,在幸福大道上,抬头往西即可看见城市边缘像墙一样平地拔地起的龙门山。它将发生的一切灾难隐藏在后面,继续考验指挥部的智慧和意志。
7点钟,部长们又围坐在几张桌子旁。没有刷牙洗脸,大家满脸倦容。听取了最新情况汇报后,温家宝为交通部门划出了冲刺线——务必要在13号晚上12点之前打通前往震中的道路。这条消息被迅速发布,“今晚打通震中道路”的大字新闻标题将许许多多救援队、寻亲者、志愿者和记者吸引到213国道入口处等待通车(事实上,这条公路3个月后才全部打通)。
在会议召开的同一时刻,高成军在天色微明中看到了让他心凉的场景:绕行所必经的庙子坪大桥断了!他不甘心,穿过紫坪铺大坝坝顶,想从大坝另一端陡峭绝壁下的水边寻找与213国道直接相连的通道。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亲自指挥,但水边都是烂泥,装载机一开过去就往下陷。绕行方案彻底破灭,13号午夜打通道路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总指挥部的会议在继续,全线道路损毁的严重性没有人完全了解,关于交通的最新坏消息也没有传到这里。温家宝进入汶川的愿望十分强烈,他向将军们要求:“把我空投进去!”这太危险了,大家一致劝阻,温家宝说:“我在西藏也坐过直升机。”他坚持要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范晓光与温家宝秘书商量,共同寻找理由来说服这个动了感情的最高指挥者。
北京,早晨8点,史培军带着熬夜得出的分析结果去找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一个多部门综合会议在此召开,史培军向与会者讲解了他惊人的判断:死亡人数可能达到5~10万人,需要准备100万顶帐篷。整个民政系统库存的帐篷只有15万顶,12号晚王振耀向上海厂家预订的裹尸袋不过几千条。但他相信史培军的专业,会后向厂家追加到了几万条。王振耀担心民众无法承受,这个数字没有对外公布。
这些珍贵的专业判断在民政系统发挥了作用。本来,它可以帮助更高层级的指挥部决策,但指挥系统的先天缺陷让这种可能失之交臂。各个行政背景的功能组之外,没有一个跨部门的信息组,信息便往往停留在各个部门内。没有建立与救援作业流程相对应的组织结构,这一点所造成的弊端,在随后交通工具的控制和使用上也将很快显现。
不过,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量开始显示威力。在全国总动员下,成千上万的人怀着急迫的心纷纷赶往四川。
(本文摘自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汶川地震16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