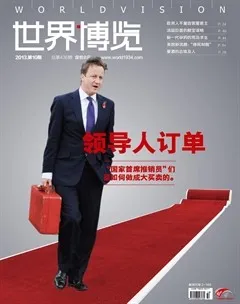拉赞助与打秋风
并非只有中国人喜欢去富人家吃拿卡要,世界人民都“打秋风”,只是没这词而已。
中国人,什么字都往雅了谈。比如上门吃拿卡要,叫做“打秋风”。米芾札里有词,曰“打秋丰”,想来意思很顺:人家秋天丰收啦,你上门去打两把,和“打土豪”差不多。但“打秋风”听来就风雅了。《儒林外史》里,张静斋拉着刚中举的范进去县令处打秋风;《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实质也是打秋风。
大的单位无比强势,就不叫打秋风了,直接是拉赞助。日本战国时,织田信长往京都去挟天子以令诸侯——日本谓之上洛;洛者,洛阳也,日本是惯例把京都当作中国汉时洛阳的,比如京都的城下町,就叫做洛外町——就往京都邻近的自由贸易都市堺港去了趟,跟当地富商今井氏们聊天:兄弟我上了洛,要保京都一带和平,你们商人们也不好意思干看着吧,那就有钱的捐钱,没钱的捐点火绳枪和茶器吧……
中世纪时候,欧洲艺术家要么靠教廷贵人养,比如罗马的艺术家作坊,或多或少,都能得些教皇接济;但小地方的教廷和艺术家就惨一些,于是欧洲地方教廷,也得跟中国僧侣似的:化缘。比如,许多地方教会,有地位但没钱,于是隔三差五,请当地领主、富商、大人物来聚聚,好比中国和尚请员外们来个法会。吃完喝完祭祀完,就让教堂艺术家奉上曲子一首,恭祝领主富商们身体健康、得上帝的宠幸,最后领主们也识趣,知道上帝的音乐不是免费的,就会捐助一二。大家面子上都下得来,多好。巴赫、维瓦尔第这些巴洛克音乐大人物,都写过类似的致敬曲子——实在是帮忙打秋风拉赞助。
大航海时代,肯砸钱的人多,打秋风的人更多。哥伦布这样的大航海家如今自然是跨时代的不朽,但当初都是接了赞助商的钱,出门给雇主捞黄金的。话说,那时代更多的是小冒险家,没大名气,也没发现过美洲、玩过环球航行,怎么蒙钱呢?于是有了个好玩的行当。那会儿,威尼斯颇多退役水手,转行去做歌剧龙套的。如果一个小冒险家想打秋风,就雇些威尼斯出产的退役水手,装满一船,然后买几张装模做样的推荐信,这里混一个印章,那里骗一封委任状,最后装点得一身金灿灿去找大贵族投资,一大笔钱到手后,没出航就已经是大爵爷的款了。总而言之吧,借着未知的世界信息不对等拉赞助,外国人更驾轻就熟。
如今举世都说,托尔斯泰的夫人如何不好,实际上,如果细加思量,托夫人一辈子在做的,就是拒绝各类打秋风的小混混。托爵爷不仅小说里写了许多理想主义故事,现实生活里也打算解放农奴,做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老人家道德高尚自然无妨,但托夫人却得想法子:怎么让家庭继续运作,养着爵爷过舒服日子。而且托尔斯泰晚年,已成欧洲青年导师,五湖四海的俄罗斯有志青年都上门来,参拜瞻仰,住下不走。托尔斯泰等于养了一门子食客,大家天天吃饱无聊,就谈论如何改造社会,如何培养道德,如何构筑人间天堂……而托夫人只好唱黑脸扮恶人,时不时赶走几个青年,时不时对新来的青年说不,就差直接说了:你们就别仗着老爷子理想主义,打他的秋风啦!
打秋风这事,其实也是人看衣装。印象派大师雷诺阿和莫奈二十出头时,俩穷学生,经常联手去蹭饭。当然,那会儿雷诺阿对莫奈有一点疑问:大家穷成这样,你还打扮成贵公子、花衣袖、金纽扣,这像打秋风的样子么?很多年后,他才明白真相。
话说1877年,莫奈打算画圣拉扎尔车站。那时他明明穷得都没法住巴黎,只好搬去乡下了,却还留着贵公子衣裳、花衣袖和金纽扣。于是昂首阔步,去找圣拉扎尔车站站长,张嘴就是“兄弟我是画家莫奈!”气度太大,站长都不好意思说“没听过,你是谁啊?”莫奈接着通报一个大新闻,“我决定画你们车站了,本来想画巴黎北站的,但你们站更有范儿!”站长受宠若惊,赶忙去安排。于是莫奈在站长室,一边享用人家奉上的咖啡雪茄,一边翘二郎腿看车站清场放烟,然后施施然出去,画了一打儿画,最后还接了站长递上来的礼物,潇洒离去——所以你看,打秋风拉赞助,佛靠金装人要衣装,全世界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