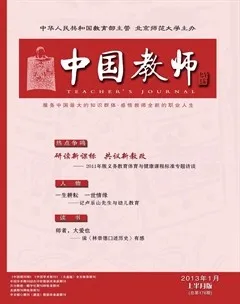国际视野下的教育公平与质量
如何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是当前中国教育领域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重要的国际性话题。2012年金秋十月,来自海内外的200多位教育专家、学者、青年学子,相聚于北京师范大学,就此重大话题展开了为期两天的多方位、有深度的探讨。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北京师范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双年度教育国际研讨会。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在国际教育学科方面享有盛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该学院已有十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并自2006年起连续成功合办了三届教育国际研讨会:2006年的“适应不断变化环境中的教师教育(伦敦)”,2008年的“学习社会中的领导力(北京)”和2010年的“全球化世界中教育与公民身份(伦敦)”,在学术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回响。
本届会议主题确定为“教育公平与质量”,是鉴于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的重大命题,得到国内外教育领域的热切关注,不仅有7位国际一流教育专家到会做主题发言,还有15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从“教育实践中的公平”“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全纳教育”“研究、研究者与教育公平和质量”“交流、文化与认同”这5个维度在大会的分论坛上展开热烈的探讨。本文着重采撷大会7个主题发言的主要观点,供大家一窥此届盛会之精彩。
一、多样性环境下的教与学
在全球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当今,教育如何面向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社会符号学研究专家、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教授以“认可”(recognition)为核心词,从全球相关性的视角提出一种在多样性环境下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教与学的理念和思路。
克雷斯教授以他在研究中积累的具体事例,向与会者展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符号或象征的理解往往千差万别。例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差异——就像一百个人的心中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欧洲儿童和非洲儿童对白雪公主有迥然不同的理解;不同职业背景下的理解差异—— 一幅在克雷斯教授眼中的剧院施工图,一位医生却理解为一张人体手术示意图;不同语言背景下的理解差异——中国幼儿与阿拉伯幼儿的涂鸦线条不同,但相关于各自的母语,前者形似一块块汉字,后者形似一串串阿拉伯文。那么,国际化的教育如何面对多元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呢?
克雷斯教授提出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认可”的教育学,其基本要义是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要以学习者的兴趣为出发点,运用符号学的一些原则设计学习环境,以促进学习者有效转化、正确“认可”所学内容——发生有效学习,获得意义。为此,课程与教学的设计需要所有学习者共同参与决策,以明晰学习者要建构怎样的意义,并设计有效工具检测学习者是否真正建构了。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获得符号的意义,评价的目的是激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而不是检测学生的记忆和模仿。这样的教育学不仅有助于每一位学生的学习,而且有助于课堂形成良好的社会伦理取向,达成多元文化之间的“认可”。
二、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问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刘精明教授以大量详实的数据作了题为《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及相关问题的社会学讨论》的主题报告。刘教授指出,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扩张,引发了社会对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争议,有的认为扩张“增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有的认为扩张“减弱”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例如“农家子弟机会减少”这一说法。
调查研究显示,家庭的阶层背景因素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的代际传承效应在不同时期一直都是十分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扩张使各阶层的相对优势有所下降(特别是普通本科教育),而在1998年后的扩张时期,阶层差异反而有较为强烈的扩大,主要体现为管理阶层、普通白领阶层的优势,以及来自工人阶层急剧的机会优势增长,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异扩大,各个阶层地位中的子代在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差异化更加明显。可以说上层优势家庭的子代基本维持了他们在本科阶段机会获得的优势地位,而中间阶层的子代,在1999年扩招之后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机会获得优势。
即使是在强烈选择后的群体(在校大学生)中,仍然体现出较强的社会阶层、家庭背景等方面的不平等差异。将在校农家子弟分为三类:农户子弟,上大学前户籍为农业户口;农村子弟,上大学家住在农村;农民子弟,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从事农业劳动。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高校学生中农户子弟已经为大多数,所占比例为63.3%。农村子弟的比例也接近一半,达48%。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子弟的比例较小,为25.8%。从时间趋势看,三类农家子弟在高校学生中的比例都呈现上升趋势。相对总体而言,三类农家子弟父母的文化水平更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水平。而家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农家子弟进入985、211工程大学比例的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研究也发现,农家子弟争取优势高等教育资源的途径在于一代一代地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
基于调查研究结果,刘教授指出:教育不平等并非“零和游戏”,总量的增减影响到全体民众;教育不平等根植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同时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实质层面。因此,教育不平等是否因为总量的增加而减少,有赖于一个社会整体的不平等程度是在加深扩大还是在缩减;在既有不平等体系下,扩大的机会提供了另一种“一部分人先富”到“共同致富”的相似模式;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是突破既有不平等体系最重要的方式,因而也是下层崛起的重要途径;杜绝非教育因素在人才选拔过程中的影响,应是制度设计需要重点考量的内容之一。
三、教育研究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格洛里娅·拉德森·比林斯(Gloria Ladson﹣Billings)教授以《犹在镜中:教育研究中的种族问题》为题,着重谈论“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在美国的教育公平与质量问题。比林斯教授以美国历史上黑人奴隶制、种族隔离、反种族隔离斗争等的一些典型事例,指出历史上的种族歧视、种族偏见仍留存于当今的美国教育。例如“智商之父”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曾将“美国西南地区的西班牙、印第安、墨西哥以及黑人家庭中缺乏严格要求和规矩”的现象,打上了“种族”特性的烙印,这种观点现在仍在美国乃至全球流传。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种族歧视表现为:以种族将人类界分为离散的群体;在不平等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将这些群体人为划分等级;认为人类群体的外貌特征标志着其智力、道德、性格等内在品质;认为人类群体的外貌特征以及内在品质均具有遗传性;每一个别的群体(或种族)都是自然界或上帝独特创造的,所以认为这些种族的特性是天生的,固定不变的,也不允许有人为的变化(例如异族之间的通婚)。
由此,比林斯教授呼吁教育界要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权益问题,研究教育如何渗透他们的文化,关注学校课堂教学中这些儿童的学习所得,促进他们的发展,以彰显美国宪法倡导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理念和目标,提高教育公平与质量。
四、教育的全球目标——普及学习
世界银行的伊丽莎白·M.金(Elizabeth M. King)教授的报告主题是“为何要将‘普及学习’作为教育的下一个全球目标”。金教授指出,近二十多年来,全球的普及教育有明显的改进,发展中国家儿童入学率显著上升,但入学率并不意味着就有学习,所以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如何改进这些国家学校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高教育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应对的问题。
人类科技的突飞猛进,使得社会对合格公民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不在于儿童坐在教室里的年数,而在于儿童在教室里获得怎样的知识和技能。而学习者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也更有利于他们开创自己美好的人生。有研究显示,学生的学业成就与国家经济状况有相关性,而学生在工作坊中表现的能力水平更能预示经济增长速率。因此,我们要将教育的目标从普及教育转变为普及学习。
为此,许多国家纷纷采取行动:肯尼亚实施“额外教师项目”,补充小学师资队伍,以减小班额,降低生师比;巴基斯坦采用学生和学校“报告卡”,实行信息责任管理;采取教师奖励制度,例如印度的安得拉邦根据学生在“安得拉邦学习随机评价”中的学业表现,颁发教师奖金,巴西的累西腓也依据学生学习结果给教师颁发奖金;巴基斯坦给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同样的人均教育津贴,以使私立学校也能为学生提供免费的教育;莫桑比克实施“儿童早期发展教育计划”,促进幼儿发展;等等。一切的举措都在为实现普及学习,提升全球教育公平和质量而努力!
五、教育与社会公平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杰夫·惠迪(Geoff Whitty)教授着重谈论英国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问题。在英国,不同社会阶层学生的学业成就之间有明显的差距,现任英国政府提出要“消除”而不是“减弱”这些差距,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已有的数据显示,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经济状况的学生学业成就存在差距,不同性别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就也存在差距。FwjaY9JFAXEC50B12vO7WA==学业成就的差距影响了学生高中毕业后能进入哪一类大学继续学习。
费因斯坦(Feinstein)2003年的调查显示,学前儿童家庭父母(特别是父亲)的职业背景与儿童在表现上的差距具有相关性,即便在认知测试中得分不错的家庭背景弱的儿童,其表现也低于来自家庭背景强一些的学生。后续他人的研究也显示,家庭经济状况与幼儿在表现上的差距相关,另外父亲职业阶层、母亲教育背景也与幼儿表现存在相关。还有许多数据显示,不同家庭社会与经济阶层的在校学生学业成就呈现差距。
为此,英国采取了系列教育政策改革,以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这些改革政策中,有效的改革政策有:在每一所学校实施“识字和识数国家措施”,提高儿童的识字和识数能力;制定优秀教师标准,注重提高教师素质,同时引导学校以教师教学为重心开展工作;鼓励一些学校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学习服务,例如额外的学习设备、在校学习时间等等;通过“伦敦挑战”项目,伦敦的学校和学生其成就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设立自治学校,赋予这些学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一对一的个体化服务(例如阅读康复),关注每一个孩子。综观这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尽管角度不同,但着眼点均关注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致力于学生的学习进步。
也有人对这些改革结果提出质疑,认为所取得的成效是否与社会经济或人口变化有关。惠迪教授认为教育界需要进一步思考,在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这一问题上,教育到底能做一些什么。
六、为公平和质量的教育改革价值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从教育改革的价值基础这一维度出发,探讨了教育公平和质量问题。郑教授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教育改革,以不断渐变的方式完成了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教育转型。在教育目标取向上,国家、民族、集体、阶级以及政治意涵消减,转向人的个体发展。德育让位于规则和权利教育,社会主义和爱国概念让位于“关爱”和“感恩”教育,“集体主义”和“团结”让位于“合作与共处”,等等。
郑教授指出,教育培养目标的语境和历史变化,是与原来的社会及国家的共同体的解构和教育的公共性内涵的变化相关的。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公共教育概念价值基础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发生了一些变化,经济的全球化开始消减民族国家的边界和价值基础,出现公共教育的危机,具体表现在普遍把公共教育仅仅视为服务于个体和家庭“升学——就业——消费”的私人利益工具,家庭一方面在子女教育上的选择、参与都有所提升,但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专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几乎所有阶层的家长仍然会屈从教育改革的生存压力及教育恶性竞争,例如应试教育和补习压力。
郑教授指出,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公平的实质,是通过公共教育激发儿童丰富的有人类价值的社会活力和人生活力,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分数和升学的追求,或简单的个人挣钱发财的能力和欲望;通过公共教育培育的是人们在具体、现实的国家、民族、人类的共同生活中所需要的价值和能力,而不是抽象的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也不是抽象的、指标化的“质量”和“平等”达成。
七、公平的教育体制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公平中心的梅尔·安斯科(Mel Ainscow)教授的报告主题是“建立公平的教育体制”。安斯科教授指出,在全世界,大约有7 000万的儿童未能接受正规的教育。即便在发达国家,贫穷的儿童也未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例如,与芬兰相比,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校表现要远远逊于芬兰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来自加拿大、芬兰、日本、韩国以及OECD合作经济体中国香港和中国上海的学生,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都照样能在学校表现良好。这些现象让我们思考,是否我们可以从改善教育体制的角度,促使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公平对待?
基于社会公正的立场,积极与有关的社会团体及系统进行合作,安斯科教授与同事们在英国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研究:在一个有着重点学校、教会学校及综合学校等各类学校的学区,14所学校共同合作,从教育体制改革的视角对英国当前教育体制下的学习困难学生进行转化研究。
研究过程中,各所学校的教师组成一个研究团队,与大学研究人员展开紧密合作,着重对学习困难学生展开多方位调查研究:数据分析、观察、学生访谈、摄像。通过调查,教师获得了许多的信息,例如有相当多的学生在7年级和11年级之间转到其他学校;那些表现不出众,也不调皮捣蛋的学生在学校得不到关注;许多学生倾向于逃学。
各校研究团队不断地将调查结果形成报告,在全校教师会议以及各校之间的交流会议上,研讨交流,相互支持帮助,以寻求改进学习困难学生的对策。研究结果表明,学校系统有不断完善自身的潜能,有必要加强学校内部及学校之间的合作,学校改进应与社区发展联系起来,需要建立一种基于责任共享原则的新的管理模式。
基于研究的结果,安斯科教授提出了教育公平的生态概念,其相关因素有:校内因素,与学校及教师的教学实践有关;校间因素,与当地学校系统的特点有关;校外因素,与学校办学相关的社会背景有关。公平的教育体制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使这些因素处于良好的生态之中。
除了大会的7个主题发言,大会分论坛的上百个发言也精彩纷呈。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在会议总结致辞中所说的,一次学术会议,就像一个个问题、一个个观点的展览会,每个人展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别人交流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每个人又都从别人的问题和思想中获得启示。因此,与其说会议是要解决问题,不如说是要产生新的更有价值的问题。本届会议主题的时代性、报告的高水平以及讨论的深度均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本刊后续还将选登一些分论坛的报告内容,以供大家更多地学习和思考,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公平和质量。
(责任编辑:马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