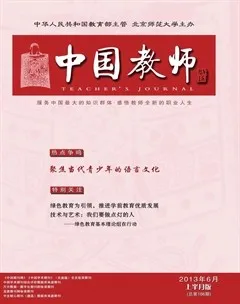教学改进与学科加工的关联

教育工程学的思路不可取
早在20世纪60年代,杰克逊就对所谓的“教育工程学”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这里的“教育工程学”,是一种在工业生产领域曾经大行其道的管理典范,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在工业生产中,老板要求工人尽量快速、高效,尽量减少无效动作。这种对工业生产效率的追求,应用到教育中来,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尽量快速、高效,尽量减少无关动作。但是,这显然不符合今天人们对教师工作性质的认识。用杰克逊的话来说,“工程学观点作为一种观看教学过程的方式,主要的缺陷就在于对小学课堂中发生了什么,采取一种过度简单的图像呈现方式”。而事实上,小学教师的生活更加复杂,“平均每个教师每一年中的1 000个小时都是在管理25~30名能力和背景各异的学生,他有可能得同时负责4~5门主要科目,要求每位教师清楚地了解他自己的每一个教育瞬间是不可能的”。
杰克逊对“教育工程学”的批评、对教室生活的描述,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是,今天中国的小学教研生活中,仍然在大量应用工程学的思路。我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原因是我观察到一些看似先进,实则落后的教育现象。
第一、一些评价教师教学行为的量化工具大行其道。这些工具观察教师提问学生的频率、频次、覆盖面,甚至观察教师在教室里走动的路线等等。这些工具看似科学,是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做法,但实际上,这些工具所基于的假设,是经不住反思的。要知道,教师的提问、与学生的肢体或眼神接触,都只是完成教学、促进学习的工具。教师首要的关注点还是教学,而不是这些工具的应用。在我看来,只是因为这些工具在管理上的应用价值,才得到人们的青睐。
第二、教师的角色被压缩为执行者,教师的兴趣ob+O7jQc7q/RFHkDSr/jYg==中心局限于行动策略。在与一线教师的沟通中,最经常听到的是这样一句话,“请告诉我们怎么做”。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现象!承担了教书育人重任的教师,原来只是等待指令的操作工人吗?绝对不行!今天的教师,应该成为一个课程专家,而不只是教书匠。作为“课程专家”,教师要关心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教科书”和“教学”。教师要关心的话题,更进一步扩展,包括更一般的“教育目的”和“课程设计”等等。
先研究内容,后进行评课
可以说“教育工程学”的贻害,远远没有被大家充分意识到。我所做的一项与教学研究、教师专业发展相关的工作,就是试图突破这种恶劣影响,试图扩展一线教师的兴趣中心。在我的听评课过程中,并不点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言一行上的得失,更不关注有关学生参与状况的统计数据。我用“学科加工”这个概念,提醒一线教师关心自己教的内容。基本上,我的评课方式可以概括为“先研究内容,后进行评课”。研究好了内容,该选择什么重难点、该选择什么教学方法,就呼之欲出了。
“提示语的书写”这节课,当然也可以应用这种方式来评议。在这节课上,教师使用了下面这段文字作为素材:
一位小学生从游戏厅门前走过。老板说:“小同学,来玩游戏机的吧?”小学生说:“爸爸妈妈不让我玩。”老板说:“玩游戏机,健脑!”小学生说:“总是玩电脑不但荒废学业,还会伤害身体!”老板说:“我请客!不用你花钱。”小学生走开了。老板道:“哎,又少了一个俘虏……”
这段文字很有教学价值,因为游戏店老板在说话的时候,很可能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学生可以通过在提示语中加入动作、神态或心理活动的描写,把这种心理表现出来。比如,有一些学生写的提示语是“不怀好意地说”。这体现出老板的狡猾和唯利是图。有一些学生写的是“游戏店老板热情地说、亲切地说”。这可能是因为教师经常引导孩子,让他们误以为但凡成人都是可敬的、和蔼的。不论学生可能写出什么样的提示语,通过描述游戏店老板,的确能够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学生们展现不同的提示语并做比较,这才是对人物性格的揣摩,或者是对他们想表达的人物性格的揣摩。相对来说,选择词汇、组织语言反倒是第二步的工作了。通过这样的教学,提示语不仅变得有趣,而且变得有意义。学生发现提示语是真正有用的,而不是教师在黑板上呈现的一种语言技术和文字工具。
与小学英语学科不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已经可以赏析语言文字了。杨校长写过一首儿童诗:“妈妈妈妈别生气,我来帮你扫扫地。妈妈妈妈别生气,我来和你做游戏。妈妈妈妈还生气?你吃西瓜我吃皮。”这首诗里的符号都是有意义的。在朗诵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气把它们表达出来。当然,在写作的时候,作者很可能没有经过细致的琢磨。但是,我相信一位优秀的作家,是可以把这些技巧自然地流露于笔端的。在“提示语的书写”这节课中,学生学习的重点应该放在语言文字的赏析上。教学的主要功夫,是帮助孩子们欣赏优秀的语言表达,赏析文字中鲜活的表达。当然,学习语文还包括许多其他任务,譬如以文字为载体学习语文技能、理解作者想表达的内容等等。我对“提示语的书写”这节课的教学重点的判断,就是基于对“提示语”这个语言工具本身的理解。在我看来,正是提示语的使用,使得一些对话描写变得灵动、精致、感人。“提示语”这个语言工具,绝不仅仅是“某某人说”这么简单。“提示语”放在对话之前还是对话之后,这不是唯一的学习内容,更不是教学难点。讲提示语的位置,让孩子们练习在对话的不同位置添加提示语,但是不去挖掘这些提示语所造成的语言效果,这样的教学哪里能让孩子们学会提示语的使用呢?
我的上述点评,更关心的是这节课本身的教学内容。我认为,只要吃透了“提示语”这个知识点本身,就不难确定这节课的重难点。我们有的一线教师在设计教学时,虽然也“关注知识点”,但是采取了一种割裂的关注。以这节课为例,教师可能的确很关注提示语,整节课都围绕着提示语是什么、怎么写来进行,但是,却忽略了提示语在写作中的价值。在我看来,这是语文学科学习的一种本末倒置。要知道,学习语文的最基本的目标是掌握语言文字的使用。类似“提示语”这样的语言工具,它的“使用方法”就好像一本说明书。掌握这本说明书很重要,但不是学习语文的最终目标。
总之,我想与各位老师分享我的一种评课方式。同时,也号召大家在评课前,务必认真地研究研究内容。
[杨丽红:挺好。前几天我们的一个特教在学校开了一个会,总结说我们要做点灯的人,真正点亮孩子的心灵。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好,点亮了我们。老师要抓这些有意思的点是挺重要的。这个内容很好,就是我们要找到用什么方法能点亮孩子,这个特别重要,我们要深入地研究研究。我们在课堂上看到了技术,但是看不到艺术。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是“文化艺术共生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