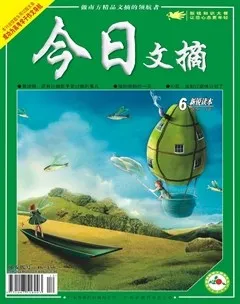最后一个愿望
那是很多年前了,外婆还在世,每星期母亲都带着我去看望她,路很远,骑车要40多分钟。一次,我们在路上摔了一跤,车子坏了,外婆叫阿茂送我们回家。
那是个很土气的男人,见到母亲,黑黑的脸涨得通红,很不自然地笑了笑。母亲有些惊讶,很突兀地冒出一句:“阿茂,你怎么老了这么多?”他还是嘿嘿笑。
坐上阿茂的三轮车,母亲一路和他聊天,不知不觉到了家门口。冬天的傍晚很冷,母亲让阿茂进屋暖和一下,他不停推辞,母亲恼了:“叫你进去坐一会儿就那么难?”这一吼,阿茂乖乖地进了屋。母亲温了酒,阿茂赶紧去拦:“坐坐就好,酒不喝了……孩子爸爸回来看见不好。”母亲倒酒的手顿了一下:“我们分开8年了。”阿茂有些吃惊,嘴巴张了张,但什么也没说。
喝了几口黄酒,阿茂不再那么拘谨,话也多了。他说他去了山里,两年后娶了个山里姑娘,回到小城。为了挣钱,办了三轮车营运执照。母亲关切地问:“这活儿是不是太累了,你都50岁的人了。”他还是嘿嘿一笑。
接着,他支支吾吾地问起母亲的事,母亲有些伤感地说了一些很少提及的往事,阿茂脸上满是遗憾。他临走前,母亲把20元的车钱塞给他,他坚决不收。最后,母亲只好偷偷放进他口袋里。
再去外婆家时,我们才知道,阿茂硬是把车钱送了回来。母亲带着我找到阿茂家,他妻子拉着母亲的手拉家常,最后,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恳求说:“阿茂常常胃疼得厉害,你能不能劝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你的话他也许会听。”母亲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母亲讲起她和阿茂的往事。他们是同学,关系很好。初中一年级时,阿茂的父母先后去世,等他哥哥结婚后,年少的阿茂辍了学,种田做工养活自己。左邻右舍都很照顾他,外婆更是常常派母亲给他送吃的。一晃几年过去,阿茂成了模样周正的小伙子,托人来外婆家说亲。然而此时,母亲已经认识了父亲。她找到阿茂,说明了原委。阿茂不相信母亲有了男朋友,直到亲眼看见身穿军装的父亲。他极度伤心,一个月后就去了山里,从此杳无音信。一晃多年过去,再相遇时,已是物是人非。
后来,阿茂常常送我们回家,车钱照例不肯收。那阵子,母亲做生意赚了些钱,虽然忙得很,但去看外婆的次数却多了。阿茂常常送我们回来后,进来坐会儿,母亲借机劝他去医院。他总是答应得很干脆,但再被问起时,却不好意思地搓着手。
就这样,一年过去。阿茂家翻盖新屋了,新屋快造好的时候,阿茂和妻子送了许多新鲜蔬菜过来,还说下个礼拜办敬屋酒,请母亲一定要去。后来我才知道,阿茂家翻盖新屋所缺的钱,是母亲帮忙垫上的。
敬屋酒最终没有喝成,因为阿茂忽然晕倒了。大家都以为是劳累过度,谁知两天后的夜里,有人拼命地敲门,我开了门,来人一下子攥住我的手,连声问:“你妈呢?你妈呢?”是阿茂的妻子,她语气慌乱,手不停地颤抖。母亲闻声从卧室出来,还没来得及问什么,阿茂的妻子就放声痛哭:“阿茂他……医生说他是胃癌……晚期了。”母亲的脸忽然煞白,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
第二天一早,母亲去医院看阿茂。阿茂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但精神还好,看到母亲,他还是一副腼腆羞涩的样子。母亲坐在床边,边聊天边削了一个梨给他,他有些受宠若惊,语无伦次。母亲几乎天天去看他,每次都带些好吃的。最初两个月,阿茂还有一丝好转,虽然医生预言他只有4个月了。
到了深秋,尽管谁也没说出真相,但阿茂还是觉察到了什么。一天,母亲又去看他,喂他喝了点儿汤。喝完,他看了妻子一眼,他妻子说要买东西,便出去了。阿茂久久地凝视着母亲,说:“我早就知道这病了,但我不怨。不为这病,你也不会在这里陪我,我阿茂实在是有福之人。”他握住母亲的手,直到他妻子回来,也没有松开。他妻子愣了一下,接着像没看见一样,继续忙。后来,只要母亲去看他,他一定挣扎着起身,握住母亲的手,尽可能保持清醒,直到再次昏睡。
冬天来了,阿茂已经瘦得吓人,对母亲也越来越依赖。母亲去外地出差3天,回来的当天,就冒着大雪去了医院。阿茂昏睡着,他妻子告诉母亲,他已经连续3天拒绝进食了,总是呼唤母亲的名字。母亲很歉疚,想解释什么,阿茂的妻子却抢先说:“我都懂,对你我只有感激。”
阿茂醒了,见到母亲很开心,还和朋友们说笑了一阵。傍晚时,母亲喂他喝了几口稀饭。等母亲要走时,他嘴唇动了动,母亲俯下身子听了一会儿,脸红了,眼里有泪。阿茂的妻子好像明白了什么,转身离开。母亲的泪水盈满眼眶,她低下头去,吻了吻阿茂毫无血色的唇。阿茂满足地望着母亲,很快又昏睡过去。
半夜一点,家里的电话忽然响了,根本未合过眼的母亲冲过去抓起电话,我隐约听见了嘈杂的人声夹杂着哭声。放下电话后,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满脸是泪。
又一个春天的傍晚,阿茂家孙子满月,母亲和阿茂妻子都喝了几杯,阿茂妻子忽然不好意思地问:“有件事一直想问你,阿茂走的那天下午,对你说了什么?那是他这辈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母亲犹豫了一阵,红着眼睛说:“他要我亲他一下,说那是他最后的愿望。”
(宋晓月荐自《情人坊》)
责编:小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