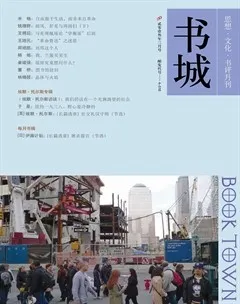胡风、舒芜与周扬们(下)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胡风并不安于座谈会以后的暂时平静,他开始把目光转向高居周恩来之上,转向真正能够代表党的毛泽东。这应该是他要坚守党和真理的一体化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胡风走向最大的精神迷恋的开始,他也逐渐把自己的悲剧推向顶端。
其实,建国以后,胡风一直在寻找和毛泽东之间的通道。早在一九五○年,他就再三关照梅志要“给领袖寄书”,具体对象是“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副主席、胡乔木部长”,寄的书有胡风自己的著作《为了明天》、《密云期风云小纪》等,译作《山灵》等,还有所编辑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如冀汸《走夜路的人们》、路翎《燃烧的荒地》等,在胡风看来,让党的最高层了解自己和朋友们的工作,是“和大斗争有关的”,因此十分郑重其事。一九五二年他的《欢乐颂》、《光荣赞》等歌颂党和毛泽东的诗集出版后,也特意关照梅志:“先寄大头”,即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领导;至于宣传部、丁玲等,“可以慢点再看。这些毫无用处,反而要刺激他们的。除非最上面奇迹似地良心出现,不会有什么用的”。他显然对“最上面”,特别是毛泽东的“良心出现”,抱有极大期待与信心。
胡风还习惯于通过报刊研究、琢磨“上面”的意图和政治动向。就在召开座谈会期间,适逢鲁迅逝世十六周年,他看《人民日报》社论(1952年10月19日),突然发现“三年多以来的一件大事,在文艺思想上透出了一股新的气象”。他喜出望外,急忙写信给梅志:“社论,那是转了大弯的,肯定鲁迅比过去一切都超过,反对复古,这都是自己打了自己的。总之,问题不简单。”根据胡风的提示,我们找出了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纪念鲁迅逝世十六周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鲁迅)这一份遗产超越于前代所有的民族遗产之上,必须由我们来继承它,这是毫无疑义的。接受这个遗产,不疲倦地阅读、研究和宣传鲁迅的著作,决不仅仅是文艺界的任务,决不仅仅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任务,而是全体革命人民,首先是全体共产党员及其干部的任务。”另外还有一段话:“有一部分人采取了粗暴的态度,对于民族遗产胡乱加以‘审判’;又一方面是另一部分人把所有旧的东西都当成宝贝的遗产,一概都‘不要动’。这两部分人显然都是错误的。”胡风所谓“肯定鲁迅比过去都超过”、“反对复古”,大概就是根据这两段话。其实,客观地看,这不过是照例的纪念文章:建国以来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鲁迅祭日,都会有这样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而且,无论是对鲁迅的肯定,还是对民族遗产既反对粗暴否定又反对全盘肯定的态度,都没有超出毛泽东的相关论述的范围。以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这就是一篇普通的社论,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没有产生、本也不准备产生任何影响。但在胡风的主观观照下,就读出了特别的意思,被赋予了重大的政治意义。他断定,“这完全是我的意见”,以为自己在与周恩来、周扬谈话里发表的意见已被高层所接受。于是,他又进一步断定:“这是最高者(按:指毛泽东)底意见。可能还是经他改写的。”进而作出极为乐观的思想文化政治形势的判断:“三年以来向封建意识投降的潮流终于不得不受到了注意,非给以扭转不可了。”在另一封信里,胡风又根据从林默涵那里得知的一个传闻—“主席最近又把鲁迅著作看了一遍”,作出推断:这“当然是由于整个思想界及文艺界底枯死状态引起的。也当然不只看鲁迅而已。希望能有一个新局面出现,至少开出一些新路”。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胡风出于主观愿望的主观臆断,甚至是主观幻觉。但胡风却是十分严肃,也十分真诚地凭借这些主观臆测,观察与分析政治形势,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政治行动。
然而,对于胡风如此易于陷入主观幻觉,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同情的理解。据绿原回忆,胡风在座谈会以后,就处于几乎无法工作的境地,他写下的文字已完全没有可能发表。因而,他陷入了选择的困境:既已丧失了公开发言权,就无法将他和文艺界领导的分歧公之于读者;但如果就此沉默或埋头著述,以求未来历史的公正评价,那是胡风难以接受的命运,因为他有着极强的现实责任感与参与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就视党中央与真理为一体的胡风,希望最高层来解决问题,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但胡风作为一个党外知识分子,根本无法了解党的高层情况,就只能依据公开发表的党的文件、社论来作主观的猜测,这其中的无奈,后人确难想象,却也不能因此而苛求历史的当事人。
这也是绿原回忆的:一九五四年初,胡风和朋友们达成一个共识:要“向中央上书言事”,以求问题的公正解决。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会议发表了公报,《人民日报》也发了社论。胡风当然不知内情,如他自己在《三十万言书》里所说,“近二十年以来,对于严格的党内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式,我是完全生疏的。”但既已渴望知晓上层情况,政治上又极敏感的胡风,对这多少揭露了中共上层分歧的新情况,自然要从中探测对他有利的信息。他立刻注意到《人民日报》里的一句话:“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本来是指高岗在东北搞所谓“独立王国”;但胡风却立即联想起自己和朋友们(如路翎、阿垅)这些年所受到的“压制和报复”,进而断定:党中央所要批判、打击的独立王国,应包括周扬等把持的思想文化战线和文艺界。胡风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推断,一路想下去,就觉得这是党对自己的召唤。他说:“阶级斗争正在向着更艰巨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文艺战线的“萎缩和混乱”,“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再不正视问题”,投入战斗,“就更不能有任何藉口原谅自己了”。可以说胡风是怀着挽救党的文艺事业、不惜牺牲的党性精神去作最后一搏的。但他这一搏,又是建立在对政治形势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不管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的迷误,但这次悲壮的一搏,还是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文本:《三十万言书》,其正面和负面的意义,都凝聚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三十万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对建国后党的思想、文化领导的历史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胡风尖锐地指出,这样的领导追求“完全的统一”,从创作指导思想,世界观,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对象到创作题材、形式和创作方法,以至具体的创作手法、风格等等,无不有统一的规定,并形成理论上的清规戒律。其二,这样的领导,又是“宗派独占”的,一切由党的领导人说了算:“只能由我直接‘培养’,只能由我直接‘改造’,只能由我批准‘发表’,等等。”这样的由党的领导人垄断的“理论统治权”和“作品的判决权”,就必然导致“把宗派利益当作不容丝毫变动的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意识地来维持军阀统制”。其三,这样的领导,必然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管理文艺,“一切都简简单单依仗政治,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完全忽略了文艺的专门特点”,而且采取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来强制作家改造思想,把作家的创作强行纳入既定的轨道。—尽管胡风当时的批判,只是针对他所说的以周扬为首的“宗派集团”,但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所批判的追求“完全的统一”、“党的宗派独占”,以及“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正是建国以后所建立的思想文化乃至文艺体制的问题,而且延续至今,而绝非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思想、作风问题。胡风的批判,其主观动机绝对是要维护毛泽东的统制,但他的批判锋芒,客观上至少是触及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文化统制的某些要害。
胡风的批判揭露了一种统制式领导给文艺创作带来的困境。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理论戒律,这样的思想统制,必然“闷死一切创造性的种子”,造成文艺创作的“混乱与萧条”。胡风如此描述作家动辄获咎的“惶惑”状态:“谁的作品里写了否定现象,那就是‘不真实’。谁的作品写的工农兵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故事,那就是歪曲了革命,是小资产阶级。谁的作品里写的革命斗争有了牺牲者,那就是散布悲观情绪,是小资产阶级。谁的作品里写的工农兵也有‘落后’的思想情绪,是在斗争中得到成长,那就是歪曲了工农兵,是小资产阶级。谁的作品里把敌人写得复杂一点不像纸人一样,空空洞洞,一碰就倒,那就是立场不稳。”他还说到批评界的问题—“批评界惯用的‘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或‘我们的人民是这样的吗?’成了一个流行的公式和棍子。”在这样的淫威之下,作家只能停笔。应该说,这是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里的批判最能引起作家共鸣之处,是其最有力量的部分。

在批判周扬等人的同时,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也在探讨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艺体系和秩序等问题。他更看重创造实践(他提出作家可以通过创作实践而接近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意思),强调创作个性,主张创作民主和自由竞赛,并提出一系列“文学运动的方式”的建议,如以“劳动合作单位的方式”办刊物,实即办同人刊物,“工作单位不能限制发表自由”,作家“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完全废除强迫学习制度”等。尽管未能充分展开,却都是很宝贵的思想。
《三十万言书》的问题,可能在于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思维去观察、分析文学艺术问题,处理文艺论争。其所有的论述都基于“阶级斗争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这样一个整体判断,而这个看法正是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必然日趋尖锐化”的错误理论导致的错误估计。从这样的估计出发,就必然要寻找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揭发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因此,胡风对周扬们的批判,最后都集中在这一点,即“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宗派主义统治”,“无论从事实表现上或思想实质上看,已经发展成反党性质的东西”,是“以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党的;而且“为了巩固他那个宗派主义的统治,为了维持他那个小领袖主义的‘威信’,甚至竟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归过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敢于瓦解没有直接接近过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对于党中央的信任。他的破坏团结的手段,就由党外到党内,以至直接指向党中央”。—这样,胡风就实际上将当时的文艺界领导定性为一个“以周扬为中心”的“直接指向党中央”的“反党”集团。胡风对此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他说“周扬同志居然忍心到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分析到这里,我的心里涌出来的悲愤强过了憎恶,全身火烧一样”。尽管胡风主观的真诚无可怀疑,但客观上这些言辞已是对自己思想上的论战对象进行严重的政治指控,希望借助最高权力的干预置论敌于死地(党中央刚刚处理过高饶反党集团,已有前例可循)。这样做显然是过了线。
同样的手法也表现在对舒芜的指控。《三十万言书》首先继续揭发舒芜的所谓历史问题,重点在揭露舒芜“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其次又直接引用舒芜给他的四封私人信件,以证明舒芜品质的恶劣。其三,则揭发舒芜私下的谈话,如“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采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他还告诉了我几件党内情况,其中有关于毛主席的”。最后,谈了自己的“一点感觉”:“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党内常常发现‘破坏者’。有的时候甚至打入了中央领导部;当时我不大理解敌人为什么这么巧妙,党内的同志为什么这样没有警惕性。现在看了舒芜的做法,我在实感上才似乎懂得了破坏者是怎么回事,是通过什么空隙打进党内的。”结论是:“舒芜是尽了‘破坏者’的任务的。”
这自然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指控:所谓“破坏者”就是敌人打进党内的内奸。其具体罪行是“他恶毒地利用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庄严的武器”,“造成了解放以来公开地破坏团结的最大的事件”,“特别是在作家中间,造成了对党不信任,对党恐惧和对党作伪的消极心理”,是一个“品质恶劣的欺骗者”。这就是说,舒芜不仅在历史上是“叛党分子”,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起到了“反党”作用的。胡风对舒芜的不满、憎恶,都可以理解;但利用私人信件和谈话,对他进行政治指控,也就过了线。
问题是,胡风这样指控周扬们和舒芜时,和我们前面分析到的舒芜对路翎的指控一样,他也是视为理所当然,十分自然,毫无道德压力,甚至是充满道德的正义感的。在这背后,有三条“充足理由”:一是出于党性。在胡风看来,向党揭发“反党集团”和“破坏者(内奸)”,是自己的责任,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也就是维护真理,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正义性。而且,在党的面前,在集体主义的最高原则面前,一切都可以,而且应当向党揭发和报告,在信奉党的至高无上性的党化社会和文化里,是不存在个人隐私权的概念的。其二是出于敌对思维。既然认定对方是敌人(舒芜)或敌对势力在党内的代表(周扬们),就可以对之采取一切手段。其三是出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既然周扬们、舒芜已经将自己置于死地,那么,自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绝对合理的。而以上三条理由,又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公共伦理,而且据说还是共产主义新伦理。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这样的新伦理取代常识性的人类基本伦理,也即我们说的“底线”。突破底线,就成为“思想进步”的表现:这样的精神迷误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个人自有责任,却不宜过分追究。
胡风最后一次“公开发言的绝唱”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将他在朋友们的协助下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的《三十万言书》亲自交给了时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习仲勋,请他转呈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焦急的等待中,突然听说毛泽东在十月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口头指示,紧接着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指责说:“《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胡风立刻认定,这是自己的《三十万言书》发挥了作用,他兴奋地写信告诉上海的朋友“这里的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这里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由此作出判断:“缺口已打开”,并立即提出“一定要从这缺口扩大到全面”,因为“这斗争,是老先生(指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胡风显然认为他已经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一再强调:“(《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和仇视青年,是老先生提出来的”,他还用了“中枢确定”的字样。另一封信里,他还透露了不知从哪儿打探来的“中央态度”:文艺界要有大的变动。他据此而分析形势,断定“斗争正在展开,封不住了。现在是斗争决心、斗争力量、斗争方式的问题”。于是,他摆开架势,准备和他认定的周扬反党集团拼死一搏,以作“总的算账”。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胡风的这些形势分析,完全是一种出于主观愿望和想象的臆断。但这一回,他采取了断然行动,而且动员了所有的朋友,可谓孤注一掷,结果自然十分惨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七日、十一日,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连续作长篇发言。有意思的是,胡风发言前还是有些犹豫,是周扬先动员他发言,接着又有人来劝说,那位“才子集团”里的乔冠华甚至鼓动说:“为什么不发言?越尖锐越好!”胡风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将多年郁积的怨愤一泻而出。一面有意突破会议预定的只批评《文艺报》的限定,扩大为对周扬“宗派”(因是公开场合,未点明“反党”)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清算,另一面为证明周扬们“向资产阶级投降”而明确宣布朱光潜等都是“思想战线上的敌人”,点名俞平伯、徐志摩等“都是属于胡适那个系统”。这样,就把问题归结为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和“小人物”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腐朽力量”和“大人物”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胡风两篇发言一口气点了他认定的党内外十个资产阶级“大人物”的名字,这样的全面开弓,实际上也就在文艺界孤立了自己,反而将自己置于不利的地位。当胡风以“湖北人独特的嗓门”,“声音高亢”地慷慨陈词时,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以后历史学家所说的,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公开发言的‘绝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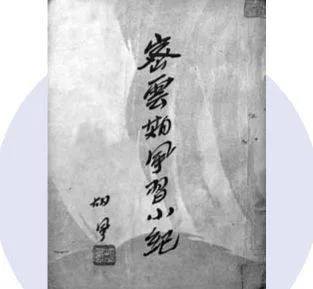
周扬们迅速反击,而且是真的(而非胡风式的幻想)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同一个讲坛上,周扬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批准和修改的《我们必须战斗》的长篇讲话,又重提舒芜的《论主观》,并且代表党正式作出判决,说“这是一篇狂热的宣传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纲领式的论文”,并且指明胡风支持《论主观》,实质上是和毛泽东的《讲话》对抗,转而又谈到以后舒芜的转变,特意指出:“党对他的这种进步是表示欢迎的,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恨。这就是胡风先生对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态度。”这样,周扬就把胡风对舒芜的不满,看作是他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的表现,也就自然拒绝了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对舒芜的指控。接着,周扬对胡风在联席会上的发言和《三十万言书》里对自己的思想、理论的批判,一一作出反驳,大谈“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以证明自己所代表的“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而胡风则是有“计划”地要“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讲话最后号召要对于“敌人和敌对思想”展开坚决的斗争;这里所说的“敌人和敌对思想”除了一开头即点名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还同时包括了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这就第一次以党的名义,将胡风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敌对思想”。直到这时,胡风才意识到自己已铸成大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如此自责:“被斗争的需要和中枢决心所鼓舞,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没有负责地分析具体情况,责任主要在我。愧对党和事业,愧对战斗者。”为承担责任,胡风决定作自我检讨,但为时已晚。
舒芜交出信件及其后果
周扬们则抓住时机,对胡风展开全面批判。舒芜作为一枚棋子,自然要再度启动,又一次被推到了第一线。他应约写《关于胡风宗派主义》,《人民日报》也是以此为题向舒芜约稿的,舒芜表示他原也有“写这个题目的考虑”,那么,这是党的领导的意图和舒芜自愿的一个契合。此时的舒芜已经认定必须“在具体工作上,经常地、密切地、真诚地、毫无保留地拥护党的领导”,而且“党的领导”就是具体党组织的个人领导,这是他在刚写的《给路翎的公开信》里说明了的;因此,他对胡乔木出的题目采取主动、积极配合的态度,是很自然的。他在文章里引用了胡风的信,以后《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借阅原信,他毫不犹豫地全部交出,也都是自然的。这背后依然是我们在前文已经作了详尽讨论的所谓“党性原则”:在党面前,应该是“毫无保留”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舒芜与胡风陷入了同一个思想陷阱。但是,舒芜所引述、交出的私人信件不仅在数量上远超过胡风的引述,涉及人更多,所造成的后果也要严重得多。在历史的讨论里,这样的数量和分量乃至后果问题,是不能忽略不计,而必须认真研究的。
在当事人《人民日报》编辑叶遥的回忆里,谈到她和编辑部的袁水拍等负责人看到胡风和他的朋友间的私人通信,“是吃惊的”,“尽管有些内容不知指向何人何事,但讥讽、谩骂的话大体上是能看懂的。当时认为胡风同志和他的朋友们确确实实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这样的反应是很值得注意的。曾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胡风的书信写作的语言特点,称其为“密语写作”。胡风的书信充分地显示了他的“隐秘情感,特殊的嗜好,行为习惯”,“交往方式”的个人性,他“性情激烈,情感偏执”,有一切“向坏处分析”的思维习惯,把所有的行动都视为一种“战争”,喜欢像“久经战场的将军一样作着战略部署”,等等。所以,在他的书信语言表述中,“恨恶爱憎”不但鲜明而且“加以想象性的夸大”,仿佛不断在进行宣战,具有极强的进攻性。而且,这种“密语”式写作方式又充满暗示、象征,仿佛在进行各种密谋。这样的个性化表述,在特定的私人圈子里,是可以心领神会而相互理解的。但一旦公之于众,就会有令人“吃惊”的效果。如果加上意识形态的解读、阶级斗争逻辑的推论,更会产生可怕的联想。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正是意识形态、阶级斗争逻辑全面渗透全民族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的时代,如舒芜晚年反思时所说,“每一个人的日常的一思一念,一言一动,一律拔高归类为某个立场、某个阶级、某个倾向、某个主义,从而判定其是非善恶、进步落后、革命反革命”。居于这样的思想和心理氛围,人们很容易从胡风的书信里读出,实际是想象出:一个仇恨一切,代表被打倒的阶级,时刻准备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一个躲在阴暗角落,窥测方向,进行密谋的“阴谋家集团”。这样的群众动员力量和效果是绝不能低估的。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读了报纸上公布的胡风及其朋友间的通信,就觉得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所写的东西,他和我所生活的“新社会”,无论是生活世界、交往方式,还是思维习惯、语言方式,都大不相同,我确实大吃一惊,困惑不解,几乎本能地排拒,因而毫不困难地就接受了“编者按语”里所作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分析,甚至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党所作出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最后判决,也就理所当然了。像我这样的反应大概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感到困惑的,不仅是对内情完全不了解的普通群众,还包括信件直接牵连的当事人。绿原就有这样的回忆:“那些反映双边关系的信件,本来彼此并无联系,一旦搜集在一起,经过精心编排,互相衬托,竟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印象。除了阿垅、方然和我解放前夕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邮检’而采用的几句反语,我能够而且必须根据真相加以澄清外,其中一些牢骚、怨言以至谩骂之所以然的复杂背景,一时间实在说不清楚。因此在审讯人员咄咄逼人的质询下,面对这些所谓‘真凭实据’及其明显的构陷动机,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就是不认也得认了。”
这就是说,舒芜提供的胡风私人通信,不但给当局提供了“罪证”,而且为此案的最后判决制造了群众基础,给被牵连的当事人造成了有口难辩的困境。“胡风反革命案”这一建国后第一个最大的文字狱得以顺利实施,这是一个关键环节。这当然是舒芜完全没有料到的,绝非他的主观愿望,也非他的主观意志所能掌握,但却是必须正视的实际后果。
而且,舒芜自己也要承担将这些信件进行意识形态化处理的任务。这任务是舒芜心目中的党的代表林默涵交给他的。据舒芜晚年回忆,林默涵对他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般的宗派主义的问题了,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是,是对党、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对党的文艺政策、对党的文艺界的领导人的态度问题了。”林默涵把“已经在原信上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的信”还给舒芜,并且布置说:“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党的代表下达这样的任务,当然是必须接受的,也是当时的舒芜所愿意接受的。但这一接受,就又落入了两个陷阱。
其一,这是先有了结论和判断,然后再对信件里的材料任加裁剪,以证明判决的正确,即先定罪,再找罪证。这就必然完全不顾客观事实,其中的断章取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限上纲,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其实就是后来在“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发展到极端的“大批判”思维和手法。
其二,林默涵要求舒芜把他划定的、认为有问题的材料摘抄出来,分类整理,实际就是要按照他的也即党的意志去编排材料,这就使了解实情的舒芜陷入了困境。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胡风给舒芜的信中提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句话,在林默涵看来,这是大有问题的,自然应该大做文章;但舒芜的心里很明白:这句话是他自己在给胡风的信里说的。这样,舒芜就面临两难选择:是尊重事实,还是不顾事实,按党的意志去上纲上线?当时已经“以代表党的负责人的是非为是非”的舒芜当然(我相信也是不无困难地)选择了后者。于是,在他编排的《材料》里,就出现了这样的《按语》:“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甚么‘主观在运行’,甚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样的移花接木,在历史的当时,可能是出于无奈;但在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却自会有更严峻的判断。
这样,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周扬,林默涵等)就通过舒芜整理的材料,对胡风和他的朋友提出了严重的政治指控,指明他们是一个“一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的领导、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的“反党宗派”。这同时也是舒芜对胡风们的控告:他在整理《材料》的同一月写的另一篇批判文章里,也指明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说胡风“‘鲜血淋漓’地诬蔑了中国人民,诬蔑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那种咬牙切齿的声音,充分表现出反对资产阶级对革命人民‘火一样的仇恨’”。
如果联系到前文已经分析了的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也同样指控周扬等是一个“反党”集团,舒芜也是一个“反党”的“叛党分子”,就可以发现一个极耐寻味、极应反思的思想文化现象:我们所讨论的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无论是周扬们,还是胡风们,以及由胡风转向周扬的舒芜,都不愿意把彼此的争论限于思想范围,而要对对方进行政治指控,而且指控的是同一罪名:“反党”;更重要的是,决定他们作出这样的政治控告的内在动力,是同一个将党与真理同一化、视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毫无保留地把一切交给党的“党性原则”(尽管他们对“党”的理解并不一样),支配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的,也是同一的“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和“对敌人可以采用一切手段”的阶级斗争伦理。而他们最后置敌于死地的撒手锏,都是直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控告,把决定生死的裁定权,也即自己的最后命运,交给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周扬们,胡风们,以及舒芜,他们之间的搏斗,其实就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相互残杀与集体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