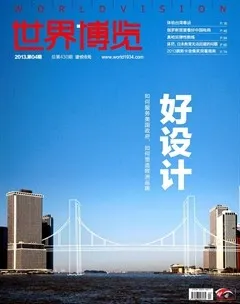美国海洋局的中国设计师
打开刘哲的网站,乍一看有些无所适从,没有人会怀疑这属于一位设计师——主页上只有竖排的6个数字,和右手边一行小字“刘哲平面设计”;数字上有个虚线的十字,鼠标无助地在屏幕上晃来晃去,十字中心瞄准的数字便跳跃起来,像是打靶,又像是音符在律动。幸好的是,只需要多晃动两下鼠标,就能摸透如何使用;否则过分流于设计,用现下流行的话说,就是矫情了。
刘哲是个平面设计师,这个网站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匠心独运又简单明了,摆在观者面前,抢眼之外就能让人会心一笑。
走在别人前面
就如网站没有中文版那样,定居华盛顿多年的刘哲,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落脚点都是美国。随着中国风向世界各地劲吹,西方设计师中站得住脚的黄种人也不算屈指可数了,但这些人大都是亚裔、华裔,中国人仍不多见,尤其像刘哲这样,像传统的中国理工科学生一样一步步从中国走到美国。
现在,就连纽约的帕森斯设计学院,这种殿堂级的设计学校都已经是中国梦想学设计的学生们耳熟能详的了,更有网上一些小广告自称可以帮助考生读帕森斯的预科,或者干脆以较低的语言成绩录取。但在20年前,学美术的人都不多,中央美院还没有设立设计系,动过出国学设计的念头的人就更少了。
刘哲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学习美术的。他是科班,十几岁时在北京工艺美校学绘画。“那时我就已立志将美术作为终生职业,”刘哲对《世界博览》记者说。高考时,顺理成章,刘哲进了中央美院,成了中央美院设计系第一届的学生。
“都说报考中央美院的有三种人:天才、勤学苦练者、自不量力者,我是第二种。”刘哲的言谈中没有艺术家身上不鲜见的狂傲,也没有妄自菲薄,他娓娓道来的经历诠释着对自己“勤学苦练者”的定义。
刘哲很少提及灵感、天分,而是像个理科生,强调“提高技能、探索思考”。本科四年后,他工作了4年,期间还在北京青年报任美术编辑,正是这一段经历促使他后来选择公职而不是从事商业设计。当时刘哲的身边并没有出国的氛围,“身边搞艺术的很少留学,有个在美国的好友对我说,全世界最好的艺术与设计在美国,你为什么不来长长见识?”两年后,刘哲获得萨瓦纳艺术与设计学院(SCAD)奖学金赴美留学,硕士毕业后进入美国商务部海洋局担任资深设计至今。
勤学苦练
到了美国和SCAD,刘哲确实长了见识,直至今日,提起母校,他还是赞不绝口,尤其是该校“在教学方面特别注重个人风格,偏实用性,培养出的学生能很快满足业界需求,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艺术家”。
“实用”是中国留学生们在赞誉外国教育时的常用词;但词汇背后是“不适应”甚至“痛苦”。刘哲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实用教育”讲究的仿真现实中的工作,老师们强调“the real world(现实世界)”。在SCAD学习时,每堂课每个项目动笔设计前都要写论文阐述设计思路,课上要演讲、分析自己的作品;另外,老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经常以小组为单位共同完成一个作品。最后,几乎每做一个项目都有校外公司或机构参与,也经常邀请业界专家来校演讲或参与作品评审。
这种仿真,尤其是阐述分析和团队合作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悲喜交加的。喜的是,这才是出国受教的精髓;悲的是由于在国内缺乏实战类的训练,再加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常常令人无所适从,无法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还有一些对于西方学生理所当然的事儿,到了中国学生这儿就慢了半拍。“比如说我们这些‘老外’刚来美国的时候都不清楚英文字体serif(有角体)和sans-serif(无角体)的发展演变及字体与设计的相互影响,不了解这些字体背后的文化就无法正确应用。”还好学校就理论研究设置了非常系统的课程,所学的知识又在实践中一再被强化,现在刘哲在英文字体的应用上也能驾轻就熟。
在他看来“设计师必须永远走在别人前面”,但毕业后的刘哲没有冲到市场的前面,却做起了美国的公务员。他觉得,自己的选择和当初在北京青年报的工作经历有关,这让他“对服务大众、公共事业怀有强烈兴趣。”
吃官饭,有道理
2012年夏天,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北美地区最大规模的创意与艺术展Artomatic,其中就有中国艺术家刘哲的系列油画《湿地2012》。该系列作品描绘了湿地美景与生态,简约宁静、浪漫纯粹。没有奇幻色彩或高科技因素,就像一幅心平气和的写生,让人无法和创意与设计联系到一起。
“设计于我来说就是用创意巧妙地解决问题,”刘哲说。为了能尽情地挥洒创意,他没有去专业公司。专业公司就是设计或广告公司,商业化和市场化必然以盈利为导向,盈利由收支决定,也就要求经费越少越好,客户越满意越好。“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创意的发挥,”但却也无需给拒绝了商业和市场的刘哲戴高帽,柴米油盐的人生不可能忽略收入,而美国政府恰恰愿意出银子让他去带着一颗科研心去搞创意,何乐不为。
海洋局的很多基础研究都是”银子落水不停响的”,需要常年累月搜集数据,如某片海域哪有礁石、海水有多深、季节性气候如何、发生风暴时水流有多快、浪有多高等。这些数据每天向全球公布。这些研究需要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并且因为是基础研究,可能很多年才能看出效果。
刘哲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工作,“没有一流的服务意识很难坚持,美国政府服务性非常强,设计应不仅是为商业服务,更重要的是为整个社会发展、人类环境服务。这种服务理念也深深影响我的设计,限制相对减少,创作会更自由,”也就可以理解刘哲为什么经常提到责任、社会发展之类的“大词儿”了。
唯一的设计师
“我每天的工作是与科学家们讨论,围绕海洋及大气环境进行艺术创作,为某一最新项目做主题包装,为他们提供艺术与设计指导,”如果按照专业工资的职务层级和人力资源分配看,刘哲是设计部门的光杆司令——他不仅是唯一的中国设计师,也是唯一的设计师。
他的同事都是美国权威的气象和海洋专家,和他们讨论设计方案,在专业上是个大挑战。艺术和科学一样,既需要事实还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为科学服务的艺术家想有的放矢,就要多和科学家沟通,而不能在一窍不通的情况下闭门造车。
经过2年的美国学习,刘哲已经适应了团队合作,他也意识到“一个有灵魂的作品不仅仅是设计,还应包括与团队的有效沟通、多学科的知识与思考、融会贯通并最终运用视觉语言巧妙地表达。”
当然,除了学习学科知识,还要体验生活,就如这次展出的湿地系列油画。科学家能够滔滔不绝地解释洋流,却无法形容湿地的鸟兽虫鱼,更不会注意紫色的暮霭。由于工作关系刘哲去过很多美国沿海湿地,参与过不少保护湿地活动,湿地独特的地貌与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次进入湿地,总能看到乌龟一家在路边散步,水蛇在爬,鱼鹰在捉鱼,鸟鸣声不绝于耳……一片和谐美好。”
抽文:中国不乏年轻设计师,缺的是十年以上仍保持活力的高级甚至大师级设计师。
图说:
1. 最得意:保护珊瑚礁标识是我在海洋局最得意的作品。2010年我担任珊瑚礁保护项目艺术指导,设计的过程十分复杂,要反复与科学家商讨,还必须了解珊瑚礁生存环境、气候变暖甚至海水酸化等专业背景知识。当最终决定跳出珊瑚礁的思路而聚焦依赖其生存的鱼类,并通过正负形的方式刻画其生态链相互依赖的主题,这一尝试好评如潮,有力的推动了该项目在全美推广。
2. 最难忘:研究生时为AOK做的保洁品品牌与包装设计,其中AOK沐浴系列瓶身设计获得了美国专利。该系列分为洗发水、浴液和剃须液,它们的瓶子造型独特,自带吸盘可以贴在浴室墙上,瓶身全黑无任何文字图案,通过容积大小识别。之所以有这个设计是出于个人体验,浴室里通常光线不足,有蒸汽,特别想要一个可以简单识别的设计。后来发现吸盘这个东西在生活中运用的很多,但从没与护肤品保洁品联系起来。
3. 最纠结:把国会报告做成艺术杂志。珊瑚礁系列报告每年要递呈国会,传统的国会报告非常枯燥,我采用大量视觉元素使其图文并茂。当时就是墨守成规还是突破创新与同事讨论了很久,最后选择了艺术画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