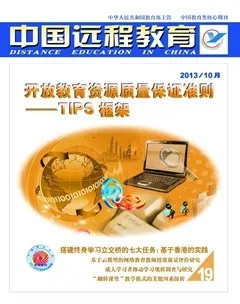开放教育资源质量保证准则——TIPS框架
【摘 要】
目前开放教育资源被看作是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一种可行办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无论是引进和改编发达国家的开放教育资源还是开发本土开放教育资源,发展中国家都能够从中受益。本文所阐述的这些准则旨在为中小学教师提供一些思路,使更多教师加入开放教育资源建设行列。换言之,教师在开发自己的开放教育资源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些准则。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开放教育资源的开发或每一位教师都必须逐一对照这些准则, 制订这些准则的目的不是为了规定一定要怎么做,而是要在有兴趣自己开发开放教育资源的教师当中形成一种质量文化,鼓励他们进行专业反思。学生在自建学习资源的过程中能很好学到终身学习所必备的更高层次批判性思维技能,所以这些准则的目标对象也包括可能想通过自建学习资源进行学习的学生。本文所提出的准则框架尚在完善之中,因此希望得到用户的反馈以进一步完善。本文介绍较为简略的TIPS框架,T代表教学和学习(Teaching and learning)过程、I代表信息和材料内容(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content)、P代表呈现、产品和格式(Presentation, product and format),而S代表系统、技术性的和技术(System, technical and technology)。
【关键词】 开放教育资源;质量保证;准则;TIPS框架;制作数字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3)10—0011—12
导读:2001 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启动了“开放课件”项目,拉开了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序幕。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给“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简称OER)下定义。十几年过去了,这场席卷全球的教育运动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期间,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保证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诚如本文作者保罗·川内(Paul Kawachi)教授所指出的:“不同层次的用户对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适合某一层次用户的标准可能不适合其他层次用户。正因如此,由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林林总总的质量保证框架各有千秋但似乎不兼容。在这个背景下,川内教授受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亚洲教育媒体中心的委托,开展了开放教育资源质量保证准则框架的专项研究,旨在批判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更加全面的质量保证框架。
作者首先分析了开放教育资源的背景、质量保证准则的理论基础和有代表性的开放教育资源定义。文中所提出的开放教育资源的本土化(localisation)、整体更新(globalis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和全球通用性(world-readiness)对于我们更加科学合理、从不同目标用户的角度开发、使用或重新利用开放教育资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作者把教师(和学生)作为制订质量保证准则框架的出发点也是其他现有框架所不及的;作者还博采众长提出了一个与时俱进、涵盖面更广的开放教育资源定义。文章的第二部分阐述了框架的制订过程,与通常把质量当成是产品或过程的观点不同,本文提出质量是一种文化,尤其是一种专业反思文化。作者分析了与学习资源密切相关的15个质量标准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由四个维度组成、包括19个子维度、共65条准则的TIPS框架(详细准则在第三部分以表格形式呈现)。
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第一,质量是一种文化。我们并不是说不能把质量看做是产品或过程,但是把质量作为一种文化则更有统领力,这是因为好的质量文化必定会产生优质产品、优质过程。第二,聚焦学习效果(教育目标)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教师和学生。TIPS框架以影响学习效果并涵盖所有已知的教育目标的五个学习领域(Domains of Learning)——认知领域(Cognitive Domain)、情感领域(Affective Domain)、元认知领域(Metacognitive Domain)、环境领域(Environment Domain)和管理领域(Management Domain)——为基础,由此可见这个框架的“草根性”。我们无意贬低专家视角下的标准或准则(事实上专家在TIPS框架的制订过程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服务学习、提高学习(教学)效果,因此,作为开放教育资源终端用户的学生以及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终端用户”的教师,他们的观点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第三,TIPS框架的开放性。文章多处提到鼓励教师和学生及时把自己使用这个框架的经验和体会反馈给作者,也计划今后继续通过交流、咨询、研讨会等形式吸收各方建议,不断修改完善框架的准则。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理论唯有与时俱进才能对动态的实践具有真正的、适时的指导意义,否则,不但不能促进实践水平的提高,反而可能成为实践发展的障碍。
早在2013年1月份开放教育资源质量保证准则框架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川内教授就欣然接受本刊稿约,答应为我们撰写一份研究报告。经过近半年的反复磋商,这份报告终于跟我们的读者见面了。我们谨此向保罗·川内教授致以衷心感谢!(肖俊洪 杨伟燕)
引 言
1. 开放教育资源的背景
目前开放数字化可重用教育资源运动席卷全球。大多数有关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和开放教育实践(open educational practice)的报告都会首先澄清作者对相关术语的理解和定义,特别是对诸如“开放教育资源”、“开放内容”(open content)和“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这些表述中“开放”一词的理解。十年过去了,开放教育资源的历史定义基本上还是有效的,在法律层面保护任何人无需支付版税、无需向版权所有者申请复制资源的许可便可合法重新利用开放教育资源。开放教育资源的历史功能定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2, p.1)给出的,意为“借助技术实现的、开放式的教育资源,供非商业用途的用户社区参考、使用和改编……通常可免费在网页或因特网上获取。”简而言之,开放教育资源指的是可以自我测评的、独立的教学小单元,具有可测量的学习目标,通常以数字电子格式呈现,一般可供免费使用。
开放教育资源的历史与早期的可重用学习对象(reusable learning objects)有一些相似之处,早期的可重用学习对象运动在成本和可持续性上有些困难,从目前情况看,给开放教育资源附加开放许可协议,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可重用学习对象所遇到的问题。可重用学习对象是不针对具体环境、免费的小块教学内容。“学习对象”一词是Wayne Hodgins在1994 年首次提出的(Polsani,2011), Gibbons、Nelson和Richards(2000)把这种教学内容比喻为乐高(Lego)积木,Gerard(1969)则用曼卡诺玩具组件(Meccano)来做比喻,因为“可以将课程单元制作得更小,以便可以重新组合,为学习者定制各种各样的学习内容。”
人们对可重用学习对象运动的热情似乎已经消退,这主要是由于其乐高式的“通用型”工业化做法不能满足教师和学习者的需要。可重用学习对象没有进行需求分析,事实上,由于可重用学习对象不针对具体环境,而且可以反复使用,根本无法知道其终端用户是谁,因此,很难开展有意义的需求分析。即使一开始进行调查,也只有在终端用户的具体环境下(而且必须是自始至终)开展(因为教育的目的是改变他们的思想),才能保证需求分析的效度和信度。可重用学习对象的市场(包括制作、发行和使用)从一开始就面临内容本土化的挑战,涉及对内容的检索、改编和改变用途。对于开放教育资源而言,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诸如知识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这样的开放许可协议得以解决。
可重用学习对象(以及开放课件[Open Courseware]和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最初的挑战是设置资源数量的门槛,这样才能使分享资源有吸引力。分享者的收益必须足够大,才能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开放课件运动要求参与者必须至少拿出多少门课程与人分享,然后才可以得到获取其他成员所贡献的数以百计课程的权限。如果教师觉得从中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内容,而仅仅是出于行善的目的,这就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在1990年前后就已经资金短缺了,因为在当时显而易见只有来自精英统治阶层家庭的学生使用或被允许获取国际资助的教育资源。随后,有关机构把资助的重点放在普及小学教育上。目前开放教育资源和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均是精英大学提供资金的,使用这些资源的学生基础相对较好。如果开放教育资源要实现全民教育和为穷人及弱势群体提供教育的目标,就必须有更多的开放教育资源是专门为中小学教育开发的。
在讨论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和重新利用之前,我们必须先对相关术语进行界定,包括本土化(localisation)、整体更新(globalis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和全球通用性(world-readiness)。这些术语有助于我们对开放教育资源用户进行分层分类以及说明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
·本土化: 对来自其他地方的开放教育资源进行改编以适应新的特定局部环境的文化、语言和其他方面的要求,改编后的开放教育资源仿佛是在终端用户当地文化环境下开发的。
·国际化:开发适于传播和本土化改编但又不是针对具体环境的新开放教育资源,这种资源便于改编但自身不含本土化内容。
·整体更新:对旧的开放教育资源进行更新以适应其他特定环境,比如对在某一种环境中使用的开放教育资源进行国际化,然后又重新本土化,使之适合在新的环境下使用。
·全球通用性:开发国际化的新开放教育资源,这种资源适合各式各样、甚至是所有情况下的本土化或包含本土化内容,中间层用户可以选取合适的简化版本,添加本地文化,即用户自行本土化(self-localisation)。
为了讨论本土化过程,我们可以设想把各种类型的开放教育资源使用者或重新使用者分成三个不同层次,这取决于他们是否为目标终端用户(主要是学生)、中间层用户(资源提供者、教师或翻译)或储存用户(资源库、 门户网站和机构)。
图1 开放教育资源本土化过程
图1所示的三个层次包括:最顶层是国际化、不针对具体环境的基于网页或因特网的资源库,完全适合跨文化传播;中间层是指整体更新但尚未国际化的情况,以资源提供者、教师或翻译为对象;最底层则是指学生终端用户特定的局部环境。不难看出,不同层次的用户对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适合某一层次的标准可能不适合其他两个层次。因此,给开放教育资源添加元数据标签能有助于说明该资源的目标用户层次和环境。
构建开放教育资源质量标准框架需要区分什么类型的潜在用户呢?我们的文献回顾显示,对于什么是优质教育,学生与教师,甚至是与为他们支付学费的父母,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很不一致,互不相容。我们目前的试点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专家都要求开放教育资源使用一种标准的国际语言(如英文、中文或法文),学生则要求开放教育资源使用他们当地的语言,而有些人则需要翻译(比如中间层的教师)的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生自己不能充当翻译,然后与其他用户共享翻译资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此外,虽然有些学生希望开放教育资源使用本地语言,但其中有一些学生还希望这些资源同时使用英语或其他标准的国际语言,以更好地了解其他文化或有利于今后考取证书。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层次用户对于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要求是不同的,比如在可获取性、多媒体的使用、考核评估等方面。
从满足环境要求的角度,我们至少要考虑三个层次的用户。在最顶层,我们希望开放教育资源可在世界各地被重用,因此,它们不能是为特定环境开发的;在中间层,教师的教学方式各不相同,也即教学法和教学路径可能因文化而异,因此,负责翻译的人可以改编资源库的开放教育资源,使之适合当地的文化、语言和环境;在终端用户层,我们必须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同时考虑学生所处的环境,才能吸引他们使用这些资源,建构自己个人的意义。
2. 开放教育资源质量保证准则的理论基础
本报告的目的是激发开放教育资源潜在作者——教师——的想象力,促使他们反思提高开放教育资源质量的方法。我们还收集分析有关质量问题的观点,以支持围绕开放教育资源的设计、试用和共享等方面的质量文化建设。我们鼓励教师和学生这些潜在作者反思这些准则并根据各自需要对照相关标准创建便于存储、可重新利用和共享的资源。制订这些准则的目的不是为了规定要怎么做。学习的情景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作者(学生和教师)的文化和环境,因此,他们对于采用哪些标准最有发言权。
我们多次指出这些准则并非专用于开放教育资源,它们也适用于任何学习资源。我们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作为学习资源,开放教育资源的确与非开放教育资源有很多共性。但是,开放教育资源又与其他学习资源不同,因为开放教育资源是数字化的,并且附加有开放许可协议,允许重新利用、改编和共享。此外,它们还具备开放获取、便于查找和可改编等技术性方面的特点。但是,本文提出的有关质量维度的许多准则也自然可用于其他学习资源。
“开放教育运动把与教育同行分享好的想法这种业已存在的传统和因特网的协作和互动文化融合起来。这场运动的理念是每个人都享有不受限制使用、定制、改进、重新分配教育资源的自由……首先,我们鼓励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积极参加正在蓬勃发展的开放教育运动,参加的方式包括:创建、使用、改编和改进开放教育资源;支持协作、发现和知识创造的教育实践;邀请同伴和同行一起参与”(The Cape Town Open Education Declaration,2007, p.1)(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因为这些内容是质量保证准则的理论依据)。
本报告所建议的准则主要是为了给创建开放教育资源的教师提供思路,指导他们进行反思,最终在各自的实践社区中培养一种质量文化。那些(有可能跟自己的学生协作)创建开放教育资源、并愿意分享这些资源的教师很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教学和学习的方法。我们也期盼支持开发和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机构在内部质量保证实践中采用这些准则。
3. 开放教育资源的定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2)原来对于开放教育资源所下的功能定义仅仅是“免费”重新利用的资源。这个定义中开放教育资源的“开放”指的是“可以完整查看”,如同“开放课件”或“开放内容”的“开放”一样,但不包括其他方面的“开放”,比如“开放获取”的“开放”指的是“便于查找、改编或本土化以适应新环境和重新利用”,而“地点开放”(open to places)的“开放”则指“便于转移或在任何平台(比如移动电话)使用”。“开放”的定义需要更进一步讨论。本文赞同Ross Paul (1993,p.116)的观点,认为“开放”仅仅是指某一教育系统在各个维度都比先前任何一种教育系统更加开放。Perraton和Creed(1999,p.30)把“开放”学习称为“无论是在获取、或时间和地点、进度、学习方法,抑或是上述所有方面,对学习的限制最小化的”教育。本文对于开放教育资源“开放”的定义是,与其他教育实践相比较,在涉及人、语言、地点、时间、进度、学习方法、观念、物理意义(传统方式)和/或在线获取、费用或灵活性等任何一(些)方面,抑或是所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最小。早期认为“开放”指的是免费,我们应该扩大“开放”范围,使其更具包容性,比如向女性、残疾人和少数民族语言等的开放,而不能仅仅指金钱方面的免费。Ehlers(2012)在阐述评估e-learning质量的标准时认为“开放”的意思就是包容性。
上述所有方面都与正规教育有关,我们也可以明确将该定义扩大至非正规教育,因此,还应该向全社会开放或向不同年龄段开放,因为开放教育资源可以是为终身学习而设计的。
Camilleri和Tannhäuser (2012,p.7)为开放教育资源质量创新项目(Open Educational Quality Initiative)改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新的定义是“以数字化或其他格式存在于任何公共领域或者是根据开放许可协议发布,允许他人不受限制或者受到有限限制免费获取、使用、改编和再分配的教学、学习和研究资源。”所谓有限限制,Wiley(2009)归纳为一个4R框架:
·重新利用(Reuse):仅在不改变其形式的情况下重新利用资源的权利;
·修改(Revise):改编、调整、改动或改变资源的权利;
·重新组合(Remix):把原始或修改过的内容与其他内容结合在一起创建新资源的权利;
·重新分配(Redistribute):与他人分享原始资源、修改后的资源或重新组合的资源的权利。
只要授予上述四种权利中的一种就能促使开放教育资源的开放,如果四种权利一起授予,这种资源就是最开放的。根据Hodgkinson-Williams和Gray(2008)的观点,不同开放度的版权标识见下面图2(原图来自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由Lessig[2001]根据知识共享协议制作)。开放度最高的是那些出现在公共领域而且没有附加权利限制的资源,美国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所提供的资源居多属于这一类(http://www.eric.ed.gov)。Camilleri和Tannhäuser(2012,p.16)也认为“附加在资源上的许可协议,也就是说至少允许资源的重新制作和重新利用的许可协议,是一件学习资源得以‘开放’的条件。”这个定义因此更关注成本和版权。说得清楚一点,Wiley和Green(2012,p.81)一再强调,成本和版权实际上都是涉及成本:“从成本和版权的角度看,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免费(零成本)获取开放教育资源以及获得免费(零成本)使用这些资源的许可。”因此,开放教育资源的历史定义强调的是无需任何费用,纯粹是功能性的定义。
图2 知识共享协议标识与开放度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2,p.1)的定义,开放教育资源是借助技术实现的并可以在网页或因特网上获取,本文所指的开放教育资源包括广播、电视、音像材料和图片或印刷材料,因此,其定义更加开放。开放教育资源的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包括可用于教学的工件(artifact)、歌词、讲故事、演讲、戏剧及其他表演(比如原子的3D模型或蒸汽机工作模型都可以从数字化资源库下载,然后制作成实体模型,如同我们把在线文本打印下来供离线学习一样)。这里的问题是:开放教育资源是仅指数字化格式的资源还是被数字化之前的资源和根据数字化资源制作的实体资源?
根据Camilleri和Tannhäuser(2012,p.7)开放教育资源质量创新项目的定义,开放教育资源是指教学、学习和研究的资源,这个新定义认为教学资源是专门为学习而设计的,研究资源也一样。因为这些资源是为自学或教学而设计的,他们的定义还包括“可以自我测评”这一表述,所谓“可以自我测评”,也包含用户和终端用户明白自己在教什么或学什么的元认知意识。“可以自我测评”这个术语在这里还指开放教育资源要包括学习考核的问题和答案,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应该是开放式的概念理解问题,目的在于检测使用者对相关概念的理解,而不是像封闭式多项选择题一样为了检查记忆和回忆。
Weller(2009)提出开放教育资源有大资源(Big-OER)和小资源(Little-OER)之分,这一区分是Michelle Hoyle在阐述开放教育资源制作成本时最先提出的。大资源由机构在经过内部质量评估之后发布,一般制作费用高昂,而小资源是一些很容易重新改变用途的小模块,不针对具体环境,类似于可重用学习对象。以下是Weller(2009)的定义:
“大资源是机构通过诸如openlearn(开放学习)这样的项目制作而成的开放教育资源,其优点是声誉较高、教学质量好、基本上可以直接使用、容易查找,其缺点是费用昂贵、往往不是基于网页制作、重新利用受到限制。”
“小资源是个人制作、成本低廉的资源,玩弄博客的人喜欢制作这种资源,其优点是费用低、基于Web2.0制作、便于重新组合和利用,其缺点是制作质量偏低、更难以确定其声誉、难查找”(p.2)。
Plotkin(2010,p.1)认为开放教育资源是“存在于公共领域或者是根据知识产权协议可以分享、获取和改变用途(包括商业性用途)的教学、学习和研究资源。”
“开放教育资源—亚洲”(OER-Asia)论坛2012年举行的研讨会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的定义需要扩展延伸,例如开放教育资源不仅仅是可供免费重新利用的资源,而是应该“与教育——教学和学习——有关的资源。”本文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给出我们自己的开放教育资源定义:
开放教育资源指的是借助技术实现、可以自我测评的独立教学单元,具有可测量的明确学习目标,通常在某个阶段以数字电子格式呈现,一般可供免费使用。因此,它附加有开放许可协议。开放教育资源还有一些可取的但并非必不可少的特点,包括可以纵向前后链接其他开放教育资源,形成某种学习路径,本身也可以通过内嵌链接与其他开放教育资源横向连接,提供额外内容,以丰富学习体验,也可以形成其他的学习路径。从设计的角度看,开放教育资源应该便于重新利用者进行改编、便于下载离线使用、可以移动和在不同平台间传送。开放教育资源应该有元数据标签,以方便检索,并且内置有供终端用户贴上社会性标签的功能。
方 法
1. 质量的定义
不同环境中的教师对各自情景下开放教育资源质量的构成要素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另外,一些教师可能需要更多开放教育资源,哪怕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而从技术角度讲质量很高的开放教育资源有时可能不实用,因为降低了可获取性,特别是需要有高速宽带支持才能下载的复杂多媒体资源。虽然质量问题见仁见智,但是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质量。第一和第二两个方面分别把质量看做是产品和过程——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作为一个产品,开放教育资源可以贴上机构的徽标或商标发布,以保护和(或)提高机构的声誉,例如遵守政府有关开放教育资源可获取性的法规在法律上对机构是有约束力的。许多机构都有相应的质量保证体系,在对公众发布开放教育资源之前会先进行质量评估。在向公众发布之前进行[β]测试(Beta-testing)也是保证质量的一种方法。作为一个过程,开放教育资源终端用户可以完成元数据标签,向未来的用户提供反馈和意见及建议。如果这些意见及建议经过审核后才发布,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以持续进行的方式对质量进行界定,换言之,质量是一个过程。我们相信开放教育资源运动远不只是制作免费在线内容(哪怕是高质量的内容),因此我们的质量保证准则更感兴趣的是把质量作为一种文化。
培养一种质量文化,而不是提倡优质产品或优质实践和优质过程,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几年前,Andy Lane提出开放教育资源的好处可能体现在教师审视和改进自己教育实践的过程(Hodgkinson-Williams,2010,p.11),我们制订这些准则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样一种专业反思文化。
2. 质量框架文献回顾
我们在文献中发现30多个质量维度框架,其中15个具有进一步详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以归纳与学习资源相关的质量维度和子维度。这些框架包括(按字母顺序排列)Achieve(2011),Bakken和Bridges(2011),Baya’a、Shehade 和Baya’a (2009),Binns和 Otto(2006),Camilleri和Tannhäuser(2012),CEMCA(2009),Ehlers (2012),Frydenberg(2002),Merisotis 和 Phipps(2000),Khan(2001),Khanna 和 Basak(2013),Kwak(2009),Latchem(2012),McGill(2012),质量至上项目(Quality Matters Program)(2011)和美国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2001)。这些报告也包含对其他框架的有趣评论,如Frydenberg(2002)指出e-learning领域难以满足学生期望,这对于开放教育资源来说也许是如此。美国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2001)指出设计方面的质量应该超越知识内容传递层面,可能的话,也应包括抽象思维和批判性推理以培养更高层次抽象思维能力,这是针对6-12年级学生而言的。这一点对未来的开放教育资源作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美国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2001,item1.8)还呼吁e-learning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课程内容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转变成与其他学习资源有横向链接的开放教育资源。
下面简要介绍这些框架(按第一作者字母顺序):
Achieve(2011)根据美国核心课程国家标准在“Achieve—开放教育资源—评估”框架中列出评估开放教育资源质量的八个方面标准:① 与国家标准相一致的程度;② 学科内容讲解质量;③ 教学支持资源实用性;④ 考核质量;⑤ 技术交互性质量; ⑥ 教学任务和实践练习质量;⑦ 深度学习机会; ⑧ 可获取性保证。Achieve公司是由教育领域知识管理研究协会(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成立的,开放教育资源共享(OER-Commons)资源库由该协会创建。但是,这个框架所使用的语言技术性太强,因此不容易被采用。
Bakken和Bridges(2011)为在线中小学课件制订了五个方面标准:① 内容;② 教学设计;③ 学生考核;④ 技术;⑤ 课程评估和支持。这些都是国际标准,可用于为在校学生终端用户创建开放教育资源。
Baya’a、Shehade 和 Baya’a (2009)提出了评估基于网络的学习环境的四个方面标准:① 可用性(目的、主页、导航、设计、趣味性、可读性);② 内容(权威性、准确性、关联性、充分性、适当性);③ 教育价值(学习活动、活动计划、资源、沟通、反馈、规则和帮助工具);④ 生动性(链接、更新)。
Binns和Otto(2006)列举了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框架的四个方面标准:① 产品;② 过程;③ 制作和传送;④ 机构的观念。这四个方面是由Norman (1984)提出的,Robinson(1993)报告了这四个方面的标准在乌干达的使用情况(以上两项研究转引自Binns & Otto, 2006, pp.36-38)。Binns和Otto (2006)的这个框架可用于在面授课堂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中地区。
Camilleri 和Tannhäuser (2012,pp.17-19) 指出以下技术性标准的八个维度和教学标准的两个维度:① 与标准的兼容性;②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③ 定制和包容性;④ 与多媒体资源互动中用户的自主性;⑤ 图形界面的可理解性;⑥ 学习内容的可理解性;⑦ 动机、互动和开放教育资源模块和(或)学习资源的吸引力;⑧ 提供报告工具(e-portfolio);⑨ 认知:开放教育资源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⑩ 教学:开放教育资源的教学设计。Camilleri和Tannhäuser (2012)的观点并不全面,如在已知文献中教育互动有12种之多,而Camilleri和 Tannhäuse只指出师生交互和生生交互。学习涉及五个方面,Camilleri 和Tannhäuser仅指出认知和元认知。认知过程有六种,Camilleri 和Tannhäuser 只列出复制性(回忆)和建设性(合成)。但他们的模型的确提供了一个构建质量标准完整模型的框架。
CEMCA(2009)在根据ADDIE教学设计模型制订的多媒体学习资源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 of Multimedia Learning Materials)框架中提出五个方面的标准。ADDIE模型是一个包括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开发(Development)、实施(Implementation)和评估(Evaluation)五个阶段的过程。它可迭代使用,与开放教育资源创建有一些相关的共同之处。
Ehlers(2012)为e-learning课程的质量保证给出以下七个方面的标准:① 专业信息和专业结构;② 目标受众定位;③ 内容质量;④ 专业/课程设计;⑤ 媒体设计;⑥ 技术;⑦ 评估和审查。目标受众定位涉及需求分析,这对于开放教育资源而言可能比较麻烦,而学生以社会性标签形式给出匿名反馈,最后一条的评估也会很难做到的。
Frydenberg (2002)突出e-learning质量的九个方面标准:① 机构的承诺;② 技术;③ 学生服务;④ 教学设计和课程开发;⑤ 教学与教师;⑥ 课程传送;⑦ 财政问题;⑧ 监管和法律规定;⑨ 评估,这些方面被称为“领域”(Domains),Frydenberg (2002)除了指出这九个领域的标准来自于文献以外,并没有进行讨论。
Khanna和Basak(2013)给出以下六个方面标准:① 教学法;② 技术;③ 管理;④ 学术;⑤ 财政;⑥ 道德。有趣的是,他们同时还给出这些标准五个层次的深度:①(最高级)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服务和网络;② 管理支持系统;③ 开放内容的开发和维护;④ 开放(在线/面向公众)教学和学习;⑤ 学习者考核和评价。Khanna 和Basak(2013) 的六个方面标准来自Khan(2001,p.77),后者提出以下八个方面标准:① 机构;② 教学法;③ 技术;④ 界面设计;⑤ 评估;⑥ 管理;⑦ 资源支持;⑧ 道德。
Kwak(2009)在一个经过ISO- 9001认证的框架中给出十二个方面的标准:① 需求分析;② 教学设计;③ 学习内容;④ 教学——学习策略;⑤ 交互性;⑥ 支持系统;⑦ 评估;⑧ 反馈;⑨ 可重用性;⑩ 元数据;11 道德;12 版权。
Latchem(2012,pp.81-86)给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保证质量标准:① 直接输出(Immediate Outputs);② 短期或中期的结果(Short-or-medium-term Outcomes);③ 长期影响(Long-term Impacts);④ 输入(Inputs)(关于这四个方面具体涵盖内容,可登录http://www.open-ed.net/oer-quality/others/appendix2.pdf 查阅——译注)。
McGill(2012)给出了以下确定开放教育资源质量的五个方面标准:① 准确性;② 作者/机构的声誉;③ 技术性制作的标准;④ 可获取性;⑤ 适用性。高等教育学会(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和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支持使用这个框架。这两家组织终于开始关注学生并认为开放教育资源适合使用。
Merisotis和Phipps(2000)给出七个方面的标准:① 机构的支持;② 课程开发;③ 教学/学习;④ 课程结构;⑤ 学生支持;⑥ 教师支持;⑦ 评估和考核。
质量至上项目(Quality Matters Program,2011)的在线和混合课程质量认证清单包括八个方面的标准:① 课程概述和介绍;② 学习目标(能力);③ 考核和测量;④ 教学材料;⑤ 学习者互动和参与;⑥ 课程技术;⑦ 学习者支持;⑧ 可获取性。该项目完整的文件不能公开获取。
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2001)针对6-12年级基于网络的课程提出三个方面的标准:① 课程、教学和学生考核;② 管理;③ 对已经上线课程的评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认为e-learning课程应该向学生传授更高层次的批判性思维技能。
上述框架的顶层标准分类和各类标准所涵盖的内容不一致。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框架不能结合在一起,只能在需要的时候逐项查询。因此,我们需要探索一个全面的、有文献支持的框架,这个框架涵盖其他框架各方面的内容。
我们以包括五个维度的教育目标框架为基础,收集其他框架的各种观点、文献的观点和来自世界各地开放教育资源专家在线讨论的观点。这个教育目标框架包括五个一级维度:认知领域(Cognitive Domain)、情感领域(Affective Domain)、元认知领域(Metacognitive Domain)、环境领域(Environment Domain)和管理领域(Management Domain)。
3. 网络空间的讨论
我们向大约60位专家发出咨询邮件,收集开放教育资源质量保证准则。一些专家提出了可持续性问题和创建优质开放教育资源的成本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涉及的是把质量作为产品,而我们这份准则的目的是在作为开放教育资源创建者的教师当中传授和培养一种文化质量,使他们在各地开发实践社区能采用最适合本地情况的质量标准。因此成本不是首先考虑的问题,甚至是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教师是在自己人中间讨论如何最有效地创建并与同事分享开放教育资源的。对于教师而言,涉及的成本将是机会成本(他们放弃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金钱收入的其他活动)、时间和精力。考虑到教师创建开放教育资源之后在可预见的未来便能够省时省力,可持续性和成本应该是最不成问题的。至于在出现成本问题时如何收回成本以及机构重新设计和发布开放教育资源的可持续商业模式等的讨论已经超出本报告的范围。关于这方面可进一步参阅英联邦学习共同体出版的一本书——Butcher和Hoosen(2012)。
4. 初步的框架
我们首先搭一个框架,把来自文献、交流、研讨会和其他框架的不同观点分门别类放到这个框架里。
我们把适用性作为开放教育资源质量最重要的原则,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关注开放教育资源使用者(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有五个学习领域(Domains of Learning)聚焦学生的学习效果并涵盖了所有已知的教育目标。因此,这五个学习领域可以作为质量框架的合适基础,对应开放教育资源质量的各个要素。
有些研究认为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应该取决于学科内容材料(属于学习的认知领域),而有的则认为开放教育资源应该让学生感到有趣(属于感情领域)。包含自我测评内容也是开放教育资源所提倡的(属于元认知领域),可获取性和本土化(属于环境领域)以及方便检索(属于管理领域)也被作为开放教育资源质量标准而提出来。以下是五个学习领域和它们各自所涵盖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学习模型,作为本研究的项目框架:
(1)认知领域:必须掌握的学科知识、内容技能(content skills)和反思批判性思维技能;
(2)情感领域:影响表现、学习者独立和自主的动机、态度和决定;
(3)元认知领域:知道如何完成任务以及自我监控、评估和制订学习计划的能力;
(4)环境领域:本土化、美术装潢、语言、多媒体、交互性和嵌入式链接;
(5)管理领域:方便检索、标签,包括时间管理、可转移性、商业模式。
大多数人关注的是与认知领域有关的准确性和学术可信度,也有人意识到要激发各种各样的学习动机(情感领域)和帮助因内容太难而情绪低落的学生。管理领域的几个方面(比如搜索技能、方便检索和处理网络上海量的信息)现在也被经常提到。相比之下,管理领域的其他方面、元认知领域和环境领域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
我们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方法,确定每一个领域的子维度(见表1)。目前本框架的完整版共收录200多条准则供反思(可登录www.open-ed.net/oer-quality/criteria.pdf下载)。
表1 五个学习领域框架的子维度
[1.内容——认知领域\&1.1 知识和技能内容\&1.2 教学法\&2.学生动机——情感领域\&2.1 外在动机\&2.2 内在动机\&3.学生自主——元认知领域\&3.1学习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3.2外部证据(external evidence)\&4.获取——环境领域\&4.1财务成本\&4.2无技术障碍\&4.3文化和环境的本土化\&4.4呈现和多媒体\&4.5社区\&5.包装——管理领域\&5.1方便检索标签\&5.2用途\&5.3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5. 海德拉巴区域咨询研讨会
2013年3 月13日至15日我们在海德拉巴(Hyderabad)的毛拉·阿扎德国立乌尔都大学(Maulana Azad National Urdu University)举行开放教育资源质量准则区域咨询研讨会,把在线咨询和文献回顾所收集到的标准提交给与会专家讨论,专家们也提出了自己关于质量问题的观点。本次研讨会有三个方面值得一提:第一,制订适合作为开放教育资源开发者或改编者的教师和(或)学生使用的质量准则;第二,建议开发一个培训模块(类似在线辅导教师培训模块),培训资源作者和改编者,培训模块应该配有例子、模型、模板等;第三,增加.oer这一新域名后缀,专供开放教育资源使用,如同.com用于商业网站、.edu用于教育机构一样。虽然第三点建议原是为了便于开放教育资源检索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现有数以百万计的开放教育资源鱼目混珠,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给优质资源加上.oer域名,也就是说,这一域名后缀是优质开放教育资源的标志,促使人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建设开放教育资源。这样一来,作者会认真准备优质资源,而不是抛出过时的讲义。
在研讨会期间,专家们分组讨论了我们所提出的五个领域的质量框架,最终形成一个更加简短的框架——TIPS,T代表教学和学习(Teaching and learning)过程、I代表信息和材料内容(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content)、P代表呈现、产品和格式(Presentation, product and format),而S代表系统、技术性的和技术(System, technical and technology)。
要制订一套适合所有用户的水平和需求的准则也许是不可能的。TIPS框架的目的是提供一套简单易懂的准则,激发首次开发开放教育资源的作者的兴趣,因此,这些准则不但必须通俗易懂,而且简明扼要涵盖全部关键因素。TIPS框架中只有1.16-1.19这四条准则涉及创建激励性开放教育资源,而完整的框架中有30多条准则从各个方面详细阐述如何调动和激发学习动力。完整框架有200多条准则,可登录http : //www . open-ed . net / oer-quality / criteria.pdf下载。 如上所述,所有现有的其他框架均不全面、系统,而且互不兼容。有志于更进一步了解开放教育资源(比如如何创建有激励作用的资源)的高级读者和教师可以免费获取包含整套准则的框架。这个框架以学习的五个领域为基础,完全覆盖所有已知的教育目标。学习的五个领域是所有准则的数据库,一开始必须有这样一个数据库,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库设计简单易用的TIPS准则。因此,五个领域框架和TIPS准则彼此相关,前者是一个全面框架,供需要时查询,后者是方便使用的子版本,专门为(尤其是发展中地区)非高等教育教师而设计的。
结 论
1. TIPS框架
最后的框架由四个维度组成,包括19个作为子维度的类别,共65条准则(见表2a-d)。应该强调的是,这个框架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开放教育资源作者针对其有效性提出反馈意见,我们将根据作者、今后举行的研讨会和世界各地专家的反馈意见修订该框架。
表2a TIPS框架:教学和学习过程
[1. 教学和学习过程\&教学法\&1.1\&考虑编写如何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学习指南,包括先行组织者(advance organiser)和导航。\&1.2\&使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法。\&1.3\&使用最新、恰当和真实的教学法(authentic pedagogy)。\&1.4\&转移到外部环境、向学生展示今后如何应用和鼓励进一步创新。\&1.5\&可能的话要包括图式激活提示(schema activation cues),引入学生的文化。\&理据\&1.6\&清楚说明使用开放教育资源的原因和目的、相关性和重要性。\&1.7\&与当地的需求保持一致,并预测学生当前和未来的需要。\&1.8\&向学生说明预期的好处,在可能的情况下与就业技能联系起来,可以添加潜在雇主的评论。\&学生\&1.9\&清楚说明目标学生的年龄和(或)水平。\&1.10\&支持学习者自主、独立、心理弹性(resilience)和依靠自我。\&1.11\&培养学生的自我价值感。\&语言\&1.12\&采用无性别歧视、用户友好的会话风格(用主动语态)。\&1.13\&不使用难懂或复杂的语言,一定要检查可读性,确保适合预期年龄和水平的学生使用。\&交互性\&1.14\&包含重复使用新信息和培养学习技能的学习活动。\&1.15\&说明为什么要布置某项任务以及这项任务在现实世界的意义,记住取得预期效果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激励\&1.16\&准确说明学习负担。\&1.17\&考虑在开始学习、学习过程和(或)结束学习的时候奖励一枚徽章。\&1.18\&激发内在学习动机,比如通过意想不到的轶事激发好奇心。\&1.19\&讲解自己对这个学科的见解,用你的热情感染学生。\&评估\&1.20\&学完之后给学生提供学分和(或)建议参加考试以获得学分。\&1.21\&监控完成率、学生满意度以及学生是否把资源推荐给他人。\&1.22\&努力积极影响学生的个性。\&1.23\&包含各种各样的自测活动,比如多项选择题、概念问题和阅读理解测试。\&1.24\&教师和学生能给你提供反馈和改进建议。\&支持\&1.25\&把形成性自测与帮助机制链接起来:为学生提供补习材料或其他学习路径,帮助他们继续学习。\&1.26\&尽量提供学习支持。\&1.27\&介绍与用户相关的社区群。\&]
表2b TIPS框架:信息和材料内容
[2. 信息和材料内容\&准确性\&2.1\&确保学生学习的知识和技能是最新的、准确的和可靠的;考虑征求学科专家的意见。\&2.2\&支持平等与公正,能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社会包容性、守法、无歧视性。\&相关性\&2.3\&所有内容应该是相关和恰当的,避免华丽花哨和分散注意力。\&2.4\&考虑与校外考试和(或)国家课程标准挂钩。\&2.5\&内容应该是真实的,具有内部一致性,恰当本土化。\&2.6\&诱导学习,包括通过相关事例说明为什么会出现理解错误以及所造成的后果。\&2.7\&鼓励学生参与创建适合情境化学习的本土化内容:充分利用学生先前的学习和经验以及他们的经验性和本土知识(empirical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资源
内容量\&2.8\&尽量使开放教育资源体积小,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学习单元;考虑它是否足够小,可以在其他的学科中重新利用。\&2.9\&添加其他材料链接,充实内容。\&]
表2c TIPS框架:呈现、产品和格式
[3. 呈现、产品和格式\&开放性\&3.1\&确保开放许可协议清晰可见。\&3.2\&尽量把其他开放教育资源作为组件重新利用。\&3.3\&尽量说明开放教育资源是否有某种封闭性,例如是否根据某种特定文化进行本土化,或者其内容是否可能不适合一些非目标用户。\&3.4\&确保容易获取和使用。\&3.5\&清楚提供原作者联系信息。\&多媒体\&3.6\&多媒体类型应限于两种或三种。\&3.7\&尽量适合多种学习方式——记住学生可能有视力或听力障碍。\&3.8\&以清晰、简洁、连贯的方式呈现你的材料,注意音质。\&3.9\&避免使用教师授课这种“会说话的人头”(talking head)视频。\&3.10\&如果你使用主题音乐,尽量使用适合当地文化和环境的音乐。\&设计\&3.11\&设身处地为学生设计一个令人愉快、有吸引力的环境,有效使用空白处(比如较宽的页边)和各种颜色,激发学习兴趣。\&3.12\&预留一些空间可以稍后添加经审核的学生反馈。\&格式\&3.13\& 考虑是否将开放教育资源打印出来、可脱机或移动使用。\&3.14\&考虑根据学生(包含老龄学生)需要使用不同字体和字号。\&3.15\&使用开放格式发布开放教育资源,以方便最大限度重新利用和重组。\&路径\&3.16\&考虑资源学习顺序建议——某条学习路径中哪个开放教育资源应该先于你的资源学习、哪个在其后才学习?\&3.17\&考虑提供可以代替你的资源的其他开放教育资源,使学习路径有更多选择。\&]
表2d TIPS框架:系统、技术性的和技术
[4. 系统、技术性的和技术\&方便检索\&4.1\&考虑给开放教育资源添加内容的元数据标签,以便于今后查找。\&4.2\&添加预计学习时间、预计难度水平、格式和大小的元数据标签。\&技术\&4.3\&尽量使用免费源代码/软件,便于跨平台传播。\&4.4\&确保你的开放教育资源便于改编,比如不要使用你自己的计算机编码编写资源。\&4.5\&如果使用声音或音乐,尽量不要使用你自己的计算机编码,使其便于翻译或重新本土化。\&4.6\&便于移动和传播,能够保存一个脱机副本。\&4.7\&开放教育资源和学生的作业应该可以方便地转移到学生个人的e-learning档案里。\&4.8\&给每幅图像配置备用(ALT)文本。\&技术性的\&4.9\&包含创建日期和下一次修改日期。\&4.10\&指引用户寻求适当的技术支持。\&4.11\&考虑设置社会性标签功能,允许任何学生或教师添加评论。\&4.12\&考虑添加元数据标签,允许学生提供直接输出、短期结果和长期影响等方面的反馈。\&]
2. 咨询和验证
这些准则是根据开放教育资源社区的在线讨论整理出来的,并在征求世界各地约60名专家的反馈、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们还在印度和英国举行研讨会,认真考虑与会者的意见并采纳了符合实际的建议。我们目前还在开展进一步验证,未来几年还会继续这项工作。我们鼓励开放教育资源读者和实践者尝试运用这些准则并把自己的经验反馈给我们。
准则的使用
TIPS框架为可能成为开放教育资源作者的教师或学生提供保证质量的准则。我们希望他们或是单独,或是与学科专家合作,或是与志同道合的作者组成团队,研读这些准则,以提高所创建的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有几个原因说明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第一,发展行动中的专业反思,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第二,通过记录和存储今后可重新利用的内容提高自己的教学效率,今后可以节省时间、精力和成本;第三,与本地或世界各地的人分享自己的工作,以促进全民教育。
我们鼓励潜在作者首先认真审核自己的教学材料,如教学大纲、课程计划、详细笔记和课程内容材料。然后他们可以认真学习这些准则,看看可以选择什么方式改编或重写这些材料,使它们更便于存储和检索。重写之后,他们可以与同事分享,在试验使用之后,或许他们还可以谈论如何进一步提高资源的质量,这时,这些准则可能会派上用场。
此外,教师或学生在学习这些准则之后可能会觉得能更好地判断从网上检索的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不管是创建还是重新利用开放教育资源,这些准则旨在逐步培养围绕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重新利用和共享的质量文化,以提高教和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Achieve (2011). Achieve-OER-Evaluation. Washington, DC : Achieve Inc. Retrieved January 5, 2013, from http://www.achieve.org/oer-rubrics.
[2] Bakken, B., & Bridges, B. (Eds.) (2011). National standards for quality online courses (version 2). Vienna, V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K-12 Online Learning iNACOL. Retrieved January 5, 2013, from http://www.inacol.org/research/nationalstandards/iNACOL_CourseStandards_2011.pdf.
[3] Baya’a, N., Shehade, H.M., & Baya’a, A.R. (2009). A rubric for evaluating web-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0 (4), 761-763.
[4] Binns, F., & Otto, A. (2006). Quality assurance in open distance education - Towards a culture of quality : A case study from the Kyambogo University, Uganda. In B.N. Koul, & A.S. Kanwar (Eds.), Perspectives on distance education: Towards a culture of quality, (pp.31-44). Vancouver, BC :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12, from http://www.col.org/SiteCollectionDocuments/PS-QA_web.pdf .
[5] Butcher, N., & Hoosen, S. (2012). Exploring the business case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Vancouver, BC: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Retrieved May 2, 2013, from http://www.col.org/PublicationDocuments/pub_OER_BusinessCase.pdf .
[6] Camilleri, A.F., & Tannhäuser, A-C. (Eds.) (2012). Open learning recognition: Taking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 step further. Brussels, Belgium: EFQUEL -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Quality in e-Learning.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12, from http://cdn.efquel.org/wp-content/uploads/2012/12/Open-Learning-Recognition.pdf?a6409c.
[7] Cape Town Open Education Declaration (2007).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from http://www.capetowndeclaration.org.
[8] CEMCA (Ed.) (2009). Quality assurance of multimedia learning materials. New Delhi: Commonwealth Educational Media Centre for Asia. Retrieved March 3, 2013, from http://cemca.org.in/ckfinder/userfiles/files/QAMLM%201_0.pdf.
[9] Ehlers, U-D. (2012). Partnerships for better e-learning in capacity building. Presentation for a wiki-based course on e-learning design. Retrieved February 8, 2013, from http://efquel.org/wp-content/uploads/2012/03/ECBCheck_Presentation_EN.pdf?a6409c.
[10] Frydenberg, J. (2002). Quality standards in e-learning: A matrix of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3 (2), Retrieved November 2, 2012, from http://www.irrodl.org/index.php/irrodl/article/viewArticle/109/189.
[11] Gerard, R.W. (1969). Shaping the mind: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n R.C. Atkinson & H.A. Wilson (Eds.),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A book of readings, (pp.573-579).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2] Gibbons, A.S., Nelson, J., & Richards, R. (2000).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instructional objects. http://www.reusability.org/read/chapters/gibbons.doc.
[13] Hodgkinson-Williams, C. (2010).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OER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Vancouver, BC: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Retrieved December 5, 2012, from http://www.col.org/SiteCollectionDocuments/OER_BenefitsChallenges_presentation.pdf.
[14] Hodgkinson-Williams, C., & Gray, E. (2008). Degrees of openness: The emergence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5 (5), 75-88.
[15] Khan, B.H. (2001). A framework for e-learning. In B.H. Khan (Ed.) Web-based training, (pp.75-98). Englewood Cliffs, N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16] Khanna, P., & Basak, P.C. (2013). An OER architecture framework: Need and desig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14 (1), 65-83. Retrieved March 8, 2013, from http://www.irrodl.org/index.php/irrodl/article/view/1355/2445.
[17] Kwak, D.H. (2009). e-Learning QA strategy in Korea. Presentation to Conference in Thailand. 1 May. Retrieved April 20, 2013, from (search on the following) 202.29.13.241/stream/lifelong/Kwak%20/eLearningQA_Korea.ppt.
[18] Latchem, C. (2012). Quality assurance toolkit for open and distance non-formal education. Vancouver, BC: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2, from http://www.col.org/PublicationDocuments/QA%20NFE_150.pdf.
[19] Lessig, L. (2001). The future of ideas: The fate of the commons in a connected world. New York : Random House. Retrieved January 19, 2013, from http://www.the-future-of-ideas.com/download/lessig_FOI.pdf.
[20] McGill, L. (Ed.) (2012).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kit.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 JISC.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2, from https://openeducationalresources.pbworks.com/w/page/24838164/Quality%20considerations.
[21] Merisotis, J.P., & Phipps, R.A. (2000). Quality on the line: Benchmarks for success in Internet-based distance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trieved November 20, 2012, from http://www.ihep.org/assets/files/publications/m-r/QualityOnTheLine.pdf.
[22] OPAL Project (2011). OEP guide: Guidelines for open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organizations. Brussels, EU: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Quality in e-Learning : OPAL - Open educational quality initiative. Retrieved July 10, 2012, from http://www.oer-quality.org/wp-content/uploads/2011/03/OPAL-OEP-guidelines.pdf.
[23] Paul, R.H. (1993). Open universities: The test of all models. In K. Harry, M. John,& M. Keegan (Eds.), Distance education : New perspectives, (pp. 114-125). London: Routledge.
[24] Perraton, H., & Creed, C. (1999). Apply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cost-effective delivery systems in basic education. UNESCO PIPS Infoshare Sources and Resources Bulletin, 2 (1), 30-33. Bangkok: PROAP Information Programmes and Services. Retrieved January 13, 2013, from http://www2.unescobkk.org/elib/publications/infoshare/infoshare0201.pdf.
[25] Plotkin, H. (2010). Free to learn: An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policy development guidebook for community college governance officials. Retrieved January 28, 2013, from http://wiki.creativecommons.org/images/6/67/FreetoLearnGuide.pdf.
[26] Polsani, P.R. (2011) Use and abuse of reusable learning objects. Retrieved November 4, 2011, from http://jodi.ecs.soton.ac.uk/Articles/v03/i04/Polsani/.
[27] Quality Matters Program (2011). Quality matters QM standards 2011-2013.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from http://www.qmprogram.org/files/QM_Standards_2011-2013.pdf.
[28] SREB - 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 (2001).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quality: Guidelines for web-based courses for middle grades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Atlanta, GA: SREB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operative. Retrieved December 9, 2012, from http://info.sreb.org/programs/EdTech/pubs/EssentialPrincipals/EssentialPrinciples.pdf.
[29] UNESCO (2002). UNESCO promotes new initiative for free educational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Retrieved December 15, 2011, from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news_en/080702_free_edu_ress.shtml.
[30] Weller, M. (2009). The politics of OER. Blog posting to The Ed Techie, 9 December. Retrieved March 7, 2013, from http://nogoodreason.typepad.co.uk/no_good_reason/2009/12/the-politics-of-oer.html.
[31] Wiley, D. (2009). Defining ‘open’. Blog Iterating towards openness. 16th November. Retrieved January 4, 2011, from http://opencontent.org/blog/archives/1123.
[32] Wiley, D., & Green, C. (2012). Why openness in education? In D.G. Oblinger (Ed.), Game changers: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pp. 81-90). EduCause Books.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2, from http://net.educause.edu/ir/library/pdf/pub7203.pdf.
收稿日期:2013-07-25
作者简介:保罗·川内(Paul Kawachi)博士是教育设计教授,《亚洲远程教育杂志》主编,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亚洲远程开放教育学会理事,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理事会成员和国际远程开放教育理事会成员。
译者简介:肖俊洪,教授,广东省汕头广播电视大学(515041)。
杨伟燕,副教授,汕头广播电视大学(515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