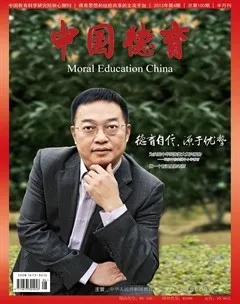内容优势:中国特色“大德育”格局*
中国特色“大德育”格局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智慧与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现代政治与革命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清晰地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的轨迹。“大德育”格局内容体系的构成,是中国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的教育表现与迫切需要。
大德育;格局;优势
王小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管理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受到极大关注。在国际教育学术界,对中国大德育进行解读的呼声与尝试,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在此项工作中,中国或西方的德育理论工作者最苦恼的,莫过于对中国“大德育”这一词汇的翻译。由于中外学者不同德育理念的客观差异或分歧,最终对此达成的初步默契是以汉语拼音的“DEYU”替而代之。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语言学问题,但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外研究者对中国特色大德育观的初步理解,更反映了对中国教育发展崛起及其价值观特色优势的部分认同。中国特色的德育内容体系是“大德育”格局的特点之一
一、“大德育”格局是中国智慧与
文化传统的教育注解
毋庸置疑,中国智慧所提供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向来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中国古代的学说之所以令西方人心驰神往,也主要是源于他们与自然、生活之间的这种亲密融通关系,儒家和较早的道家及佛家,也较好地继承和融合了这一传统,并均以此作为各自“育人”之本。虽然我们还无法就此确定这或许就是中国大德育之“大”的准确根源,但至少是酝酿中国大德育格局产生的文化影响与环境。
随着对生活的认识逐渐摆脱蒙昧,古代中国逐步从神化阶段进入羿、鲧、禹、黄帝等英雄时代。古典教化中的神灵慢慢地被英雄所替代,开始“传达当时伦理生活的基本方面”,同时也传递教育者对当时生活的价值思考,这种思考还没有界限之分或学科之分。“正如耶格尔(Jaeger)所言,在古代没有‘纯文学’、‘纯伦理哲学’等等的细密分工,一切智慧皆混沌不分”。[1]教育即大德育承载了当时的社会意识教化的基本使命,实现了全部生活、社会实践的价值传递。
中国古典德育内容传递的主要媒介是文学色彩浓厚的叙事性文本。文本记载的是时代对神或英雄的价值崇拜的历史过程,也适时总结了社会人伦关系的规则、准则,成为了当时德育的主要内容。文本在内容处理的方式或结构上,明显表现出德育的目的与方式。比如主要德育典籍“四书五经”对内容的处理路径是:先对生活或自然中存在的现象进行本真地叙述或描摹,后引申到德育的对象或目标上去。例如,《诗经》中的叙事方式“赋、比、兴”,在当代更多地是被看做文学角度的,但实际上从大德育角度看,应该是一种效果不错的教育方式:《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2]。
早期中国德育内容的处理方式虽然是诗意化、文学化的,但寓叙事于自然或生活的真实叙述或描写中,自然而真切且富有教化力,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以血亲伦理去想象和处理“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朴素的德育观,这种观念或者也是所谓“天人合一”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影响了之后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中国古典德育的内容,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其鲜明生动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德育。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多”与“广”,不可能不谓之“大”,但“大”并不意味着“杂乱无章”和“枯燥乏味”。
二、“大德育”格局的形成是中国政治与革命实践紧密关联的真实体现
“大德育”准确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政治教育与革命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学校德育,主要由以《政治》《思想政治》或《思想品德》等课程为主构成的德育体系呈现,这一传统源于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思想政治课的主要起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经验总结和筛选,这种德育在前期主要集中于政治教育,而后期则逐渐转向以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及心理教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或广义的大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相应地,从小学一直开设到大学阶段的大德育课程体系也逐步建立,只是在不同的阶段,课程开设的形式有所不同。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与实践中,根据地、解放区根据当时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战争需要,确立了以思想政治为主的德育形式,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德育内容主要由“故事、问答、对比、歌谣、韵文、顺口溜等构成,教材文字通俗易懂,有的能贴近生活,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有的还配上插图,形象生动。思想政治教育同时渗透到其他学科,尤其是实践活动中,如“生产劳动、儿童团活动(站岗放哨、小先生教成人识字、拥军优属)等”。[3]这种德育,一方面顺应了现实的需求,一方面使用了以受教育者为本的德育方法,受到当时工农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
诚然,这些内容虽然存在一定的“‘政治口号化’‘对儿童要求过高’‘反映儿童社会生活的内容太少’等弊端,且在战争环境下内容上也有对礼仪等文明行为习惯即所谓私德不够重视”[3]等缺陷,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将德育与政治教育结合的做法,反映了革命斗争的实际需求和时代特征,不仅成功地宣传了政治主张,吸引和巩固了革命所需要的统一战线,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成功。这种教育形式和内容基本奠定了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基础和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区别于旧时代的新的科学德育的诞生,以及以生产、生活实践为主要理论基础和方向的、崭新的“大德育”内容的逐步形成。
三、“大德育”格局是中国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的教育表现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和转型,这一变化也具体地表现在了教育领域,德育学科的内容演变更为剧烈和明显,但其大德育的特征却始终很明确。从所确立的教学目标来看,我国小学围绕思想品德课初步建构了大德育课程内容,而到中学阶段,以思想政治或思想品德课中心的内容开始大大超出狭义的道德教育范畴,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广义“德育课”。中国当代大德育内容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政治学科阶段。以政治思想、理论与体制教育为主的大德育准学科化阶段,表现了新中国建立时期巩固政权的现实需求,是目前大德育格局的奠基时期。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德育内容的主体。除了早期特殊阶段的需要以外,在某种程度上,无形中也受到了中国传统德育的政治观及其教化观的影响。主要内容从教材上看分为两种:一种是经过重新概括、编辑和整理的专门的、学科化的思想政治学科内容,如:《政治》《做革命接班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政治》(早期)或时事政治等;另一种是直接选取经典理论家的原著(选读)作为文本,如《毛泽东著作选读》《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共产党宣言》《共青团的任务》《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这种典籍化的政治内容,大都是在学校教育体制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比较突出的德育内容。
第二个时期:思想政治学科阶段。大德育内容的初步形成或学科化阶段,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步入正轨,并走入新的社会全面发展与改革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社会的主要任务已非政治,这种社会现实的多样化要求反映在德育领域,增加了德育的内容成分。在初中至高中阶段,这一内容增加的变化最为明显:社会教育、公民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经济教育、文化教育等逐渐融入德育;教材文本中不断出现《社会发展简史》《法律》《心理健康》《公民》《经济常识》及基本国情学习等新面目。虽然在一段时期内该学科的考试评价中仍将其统称为“政治”,但其内容已明显广于狭义的“政治学”。不过,该阶段德育学科形态仍然是相对独立设置或各自割裂的,内容之“大”仅体现在数量方面。因而我们说,这一阶段的“大德育”格局的内容体系仍处于初步形成阶段。
第三个时期:“大德育”格局的内容体系正式建立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德育要尽快适应并体现这种价值多元的现实与诉求,就必须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新的德育内容体系。实际上,专门的或狭义的道德或价值观教育内容及其教材体系,早在1960年代前后就已短暂出现或使用过,如全国范围使用的《道德品质教育》,上海市在1980年代初期的道德课(实验)等。由于我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发展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这种狭义的德育逐渐整合了上述两类内容体系中的一些构成,构建起了以思想政治和思想品德为核心,有机整合社会、经济、公民、心理、法制、国情等部分内容的新的综合的、广义的德育内容体系。这一综合的、广义的德育内容体系在当前教材中的处理方式是,在低年级阶段,以小学阶段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为主,偏重“道德的或心理健康教育”,从初中及中高年级开始,逐渐转向法律及政治、经济等国情方面的教育。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及新的《课程标准》的修订完善,无论是从外在形态上看,还是从内容实质上,德育课程及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容安排做到了有机整合,强调按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或可称为心理学或科学的逻辑)来编排,贴近学生、注重社会实践方面的内容,结构体例有了较大变化,出现栏目式、板块式、开放式设置,而非各自独立成册,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等有机统一于文本之中(综合基础之上的学生“生活逻辑”的逐渐突出)。内容之“大”部分都较好地体现在了质量方面,也标志着既是专门的或狭义的、又是综合的或广义的新的“大德育”格局内容体系的建立。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很多国家中,如果没有专门的德育设置,则必然存在大德育内容设置或其他形式的综合体系,像宗教的、公民的、社会的或文学、艺术等其他学科共同支撑着的内容构成。如果有专门的德育课程设置,则又必须面对以其他形式将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诉求整合进专门的课程内容体系中。国外的大德育内容构建以英国的PSHE(个人、社会和健康及公民教育)最为典型,另外美国的品格教育、社会教育与公民教育并行的格局、德国的以政治教育为主的多学科组合状况、法国与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由于人的异化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而提出的理想目标以及对未来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设定。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多种阐述,包含了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这种协调发展本身就强调了相互渗透、兼容并包的大德育格局的精神。■
参考文献:
[1]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0-31.
[2]吴兆基.诗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59,193.
[3]吴慧珠.新中国小学德育课程的演变[J].课程·教材·教法,2006(2):53.
责任编辑/齐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