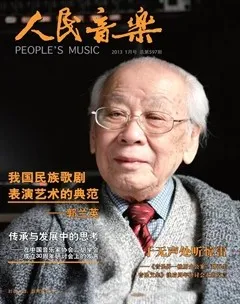蔡仲德为什么要“向西方乞灵”
仲德《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以下简称《思考》)一文的节简本发表于《人民音乐》1999年06期以来,音乐界便陆续展开了对蔡仲德《思考》一文,尤其是针对蔡仲德借鉴青主“向西方乞灵”一语的批评和讨论。纵观善意者的建议或批评者的批评,都存在对蔡仲德学术思想的误读,甚至歪曲。本文旨在通过对蔡仲德学术思想及其理论高度的考察,试图探究蔡仲德为什么要“向西方乞灵”的根本原因,并就教于方家。
一、“向西方乞灵”——接着青主说
蔡仲德对青主音乐美学思想的阐述主要集中在《为青主一辩》(下简称《一辨》,《人民音乐》1989年第4期)和《青主音乐美学思想述评》(下简称《述评》,《中国音乐学》1995年第3期)两篇文章中。前者是为青主正名,后者则是对青主音乐美学思想作进一步解读与评说,其中也都包含了学界对青主的种种责难及其辨答。两篇文章都表现了蔡仲德对于青主主张“音乐是上界的语言”、“音乐不是礼的附庸”、“夺回音乐的独立生命”、“中西乐”的关系,以及“向西方乞灵”等美学主张的高度认同。如果说,《一辩》、《述评》是蔡仲德照着青主说的话,那么,《思考》一文则是进一步基于“人本主义”立场,接着青主讲。蔡仲德得出中国音乐的“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并非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他体认青主,认同青主,着力以人本主义阐发了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因为他们都看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
在《一辩》中,蔡先生说:“青主批判了儒家的礼乐思想,继承了《庄子》‘法天贵真’、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李贽‘以自然之为美’的思想,又以西方先进思想武装自己,认为中国音乐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方法、技巧而在受礼制约,丧失独立生命,不能自由发展,因而所谓‘向西方乞灵’首要者不是利用其方法、学习其技巧,而是引进其先进思想以建立全新的音乐美学,根本改造中国音乐,把音乐由‘礼的附庸’、‘道的工具’变为独立的艺术、‘上界的语言’,使音乐获得生命,自由发展。”
在《述评》中,蔡先生研究青主关于“中国音乐出路问题”时,指出青主的三点主张,其中第二点是这样论述的:“必须研究‘西乐’,借鉴‘西乐’,‘向西方乞灵’。他反对‘关起大门,南面称朕’,认为‘这是一件最可笑,亦最可怜的事’①,认为‘西方的音乐……非输进不可。这种不可掩的事实,自然是有他的不可掩的理由’②,输进是为了研究与借鉴,而研究、借鉴应该不限于方法、技术,更注重根本精神,因为‘中国旧日那种道的世界观念,和儒冠的文人那些兼通天地人的学识是不可以帮助你认识什么是音乐。……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音乐,你还是要向西方乞灵’③。”
青主主张借鉴与研究西方音乐“应该不限于方法、技术,更注重根本精神”。
在《思考》一文中,蔡先生说:“‘乞灵’就是求道,就是寻求音乐之道,寻求音乐的根本精神。‘求道’的目的是夺回音乐的独立生命,使之由礼的附庸变为人的灵魂的语言。”
向西方学习的目的就是“寻求音乐之道”,寻求“音乐的根本精神”,回归“音乐的独立生命”,使音乐的“根本精神”由“礼的附庸变为人的灵魂的语言”。强调音乐的主体性,让音乐成为“灵魂的语言”,让音乐成为一门“由灵魂说向灵魂”的艺术。青主指出,“你们承认音乐是一种独立的艺术,那末,你们便不能够把他当作是礼的附庸。……你们要把音乐的独立生命夺回来,自然要把‘乐是礼的附庸’之说打破,……必要把这一类的学说打破,然后音乐的独立生命才有着落。”(《通论》)蔡先生之所以接着青主说,正是他也看到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弊端而有所认同,蔡先生也着重强调“音乐的独立生命”的回归,而“音乐的独立生命”是音乐艺术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反对“乐是礼的附庸”并不是要反对音乐的民族性,恰恰相反,将音乐的世界性置于民族性之上正好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蔡先生说:“他(青主)把音乐的世界性置于民族性之上,我以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一辩》)
在《评述》中,蔡先生说?押“青主围绕“向西方乞灵”命题展开的有关论述,在肯定音乐的民族性的同时,将音乐的世界性置于民族性之上,强调凡中国人作的好的音乐都是中国的光荣,反对“国乐”、“西乐”之分,这就突出了音乐的世界性;认为必须“向西方乞灵”,以便在重建中国音乐美学的基础上改造中国音乐,另辟蹊径,进行造新,这就突出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向西方乞灵”命题的意义就在于此。”
笔者曾经请教过先生,为什么在《思考》一文中要采用“向西方乞灵”的标题?先生说,用这一标题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学界关于中国音乐出路问题的“浮躁”情绪,“向西方乞灵”就是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已经实现了音乐文化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之所以坚持用“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这一标题,是为了强调向先进学习必须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并希望在这—点上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并以此展开深入的讨论④。这一标题恰似当头棒喝,《思考》一文的发表正如先生之所愿,多年来该文带来了学界持久的批评和赞誉。通观反对者的言辞,对“乞灵”一词还有不少望文生义的误解。“乞灵”一词在“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笔下,其基本涵义为“学习”、“求助”之意,傅斯年就曾主张学习白话文要“乞灵”于我们平时的说话⑤。青主在别处也使用“乞灵”一词,如:“普通一般人认为要练习音的审听,最好是乞灵于那架钢琴”。⑥通观青主的原意,怎能把“乞灵”与“跪对”、“乞讨”划上等号呢?
翻开青主的《音乐通论》、《乐话》等著作,可以发现青主对“音乐是灵魂的语言”的描述是借鉴古希腊以来西方对于音乐语言的特殊性而阐发的。而“灵魂”一词的借用也与赫尔曼·巴尔将表现派艺术称作“灵魂的呼唤”有关。“向西方乞灵”就是向西方学习,寻求“音乐的根本精神”,使之能自由、充分、深刻地表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灵魂的语言。就这一主张而言,蔡仲德无疑是接着青主说的,而其学术思想的动力源则是中国文化的转型理论。
二、中国文化的转型理论——接着冯友兰讲
冯友兰先生在《答哥伦比亚词》中说:“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个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⑦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1940年)中曾对“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批评,认为它们“俱是说不通,亦行不通底”。他从“新理学”体系“别共殊”的观点出发,认为各国文化之间既有相同的基本类型,也有各异的民族特性,前者是文化的时代性,后者是文化的民族性。冯友兰先生说:“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⑧”
蔡仲德继承了这一理论。他在《冯友兰先生评传》(载《文史哲》1996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以此观点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便应认识中国文化的任务是由前现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特型,而西方文化已经完成这一转变,故应向西方学习。”所以,在《思考》一文中,蔡先生说:“中国文化在近现代所面临的任务,是由前现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而西方在中国之前已完成这一转型,故理应向西方学习。但所学应是西方文化中对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民族特性,故其中与现代化相关的主要成分是我们需要吸取的,与现代化无关的偶然成分是我们不必吸取的;同理,中国文化中与现代化相冲突的部分是我们必须改变的,与现代化不相冲突的部分是我们不必改变的;就与现代化相冲突者均应改变而言,这种改变是全盘的,就与现代化不相冲突者均不需改变,只改变文化类型而不改变民族特性而言,这种改变又是中国本位的。”
蔡先生还认为,西方文化中对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主要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人权为核心的观念、价值系统。它们不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专有物,而是西方文化的伟大创造,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必将在全世界普遍实现。中国文化中与现代化相冲突的东西主要有以下几点:1.政治权威高于一切,文化从属于政治,不能独立发展。2.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学术无自由可言。3.以“三纲”为天经地义,等级观念牢不可破,影响深远。4.以群体为本位,强调“私”与“公”、“利”与“义”的对立,只讲个人义务,不讲个人权利,国家至上,个人无独立与自由可言。5.天人不分,轻视科学技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6.强调“夷夏之辨”,华夏中心主义根深蒂固,不利于真正吸取外来思想,除旧更新。此六点构成中国文化的基础与核心,使之成为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不批判它们,不打破中国文化的原有体系,就不可能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人权为核心的观念价值系统在中国生根。中国文化中与现代化不相冲突的东西,除优秀的文学艺术、优秀的科学技术及某些体现善良情谊的民间习俗等等以外,在思想、价值层面,还有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忠恕之道(墨家的兼爱主张与之相近),道家(主要是庄子)反异化求自由的精神,法家顺应时势进行变革的主张,以及墨家的科学、逻辑思想。但在中国文化中,仁爱思想与忠恕之道受制于等级观念,不具有独立意义,反异化求自由精神历来被视为异端,变革主张、科学与逻辑思想则长期未得到发展。不把它们从中国文化的体系中剥离开来,就不可能真正继承、发扬这些优秀思想(《思考》)。基于这样的观点,蔡仲德学术思想的逻辑势必指向西方文化中有助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以人权为核心的观念、价值系统。这同时也是《思考》一文为何“向西方乞灵”,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理论根源。就中国文化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理论而言,蔡仲德无疑是接着冯友兰讲的。
三、理论高度——人本主义
蔡仲德学术思想及其理论高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本主义”。在《思考》一文中,他说:“人本主义——据对文化的目的与特性的哲学思考,要求能动地创造文化,创造音乐,使文化日益进化、发展,有利于进一步解放人,改善人的存在,不断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使音乐日益进化、发展,有利于更自由地表现人,不断满足人的审美需求。”又说:“文化由人所创造,也为人而存在,它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不是民族性而是人性,而人性有个体性和群体性之分,群体性又有家族性、区域性、团体性、职业性、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全人类性)等等的不同。民族性仅为群体性之一,它既不是人性的根本,也不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在文化的群体性中,大的群体性应包容小的群体性,小的群体性应不与大的群体性相抵触,故不应将民族性置于文化的其他属性之上,以民族性压抑个体性,阻碍人性的发展,而应有世界的胸襟,人类的眼光,高扬人性,高扬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并不是蔡先生的独创,但蔡先生无疑是这一思想的忠实贯彻者,“人本主义”的理论及其依据来自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蔡仲德在《评述》一文中写道:“马克思曾说,‘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活动。’⑨……说要理解人的一般的世界历史活动都必须从人本主义(或曰自然主义,即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者统一起来的真理’出发,而不能只从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出发,那么,要理解人的艺术创造活动就更是如此。青主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关于艺术的主体性和音乐的特殊性的论述虽不如马克思所说科学、明晰,其根本思想却是与之相近相通,它们正是从人本主义出发,因而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是二者的统一。”
在《论“五四”价值及其恒久意义》一文中,蔡先生又写道:“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⑩就此而言,人本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它既保存了人类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种人本主义不仅是一种价值观,而且是一种世界观与历史观,它主张考察、解决一切有关人的问题都必须从人的经验出发,都必须以人为目的,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人本主义又认为自由的、能动的创造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因而自由是人所追求的最有价值的价值,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追求与实现自由的过程,社会合理的程度决定于它保障个体自由的程度,而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人本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人本主义无疑有利于解放人、改善人的存在,因而它既具有恒久的意义,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未来;又具有普遍的意义,无论是对欧洲还是亚洲,西方还是东方。”{11}
由此可见,蔡仲德将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赋予“人本主义”理想而加以发展,他的音乐美学思想既继承了青主又发展了青主,他们都强调音乐的主体性,都强调了音乐的特殊性,强调音乐是人的精神(灵魂)的表达(人的灵魂的语言),也都强调人的解放和音乐的解放的重要意义。蔡仲德美学思想着重阐发了中国音乐的未来之路必然要通过“人本主义”的洗礼,使音乐不至于沦为“礼”的附庸或政治的工具,从而使音乐能自由、充分、深刻地表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的语言。
蔡仲德美学思想所推演的逻辑,便是要通过“人本主义”改造,使音乐摆脱从属于“礼本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传统,成为“独立的艺术”。而要早日达到这个目标,完成中国音乐文化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必然要走青主指出的道路,即“向西方乞灵”。“乞灵”就是求道,就是寻求音乐之道,寻求音乐的根本精神。“求道”的目的是夺回音乐的独立生命,使之由礼的附庸变为人的灵魂的语言。他认为,中西音乐的根本差异不在民族性,而在时代性,即是前现代与现代的差异,“求道”就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音乐从前现代到现代进程中,如何赋予音乐以独立精神的本质之所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音乐技术与技巧的单纯学习与模仿,更不是守护在狭隘民族主义旗帜之下的保守主义或国粹主义。
蔡仲德的学术无疑是建立在他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文化,以及对冯学长期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他的学术具有“世界的胸襟,人类的眼光”,他极力在其学术思想中高扬人性,高扬人本主义。他对于现当代音乐及其理论的批判,及敢于和巧于论辨的精神,既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又体现了为探索真理而无所畏惧的学术勇气,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真正学者和导师。
通过对蔡仲德学术著作的解读,不难看出蔡仲德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和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强烈呼唤。他之所以要“向西方乞灵”,正是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所驱使。如果抛开蔡先生在论述“向西方乞灵”这一命题过程中存在的个别偏颇之处不论,他继承青主“乞灵”理论,并加以“人本主义”和“中国文化转型”理论的阐述与延伸,“乞灵”一词本身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向西方乞灵”——蔡先生敢言别人之所不敢言的音乐美学思想与学术勇气均值得肯定。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勇气和探索精神永远值得后学者学习和景仰!
谨以此文,纪念蔡仲德先生逝世五周年!
①原注引《介绍几个新的音乐作家》
②③原注引《音乐通论》。
④此说也可参见蔡仲德《致〈人民音乐〉编辑部的公开信》,载《中国学术论坛·学人主页·蔡仲德》,地址:http?押//www.frchina.net/person.php?芽id=141
⑤参见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⑥青主《论音的审听》,《音》1930年第十九期第1页。
⑦引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3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⑧同上,第4卷224—227页
⑨原注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0页。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
⑩同上,第50页。
{11}载加拿大《文化中国》1999年9月号。
叶明春 博士,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