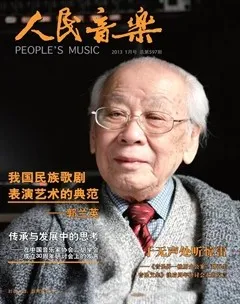大理洞经音乐的表演与记谱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
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中,关于表演与记谱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较为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并且这一问题也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一、规定性记谱与描述性记谱的阐释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提出了“规定性”(prescriptive)记谱法和“描述性”(descriptive)记谱法的定义;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在文章中对这两种记谱法进行了解释①。根据笔者的理解,西格关于规定性记谱和描述性记谱的划分具有很明确的指向。规定性记谱主要指西方专业艺术音乐,先由作曲家完成乐谱,之后交给演奏者来演奏,演奏者需要准确地表达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和理念。与之相对应的是描述性记谱法?穴descriptive?雪,是发生于音乐声响之后的一种描述声音的记谱形式②。一般认为许多东方国家或者非欧洲国家的音乐属于描述性记谱,这些音乐一般不以曲谱来规定,在表演和传承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研究者要对其进行描述性的记谱。很长时间以来,学者们认为描述性记谱几乎可用在所有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类型研究中。
但事实并非如此,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民间音乐,很大一部分音乐是有乐谱的传承,比如器乐、戏曲等音乐形式。中国传统音乐中有乐谱记载的器乐曲不胜枚举,如明代朱权编译的古琴乐谱《神奇秘谱》、清代华秋苹编的《琵琶谱》。无疑,这些乐谱对演奏者的表演起到了一定的指示作用,不再是研究民间音乐中所使用的描述性记谱了,与西方音乐作品的乐谱具有相似的作用。因此,这些乐谱是指导艺人演奏的规定性记谱文本,是一种局内人的乐谱。
二、洞经音乐中的规定性记谱
尽管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丝竹乐的研究成果非常可观,但对于丝竹乐的表演和记谱之间关系的研究,则呈现出了一定的空白。大理洞经音乐中有近百首曲目均由工尺谱记谱,并流传至今。但其在表演和记谱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大理洞经音乐的乐谱中,不难发现“规定性记谱”的存在。大理洞经音乐的来源,不仅包含有佛教、道教曲牌的经腔,还包括内地传入器乐曲。其中器乐曲是在元末明初时由中原、内地传入大理,后经过吸收大理白族民间音乐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大理洞经音乐经过历代文人士大夫的整理收集,已经有了一些严格的乐谱,因而具备了规定性乐谱的特征。例如出生于洞经音乐世家的李莼先生,其先祖就是洞经乐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家中藏有《玉振金声》这样的古谱,用工尺谱记载了大量的洞经音乐曲目③。按理说,这些乐曲的工尺谱应该是演奏的范本和蓝图,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大理洞经音乐的乐曲虽然有“规定性乐谱”作为范本,但是研究者为了较好地完成研究工作,仍需要对表演进行描述性记谱的分析。
三、不同洞经会演奏同一乐曲时存在的差异
笔者发现,大理不同的洞经乐会演奏同一首乐曲时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乐曲的旋律构成及节奏层面。但在很多资深的乐师看来,这些差异只是每个人的演奏习惯不同罢了,并没有改变乐曲的重要特征。
(一)乐曲《南清宫》的变异分析
通过对大理洞经乐曲的记谱分析发现,在洞经音乐表演中,一些承载着仪式功能的经腔曲牌与传统乐谱大同小异。比如,不同乐会弹演的《元始腔》、《咒章》、《开经偈》、《元皇赞》这类经腔时,变化较少。这是因为承载仪式功能的曲牌CzuPE0JGnOgiQrgBt92blg==经腔多与洞经会弹演的经文有着密切的关系,曲调多以弹经师吟唱的经文腔调为基础,因此所唱经腔与乐谱之间的变化较少。而一些距仪式功能较远的器乐曲如《小桃红》、《南清宫》、《浪淘沙》、《万年欢》等,因为不以经文为依托,所以体现出了较多的差异。大理洞经器乐曲《南清宫》是一首古曲,据史料记载,这是一首南宋时的宫廷音乐,主要用于祭祀上天的仪式活动中。大理喜洲镇、周城镇与南诏古乐会演奏的三种文本均是乐曲《南清宫》的变体。由此让我们想到了江南丝竹乐曲的构成方法。江南丝竹音乐结构除了一般民间音乐常见的单曲变奏与多首曲牌连缀的曲式结构以外,最大的特点是以板式变化手法构成的曲式结构特点。如乐曲《中花六板》等是在曲牌《老六板》的基础上扩充加花变化成为五首节奏、速度、风格不同乐曲——《五代同堂》④。事实上,很多大理洞经器乐曲在演奏和构成方面与江南丝竹有相似之处,这一问题已有学者给予关注,认为其曾受到江南丝竹的影响⑤。乐曲《南清宫》实际上很像对一个母曲所做的不同类型的变奏,只是它没有按照像江南丝竹以板腔体的构成方法发展成一组乐曲。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加花扩充和减缩的方法,对《南清宫》不同乐谱文本进行减缩还原,也就是找出旋律结构的骨干音。
以下是笔者对大理不同地区演奏的乐曲《南清宫》的记谱,及骨干音的简化还原分析。
谱例1:南清宫⑥,滕祯记谱
骨干音分析:
三种演奏文本均是在乐曲骨干音的基础上做上下二度、三度这样迂回的加花变奏。但其变奏并不是按照同一种音程度数或者加花规律来进行的。这是由于乐器的性能、音域不同,在演奏中会产生高、低八度的差异(但在艺人们看来,高、低八度本身没有区别)。如此一来,演奏的骨干音势必会影响它的变体,围绕骨干音扩展的旋律也因此会有不同,因此产生不同的乐谱文本。以下是此乐曲中几种骨干音高、低八度及变体的分析,其中①为骨干音,②为骨干音高八度的变奏,③为低八度变奏。
谱例2:
谱例2中“sol”具有高、低八度的形式出现,在高八度的加花变奏中旋律是向上方二度加花,而在骨干音为低八度的加花中,旋律出现了向上方四、二度的加花,这与高八度的变奏完全不同。
由此看出,洞经音乐的乐曲发展方式并非与江南丝竹相同,它们没有严格的板式变化规定。而且乐曲变奏过程中的骨干音并非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变奏不断地进行改变。
(二)乐谱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解释
乐曲《南清宫》的三个乐谱文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们又不同于原文本。这正如符号学互文性原理所陈述的一样: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⑦。互文性理论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是说文本是由它以前文本的遗迹或记忆形成的。并且每个文本的外观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但文本绝不能被理解为摘抄、粘贴或仿效的编辑过程,而是说,从文本网中抽出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此文本而指向其他先前文本,这些文本把现在的话语置入与它自身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更大的社会文本中⑧。以上这些关于互文性的理论,可用来解释《南清宫》这首乐曲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出现的多个文本。笔者对李莼所抄《玉振金声》中的《南清宫》工尺谱进行译谱,却得到了和上述三个地区完全不同的乐谱,详见下面谱例。
谱例3:南清宫⑨
从以上两行乐谱中可以看出,乐曲在开始部分基本保持着一致,从第6小节之后,两种乐谱的音乐旋律在节奏和音方面均有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是由于乐器演奏时所产生的不同高、低八度音所致,因此旋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前所述。
三个音乐会演奏的《南清宫》实际乐谱与工尺谱、传统的保存谱,出现了五种不同的版本,这些文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用互文性理论来分析洞经音乐在当下演奏活的文本,与传统保存谱(李莼译)二者之间存在着引用和间接复制的关系。而不同地区的表演文本则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都是对原有文本不同程度的复制和改写,都与原有的文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三种乐谱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衍生关系,其次是一种交汇的关系,三者之间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差异。因此,文本之间互文性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种复制、拼贴的关系,而是一种吸收转化的过程。
四、表演的即兴性因素是产生不同
文本的重要原因
乐曲《南清宫》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艺人的演奏带有某种即兴要素,尤其是一些造诣较高的资深艺人,他们本身在乐器的演奏和乐曲风格的把握方面非常娴熟,具备一定即兴发挥的能力。其次,艺人之间的合作具有习惯性的默契,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长期以来,这些演奏习惯就成为一种固定的技巧规范,而被艺人们所接受并传承下来。但仍不能排除乐曲在传承过程中可能产生新的即兴习惯,因为人们的文化语境总是在变化的。
长期以来,即兴问题在民间音乐的研究中一直被忽略,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Bruno Nettl)曾在《世界音乐在表演过程中的即兴研究》一书指出即兴的重要性。内特尔在这本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论证了“即兴”作为一种产生于外在的表演要素,对研究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甚至是艺术音乐,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即兴的概念实际上更广泛,而且比作曲本身包含着更多的创造性,可以看作是个人写作的乐谱。同时,对音乐的整体性来说即兴是中心,它是理解音乐大环链中的一个重要要素⑩。
同时即兴因素的产生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民族音乐学家布鲁姆(Stephen Blum)指出,如果即兴经常被描述为听众在熟悉环境里的期望和反应的一个方面,即兴还可以看作是使表演者去控制他们依赖于习惯的反应的艺术{11}。表演者的即兴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会依赖于自己已经形成的对乐器的表演习惯,以及他们的表演环境等。并且,这些即兴能力依赖于他们所受到音乐教育水平的高低。通常,一个有造诣的表演者的演奏风格和即兴表现会被一些新手所模仿,所以演奏者的即兴风格有相对稳定的特征。
因此,乐曲《南清宫》在不同的地方演奏会出现三种不同的乐谱文本,是由于一些资深的老艺人在演奏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即兴习惯,而洞经会的其他乐手也会模仿这种风格。久而久之,乐曲就会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演奏风格,从而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演奏。同时,现场的演奏与原有乐谱的不符,很大程度上是即兴原因造成的。因为,艺人们通过长期的表演,已经形成各自固定的即兴风格,这样势必会产生不同的文本。正如符号学互文性所谈到的观点,每个文本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但又都不同于原文本。
结 语
本论文是在笔者田野考察过程中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目前自己在洞经音乐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状况和问题进行的思考和分析。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首先,民族民间音乐处于一个活态、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即使是洞经音乐这样有着几百年历史的音乐文化,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异,虽然大部分乐曲都有原文本的乐谱。其次,变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排除一些人为的因素,如专业作曲家的改编、创作等情况。但是,民间音乐自发的种种变异也是决定音乐不断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洞经音乐在演奏和记谱中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也将为我们理解其他民族民间音乐提供一定的借鉴和视角。
①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论导读》,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240、264页。
②Charles Seeger. Prescriptive and Descriptive Music -writing?熏 Ethnomusicology edited by kay kaufman Shelemay Wesleyan University,Graland Publishing New York?熏1990?熏P184—195.
③何显耀《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揭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玉振金声》乐谱于明嘉靖九年下关三元社和大理叶榆社成立后,由杨慎、赵雪屏、李以恒等共同搜集流传于大理一带的洞经乐曲而成。
④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355页。
⑤大理下关文化馆编《大理洞经音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⑥乐谱第一行为大理南诏古乐会的演奏记谱,第二行为喜洲史城聚真经会的演奏记谱,第三行为周城周德会的演奏记谱。由于篇幅所限,乐曲均不完整,下同。
⑦⑧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1页。
⑨第一行乐谱为李莼根据下关三元会传谱整理,第二行为笔者根据工尺谱的译谱。
⑩Bruno Nettl?熏 Melinda Russell.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ance Studies in the world of Music Improvisation?熏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熏1998,P3—19.
{11}同⑩,第33页。
(基金项目:2012年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基金项目《大理白族洞经会三种仪式音乐的研究》,课题编号:12py201。)
滕祯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博士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