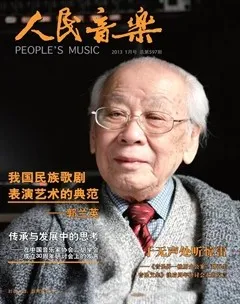想象的智慧
么是音乐作品,或音乐作品这一概念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个一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让一位哲学学者莉迪娅·戈尔(?穴Lydia Goehr)在其著作《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中进行了呕心沥血、弃而不舍的追问。莉迪娅·戈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美国美学协会理事,1960年生于英国。她不仅擅长演奏小提琴,更热衷于历史。因此她的研究虽侧重于德国美学理论,但对哲学、政治和历史与音乐的关系尤为关注。①《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一书的诞生,正是基于戈尔多年来对哲学、历史与音乐的深刻思考和浓厚兴趣。该书不拘泥于传统音乐美学和史学的思考方法,开启一个了全新的音乐思辨里程。全书分为两个部分,戈尔从其独特的哲学家视角,用“分析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分别探讨了核心问题“音乐作品”。
在戈尔看来音乐作品似乎并不是不言而喻或自明的,西方音乐历史漫漫长河的绝大多数时间中音乐作品并不存在。她的一些话猛一听起来使人诧异:“人们仍可创作或谱写音乐而不由此而产生作品”(第119页);“我根本无意将作品等同于曲调和歌曲”(第121页);存在“没有作品概念的音乐创作”;巴赫谱写了音乐,但他无意谱写音乐作品。戈尔的言论别出心裁,到底她说的音乐作品指的是什么?
《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整部书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解释这一中心话题。在全书的第二部分“历史的方法”中,她在第三章“中心论点”的开始进行了回答:对于音乐作品这一概念,我将明确主张:(1)它是一个开放性概念,有原初和衍生的用法;(2)它与实践的理想相关联;(3)它是一个规范性概念;(4)它是投射的;(5)它是一个新兴的概念。”(第88页)
对于这一“中心论点”初读起来浑然不解,即使是顺着她的解释读下去也会感到扑朔迷离,疑惑丛生,但耐心细致读下去最终还是可以大致理解作者的思路。中心论点的五个方面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什么是音乐作品,而是以哲学(美学)意味阐述了与音乐作品概念相关的若干理论性问题,这五个问题虽然分离,但彼此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五个方面,回答的都是:什么是音乐作品?
(1)开放性概念。在戈尔看来,虽然她对音乐作品有一个明确地界定,但这个概念是“开放性”的,即它不是“绝对准确”的定义,是可以修改的,具有“可质疑性”,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能怎么说都行”。戈尔的回答是很有弹性的,但也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历史性的界定——音乐作品的概念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中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有了“原初的”和“衍生的”划分,前者是规定的,后者根据历史境况进行变通。
(2)与实践的理想相关。在戈尔看来,音乐作品概念是否产生,与演奏中是否“努力趋近与充分而具体的乐谱尽可能的相符”(第88页)有关。演奏与乐谱相符对于戈尔来说,是一个音乐实践中的理想问题,也是攸关于作品是否存在的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下面还会涉及。
(3)规范性概念。这一点尤其重要。音乐作品是否成立,要看它是否具有规范性概念。所谓规范性概念固然与音乐的形式、法则、方法等实践性构成要素有关,但戈尔专门强调,“规范性概念与构成性概念不同”,更注重的是从外部指导实践的思想、观念、文化、习俗。音乐实践之所以遵循一些规则,“乃是基于我们对诸如自由、正义和责任之类的概念的把握。后者并不构成实践之结构,而是在其相互关系中确定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决定实践性规则的是背后看不见的精神性的事物。音乐作品的概念与特定时期的文化观念所形成的约束力——也即规范性概念有关。由此看,戈尔所谓的“规范性概念”指的更多是认识性因素,是“信条和价值观”。
(4)投射的概念。与上一概念密切相关。戈尔说:“作品仅以投射形式存在;真正存在的是规范性作品概念。”(第106页)投射,是把头脑中的东西外化出来,即戈尔所谓的“实存化”或“客体化”,只有作曲家依据“规范性概念”——特定的观念和意识——把头脑中的音乐想法或信念投射出来,实存化后,作品才能形成。戈尔写道,“通过投射或实存化,人们找到一种客体,这一客体叫做‘作品’”。(第186页)
(5)关于“新兴”的概念。更准确地似乎应该是“兴起”。依据以上,在戈尔看来,音乐作品的概念并不是任意的,它与历史和文化有关,它需要演奏和乐谱相符,需要投射并固化。只有具备了一系列条件之后,音乐作品的概念才得以产生。戈尔认为,1800年前后,是音乐作品兴起的一个时点。
凭什么说1800年前后才出现了音乐作品,难道此前的音乐不是作品吗?这种诘问是不可避免的。戈尔这样回答:1800年以前的音乐家并非在作品概念规范下从事创作。……他们当然是以歌剧、康塔塔、奏鸣曲和交响曲这些概念从事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当时是在创作作品。只是到后来,当人们开始以作品为原则看待音乐创作时,早期音乐、康塔塔、交响曲和奏鸣曲才获得其作为不同种类音乐作品的地位。而这就是何以我们至此可以不无意义地说,巴赫创作了音乐作品。(第116页)
什么是“以作品为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在戈尔看来,音乐之所以为“作品”的原则就在于,音乐脱离于一切外在于自己的功能,获得独立性,“音乐作为一门艺术获得了自主的、音乐本身的和‘文明’的意义,逐渐按其自身特点为世人所认识。……从外在于音乐到音乐本身的转向,其标志就是音乐作品这一概念的兴起。”(第125页)
那么巴赫创作的音乐难道不是作品吗?戈尔仍然坚持,“巴赫并未绝对明确或用意明确地从作品角度看待他的活动,规范他的活动的是别的东西。”(第115页)在她看来,巴赫时代音乐并不是自主的,巴赫的创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某一部音乐作品,而是在做“上帝让他做的事”,不是规范性概念下写作音乐,“他当时明显从不同的概念角度思考音乐。”(第114页)
戈尔认为,1800年前如下情形是普遍存在于实践中并妨碍作品概念成立的:
1.音乐无法完整重复,或者每一次的演奏都是不一样,这样音乐完全依附于演奏存在,而作品概念要求“超越于演奏而存在作为音乐活动的首要目的。”(第119页)
2.演奏和乐谱不相符。一直到巴洛克时期,即兴演奏仍然是西方音乐存在的重要方式,而即兴意味着记谱的不完整以及音乐构成的非标准化,这导致“音乐家不是把作品,而是把单独的演奏活动看成其创作活动的直接产物”。(第200页)
3.这样的音乐活动是富于表现力而非生产性的,其“表现潜力指向演出或活动本身,而不是创作有形的建构或产品。”(第127页)
4.上面情况导致音乐不是“投射”的,演奏完毕后无法形成长存的有形之物,即缺乏“实存化”的音乐。
5.缺乏“实存化”导致音乐无法重复出现,同一首音乐无法在下一次演出中重复,巴赫时代没有把演出过的音乐再在下一次演出的习惯,“巴赫的后继者不会经常演奏他的乐曲,正如他并不经常演奏其前任的乐曲”。(第201页)
6.作曲家并不详尽地谱写乐谱,并具体规定乐器。
7.随意篡改作品,或公然随意借用别人的材料。
8.作曲家的社会地位是从属仆人,不是自由作曲家。
但即使如此,戈尔也并没有把1800年前后完全分开,她的“开放性概念”理论使她的这种观点获得了某种弹性。尽管1800年前人们并未以明确的作品意识在谱写音乐,但作品的概念已经蕴含于音乐实践中,我们今天之所以把巴赫的音乐视为作品,是因为我们不自觉地把巴赫的音乐放在了如今的作品语境中,这是衍生性的。我们可以衍生性地把巴赫、帕勒斯特里那的音乐归类为“作品”。
戈尔为何要如此煞费苦心地在一个概念上大做文章?为何死死地盯住了1800年前后?这就要去了解她的总的学术倾向和立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家F.施莱格尔(1772—1829)在其早期论文《希腊文学研究》(1798)和《希腊人及罗马人的诗歌史》(1798)中认为古希腊艺术是真正的典范,又认为古希腊人所创造的在当时客观存在的艺术品,是必将消失的作品,而现代的主观精神则可以继续发展。他主张抽象的“普遍艺术”,强调艺术的主观性,反对艺术与现实发生任何联系。1808年皈依天主教后,施莱格尔开始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试图逃往理想国,避免接触鄙陋的政治现实。他认为诗人不必受法律规则等条框的约束,“天才”可以越过现实社会的限制。其观点在当时有相当的影响。②19世纪杰出的德国小说家E.T.A.霍夫曼(1776—1822)的创作受到浪漫派的影响,其文学作品具有怪诞、诡秘的色彩。但他并不颂扬黑暗或逃避现实,而是用作品中的黑暗面折射现实社会,对现实进行批判。他的深刻思想对揭露19世纪德国病态社会具有重大意义。③在历史观上,戈尔深受这两位浪漫派代表人物的影响,认为音乐——尤其是器乐——在世纪之交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音乐前所未有地独立、自主,它脱离了它过去所依附的宗教、社会、语言,成为一种最纯粹的自为的绝对艺术形式,跃居于艺术王国之巅。
因此看出,戈尔的音乐作品的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其中包含了她对历史的理解。和之前的浪漫主义者一样,戈尔在其学术论著中充满了富有诗意的想象。在她看来,作品概念的兴起与音乐作为美艺术是同步随行的,而美艺术意味着长存必灭。音乐具有的短暂的、易逝的特征使其无法长存。因此音乐也应该像其他美艺术一样建立自己的博物馆,“音乐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为自身创立一个比喻意义上的博物馆,即某种与造型艺术博物馆相当的东西——今日所谓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第186页)
作为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其基本特征有,第一,它脱离日常书面语体,思想可以直接用作纯粹表现审美的载体,不再必须以外在的实体事物作依托,不承担对外在世界的功利责任,也不对外在世界具有额外的影响力;第二,它是对于音乐作品审美本质意义的保存,不再任由他人对作品进行擅自改动。但不同在于,这一博物馆是想象的,亦即是虚拟的,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第三,它是以真实客观为标准保存的原生态的艺术思想,而不是通常指称为由某个人演唱或演奏的作品。原作者思想储存,这是对于该作品最具典型意义上的储存,任何其他人们的演唱和演奏,既可能是对该作品的再创造,也可能是对该作品内在含义的扭曲;第四,作为想象的音乐博物馆,它是属于个体思想的领域,因为想象具有极为特殊的个体性,创作个体对于其作品既具有记忆与保存的功能,同时也能够对其音乐思想进行阐释和解读,直至有时随着思想的变化及时对某些作品进行新的阐发与拓展;第五,想象的音乐博物馆的出现,是对于音乐表现和审美哲学的丰富与提升,它一方面尊重和强调了个人思想的作用,但又促进了个体差异与整体和谐的统一;第六,想象的音乐博物馆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音乐作品在想象的博物馆中的投射,需要深湛的思想和战略性的行动”(第187页),人们还要付出持续的研究和思考。同时这种博物馆又是可以交流的,即人与人之间的对于音乐的不同理解可以实现互通与相互补充,使之成为具有广泛和动态意义的博物馆。
通过想象的智慧,戈尔终于在她厚重的著作中建立起了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它基于传统的音乐本体论美学思想,但又有不同。有许多学者同样对音乐美学的本体论有着深厚研究:如卓菲娅·丽萨在音乐自身中去理解音乐;茵加尔顿认为音乐是纯意向性对象;古德曼认为哲学、科学、艺术等都是服务于不同目的的构造世界的方式;大卫·戴维斯将艺术作品定义为艺术家创作通常被称之为“作品”的那些实体的过程……戈尔则跳出了传统音乐美学思路,独辟蹊径。确立音乐想象博物馆的意义主要在于:人们应当认真研究对于音乐作品本体意义的尊重与思想介质的保护,即便它主要存在于个体的想象之中。作为这一奇想的呼唤,将引导更多人们尝试研究并进入自己思想的音乐博物馆,这就会使得音乐既可以获得心灵深处最具本体意义上的刻录,展示人生最原始和真实的思想本原,又可以生成千差万别的音乐世界,使得人们对于音乐拥有越来越多的深层理解与共识。而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将促进音乐文化得到正确的普及与提升。
参考文献
眼波卓菲娅·丽萨《论音乐理解》,于润洋译,《音乐研究》1988年第2期。
演于润洋《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述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演?眼美?演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演?眼加拿大?演戴维斯《作为施行的艺术:重构艺术本体论》,方军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①[美]莉迪娅·戈尔《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罗东晖译,杨燕迪审校,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简介。后文标注页码之引文,皆引自本书。
②Victor Lange:Friedrich Schlegel's Literary Criticism,Comparative Literature,1955,7(4).
③Georg Ellinger:E.T.A.Hoffmann:Sein Leben Und Seine Werke,Kessinger Publishing,1894.
张景晖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级2010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