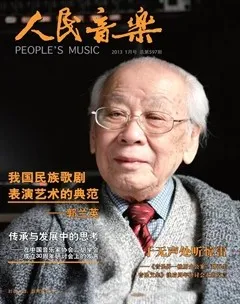曾侯乙墓中室金石乐悬性质再探
77年9月,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重大新篇章——在湖北随县城郊擂鼓墩附近,发现后来著称于世的曾侯乙墓。
该墓椁室可分为东、中、西、北四室,西室主要放置13具陪棺。北室主要放置兵器、车马器及简册。东室放置主棺、陪葬棺,还有一些兵器、乐器、漆器和金器。中室放置编钟等礼乐器。
这座大墓的随葬品,诸如青铜礼器等,数量众多,异乎寻常,它们完整地保存于地下达两千四百多年,可谓我国考古发掘史上一大幸事。墓中出土众多音乐文物,是我国先秦时期音乐辉煌发展的见证,令人震撼,不仅大大改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也为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揭示了灿烂篇章。这些音乐文物主要集中在大墓的东室和中室,特别是中室,展现了当时“金石之乐”的壮观场面。宏伟的曾侯乙编钟,甚至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前辈学者对该墓音乐文物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取得巨大成绩。已故黄翔鹏先生对曾侯乙墓乐器和乐律成就的研究,成果突出,他对中室金石之乐的性质也有重要探索。他曾指出该墓一次出土金石丝竹以及建鼓等多种乐器共一百二十多件,但“其中并没有典礼场合用以起乐、止乐的‘柷’和‘敔’,这些乐器的布置和酒器形成一种配合关系,也许是一种宫廷讌享日常使用的乐器配置吧!”①
不少学者同意和采取这一观点。本文作者之一便曾在一本小书中写道:“对比《礼记·乐记》和《诗经》中《那》、《有瞽》等篇所记载描述的钟磬乐队,曾侯乙墓中室没有柷、敔、鼗等乐器,也就是少了所谓‘德音之音’六件中的四件。加上这一乐队演奏者是殉葬的女乐,说明曾侯乙金石之乐的性质,不是‘祭祀先王’和‘献酬酳酢’的庙堂之乐,不是魏文侯‘端冕而听’的那种‘古乐’,而应是艺术性、娱乐性较强的‘女乐’和‘新乐’”。②
现在看来,我们所持这一观点,应再斟酌。这里谈谈我们对中室金石之乐性质的一点新考虑,也是对我们原看法的自我批评,希望大家指正。
一、中室金石乐悬的基本性质究竟如何
1.原先作出中室乐悬性质判断时的若干依据
当时认为中室金石之乐可能是“女乐”和“新乐”,除没有柷、敔等雅乐乐器外,还有其他考虑。一是曾侯乙墓东室和西室,有多达21具随葬女性骸骨。经鉴定,东室随葬女性均在19—26岁之间,西室随葬女性均在13—24岁之间。因此专家们推测,东室随葬女性应是曾侯乙生前妃妾或近侍宫女;西室13位女子,木棺制作比东室好,随葬物也较东室为多,她们很可能是宫中的乐舞奴婢。③这从一侧面显示曾侯乙生前喜好音乐。陪葬的乐舞奴婢,是乐器演奏者还是舞者,尚无充分证据,但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她们与中室金石之乐联系起来,视为乐器演奏者或相关歌舞的表演者。二是据《左传》等文献记载,当时日益兴盛的“女乐”、“新乐”即所谓的“郑卫之音”,与宫廷原有的金石之乐,并非绝然分离。这对我们判断曾侯乙墓中室金石之乐为燕乐、女乐服务,也有很大影响。
“郑卫之音”,原指郑、卫等地(今河南新郑、滑县一带)音乐,实际上是一种保留了浓郁商族音乐风格的民间音乐。从《诗经》中郑、卫两国的“国风”和有关郑、卫两地民间风俗的文献看,郑卫之音热烈奔放、生动活泼,仍保留商代音乐优美抒情、色彩华丽的特点,比较富于浪漫气息。④应该指出,孔子等人强烈指责的“郑声”或“郑卫之音”,并不包括西周制礼作乐以来,盛行于天子及各国诸侯宫廷的“郑风”及“卫风”。因为对“郑风”、“卫风”在内的《诗》(《诗经》),孔子曾“一言以蔽之”,誉为“思无邪”。孔子不仅自己对《诗》中所有作品“皆弦歌之”,还把它们作为“六艺”的主要内容亲自传授。显然,“国风”所收的传统“郑风”、“卫风”,在孔子眼中,应属于他极力推崇的“雅正之乐”。
孔子曾斥责“郑声淫”,主张“放郑声”。他深恶的“乱雅乐”的“郑声”(《论语·阳货》),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郑卫之音”(郑风、卫风),而与“新乐”、“女乐”密切关联的流行之乐。孔子之所以决然去国,就因为鲁国当权者接受了齐国馈送的“女乐二八”及其他礼物。⑤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外交拉拢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其大宗赂以女乐”的记载,则表明连一些官司,人们也通过送“女乐”来行贿走后门。
这种“新乐”、“女乐”表演,往往与金石之乐有关联。《左传·昭公二十年》说:“高台深池,撞钟舞女”;《史记·楚世家第十》说:“(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礼记·乐记》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看来当时金石之乐陈列或表演的场合,可能有“女乐”即“郑卫之音”接续出演。传统的钟鼓陈设与礼乐格局,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配合新乐、女乐的表演。
文献记载还表明,郑、卫之乐的传播输出,不光是女乐或“靡靡之音”。例如强邻环伺的弱国郑国,便常向强邻“赠送”女乐歌舞和编钟、编磬等金石乐器,以求少受欺负。《左传·成公十年》载:“郑子罕赂以襄钟”;《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鏄磐,女乐二八”,都属显例。
上引材料说明,不仅归属《诗》乐的传统“郑风”、“卫风”,可与金石乐悬合作,作为“新乐”、“女乐”的“郑卫之音”,也往往同金石之乐关联。因此,判断曾侯乙墓中室钟磬乐可能是燕乐、女乐,似有一定道理。
2.对旧判断的几点质疑
但上述判断并不稳妥。一方面,曾侯乙墓中室的金石之乐陈设,应是沿袭西周以来宫廷雅乐表演的盛大规模。中室巨大的编钟出土时,基本依原始编组和悬列方式悬于架上,显出规律和秩序。钟架(簴)高达3米、长达11米,64具钟,分为8组3层悬挂,上层为3组纽钟,19件;中层为3组甬钟,33件;下层为2组大型甬钟,12件。错金青铜甬钟,金碧辉煌,尤其下层钟体量巨大,令人震撼。曲尺型钟架靠西壁和南壁架设;编磬则靠北壁立架;建鼓树立在该室南部东壁旁。靠近编钟东端。瑟、笙、箫、篪和2件小鼓,因椁室内积水有所漂移,但大体上仍可看出,这些丝竹乐器及小型鼓,原放置于钟、磬、建鼓所围构的长方形空间之内。这种三面悬金石,其间并陈丝竹,正如有些前辈学者指出,应是春秋以来诸侯宫廷乐队基本建制,符合其演奏时的大体布局。
另一方面,若以没有柷、敔等“德音之音”乐器同出,作为判断该墓金石之乐不是雅乐的重要依据,却不尽可靠。目前音乐考古虽发现诸多乐器及乐器组合,却没有发现柷、敔等乐器实物。或许柷、敔等乐器属于“八音”之“木”,难以保存,但琴瑟等丝竹乐器也有不少出土,唯有柷、敔等迄无一例发现;在先秦考古图像中,亦不见其踪影。这恐怕不全属偶然。如坚持这一条件,则已知先秦全部金石乐悬,均不属于宫廷“雅乐”乐器。因为没有柷、敔等乐器的出土实物,周代雅乐就只存在于文献中,这岂不变成了“纸上谈兵”?显然,不能将柷、敔等乐器作为判断雅乐的必要条件。
再一方面,“新乐”也好,“女乐”也好,“郑卫之音”也好,既可能与金石之乐合作,若换一角度思考,则金石之乐当然可能继续演奏宫廷雅正之乐,或根据礼仪庆典需要,先奏雅正之乐,之后也奏新乐、俗乐。
换言之,作为礼乐陈设的金石乐器,其传统性质或基本性质,与它所能演奏的多种乐曲性质,不必完全吻合绝对一致。金石之乐长期主要演奏“古乐”,固然属于宫廷雅乐而为宫廷礼仪服务,但它们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功能强大的音乐工具(乐器、乐队),当然可以演奏多种性质的音乐,如《诗》乐中的风、雅、颂等乐,宫廷贵族所喜好的燕乐,以及新乐、女乐等流行之乐。
演奏多种音乐,并不意味金石之乐的传统性质彻底改变。就像钢琴,本属西方“高雅音乐”或“严肃音乐”工具,但它既能演奏“古典音乐”、“高雅音乐”,也可以演奏各种民间音乐、乡村音乐,以及各种流行音乐、爵士乐,也可以成功演奏中国及其他各国音乐,这些时候钢琴不也充分发挥着强大的乐器功能?又如中国的“民族乐器”,历来主要演奏中国传统音乐,不也可以自如演奏新创作的音乐和流行音乐,同时还可以成功演奏外国的音乐。它们作为“民族乐器”或“国乐”传统属性,与所能演奏的音乐性质,不必完全一致。它们并非“从一而终”地只能为某类特定的音乐服务。
长期演奏宫廷雅乐的先秦金石之乐,既可继续服务“古乐”,也可以配合新乐、女乐等新流行音乐,不正是春秋战国所谓“礼崩乐坏”之后,音乐实际上大有发展的一种生动写照吗?
3.曾侯乙墓中室金石乐悬的再认识
我们再来看中室乐悬,有一点非常重要不容忽视:中室金石乐悬,原与同室大量礼器、酒器并置,共同构成一道完整、统一的文化景观。
曾侯乙墓中室不仅呈现金石之乐的盛大场面,同室出土的礼器、酒器,制作也非常精美,体量也十分宏大,它们主要存放于中室南部,成组成排,摆列有序。
首先是显示身份等级的重器“九鼎八簋”,它们分类放置,十分齐整。鼎是周代贵族“别上下,明贵贱”的青铜礼器,在众多青铜礼器中尤具举足轻重的意义,是重器中的重器。“九鼎八簋”本属周代天子身份的象征,曾侯乙墓也按最高的天子级别列鼎,显然超越了旧的礼制等级规范,尽显奢华尊贵。该墓所出鼎分三种共22件。大鼎庄重厚实,显然是曾国祭祀之重器。八件簋,形制、大小相同。
中室还出土了著名的尊盘、鉴缶等“酒器”。尊盘用“失腊法”铸造,体现了当时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无比精美。其实,它们和同出的鼎簋(最初也从食具发展而来)等一样,也应属于礼乐仪式中的“重器”。
这些用于祭祀的礼仪重器,尽情展现显赫的列鼎制度。
与上述礼制重器相伴的中室乐器,有编钟、编磬、鼓、琴、瑟、均钟(律准)、笙、排箫、篪等9种,共计125件。还相伴出有与部分乐器配用的击奏工具(如钟槌、鼓槌等)10件和各种附件(如钟架、磬架、磬匣、瑟柱)等。金石之乐的宏大辉煌,与同室礼器恰相辉映。显然,整个中室展现的,是极其辉煌的礼乐祭祀完整场面。
青铜礼器与乐器,在礼乐仪式中同等重要。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礼乐器总重超过十吨,而曾侯乙编钟竟重两千二百多公斤,尽管曾侯乙墓的随葬品数量规格,大大“僭越”本应严格遵循的礼制等级,正说明曾侯乙的继承人,恪守敬天祀神原则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价值观,极力显示礼、乐并陈之豪华,竭力装点墓主的荣华富贵,以表明墓主权势和财富的不同凡响。
中室金石乐悬,与同室礼器的陈设是一个统一整体,是盛大庄严的礼乐场景,生动体现“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通志·乐略》)的紧密结合。此前,曾有谭维泗等考古专家,称誉曾侯乙墓为辉煌的“礼乐地宫”,这一说法正确道出墓中豪华礼、乐器陈设的根本性质,在显示墓主显赫权势和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展现这一时代礼乐并举交相辉映的超前格局。
4.楚王镈铭文进一步揭示中室为地下宗庙祭祀场景
曾侯乙墓出土青铜钟其实共65件,但前面我们说编钟由64件纽钟、甬钟组成,其实还另有1件大镈,悬挂于钟架下层,以其另类的形制纹饰而引人注目。该镈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体扁椭形,上有立蟠龙形复式纽。
该镈钲部为梯形,一面光素,一面有铭文3行,计31字:
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
(方伤)阳,楚王酓(熊)章乍(作)曾侯乙宗
彝,奠之于西(方伤)阳,其永(口寺)(持)用享
铭文大意是楚惠王熊章在56年,获悉曾侯乙死讯,作此镈(宗彝),用作宗庙祭祀。我们认为,铭文是准确判断曾侯乙中室乐器性质的重要依据。
据《汉语大词典》,“宗彝”指宗庙祭祀的酒器。广义的宗彝,则指专用于宗庙祭祀的礼器,也称“宗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重之以宗器”,杜预注:“宗庙礼乐之器,钟磬之属”,则包括宗庙祭祀的各种礼乐器。又《辞海》解释“奠”是“祭奠,向鬼神献祭品。⑥说明古人运用礼、乐器于宗庙举行祭祀,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
铭文说明,楚王为祭奠慰籍去世好友曾侯乙,特意制作了包含此在内的一套钟(“宗彝”),并在“西阳”举行祭奠。曾侯乙入葬时,其后人取下此镈,加挂在中室簴架上。显然,该镈与曾侯乙编钟不是同套乐器,主办丧事者则希望籍此镈将楚王祭奠曾侯乙的一片情意,带入地下永久存续。即便曾侯乙生前很可能非常喜爱“新乐”、“女乐”,也许曾用钟磬兼奏俗乐或伴奏女乐歌舞,但中室随葬的金石乐悬,与同出“九鼎八簋”等礼器重器,经由楚王镈铭文进一步点明,均属祭奠的“宗器”。整个中室的礼乐陈设,其宗庙祭祀的特性,由此得以揭示和确证:曾侯乙墓中室,是一个逾越等级限制的壮观的地下宗庙祭祀殿堂,室中金石之乐,当属地上宗庙之乐(雅乐)在地下的延展和久远回响。
二、再探“礼崩乐坏”的实质
关于“礼崩乐坏”的问题,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到底有没有“崩”?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到底有没有“坏”?曾侯乙墓中室的盛大壮观的礼乐场面,给我们带来了重要的新启示。
1.“礼崩”的含义
《礼记·明堂位》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为巩固其统治,制定了一整套封诸侯、建国家、严格等级的礼乐制度。
“制礼作乐”据说是周公进行的文化创新,但根本实质正如《中华文化概论》所说:“乃是确立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⑦《礼记·曲礼上》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游桂注:“庶人不庙祭,则宗庙之礼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则车乘之礼所不及也;庶人见君子不为容,则朝廷之礼所不及也。不下者,谓其不下及也。”说明“礼”原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为统治者所拥有的。“礼别庶人”、“礼不下庶人”记载,反映礼制所要确立最大的等级区分,是要强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天壤之别,要求人们承认等级尊卑而安分守己,更好维护现有统治。
由于“礼”体现着“立国经常之大法”,因而在等级社会中具有维护统治规范和道德规范的作用,是统治阶级凸显威风的一种工具,也是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核心手段。
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争夺激烈,王室势力剧减,群雄纷起,天子地位一落千丈,新兴中下层贵族不断扩展势力,纷纷突破旧有等级限制,竭力问鼎更高权利和地位,各诸侯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断僭越礼、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随之来临,旧的格局被打破,诸侯、陪臣用乐竞相攀升,甚至逾越天子,出现严重的“文化下移”现象,这是维护旧礼制者痛心指斥的“礼崩”。
从字面上看,“礼崩”说的是礼制崩溃,即严格限定的等级规范被严重破坏,使其失去了约束力。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2.“礼崩”的实质
周代礼乐制度中,鼎制和乐悬制度是现实身份等级的标志。曾侯乙墓中,各种礼乐器以九鼎八簋为中心,钟磬共列一室。一般认为,诸侯用九鼎是对礼的破坏。但是从钟磬的悬制来看,不全如此。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有学者认为,曾侯乙编钟呈曲尺形靠椁室西面、南面悬挂,编磬靠北面悬挂,符合文献“诸侯轩县”的记载,所以当时诸侯使用九鼎可能并非僭越。⑧但曾侯乙列鼎体量之巨大、纹饰之精美,仍为西周和春秋以来同类器物所少见。
曾侯乙墓葬出土编钟共计65件,是一套举世罕见的庞大乐器组合。至今仍属世界少见的庞大乐器,其规模、数量、体量及错金纹饰之奢华,远超目前所知西周、春秋时期各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编钟组合。
的确,从维护和固守旧的礼制等级的角度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礼”似乎严重崩坏了:严格的等级制度被打破,被忽略,被僭越。但曾侯乙墓大量出土实物显示,它仍是一座辉煌的“礼乐地宫”,仍充分体现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本质。
我们曾在李宏锋博士论文《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的《序》中谈到对所谓的“礼崩乐坏”,如果试换一个视角,就会显示另一番风景:
“礼崩”既不是西周以来的宫廷礼乐建构的全面崩溃,也不是礼仪制度荡然无存,从而社会全然“无礼”约束的时代。“礼崩”更不是从天子到各国诸侯、陪臣以及各种新兴的政治势力,全都放下架子,放弃礼制所规定的排场享受,与百姓、奴隶等社会底层同甘共苦进入浑然一体的“无差别境界”。⑨
所以,“礼崩”不是礼制彻底消灭,不是等级制度和阶级隔阂的彻底废除,也不是“刑不上大夫”和“礼不下庶人”被根本捣毁。yOGfgOuoZGNV3UDwe/262rTxuxVMsaAX2MKIxp1MlSg=春秋战国“礼崩”的实际结果,反而是是礼仪享受的放开竞赛,是各国诸侯竭力“大其钟鼓”,人人“九鼎八簋”,是二三等诸侯小国君主曾侯乙墓那样空前豪侈的礼乐陈设。文献记载和地下出土实物史料表明,“礼崩”其实是“礼未崩”,结果“是显示统治者权势威风和社会享受的一座座更加富丽堂皇的礼乐大厦,反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横空绝世”⑩。
实际上的“礼未崩”,也促进了实际上的“乐不坏”,音乐反而得到某种解放,实现了长足的进步。曾侯乙墓乐器和乐律材料所反映的当时音乐艺术的高度发展水平,正是“乐不坏”的生动说明。
三、结 论
曾侯乙乐器的陈列,固然有“事死如生”,再续其生前热爱音乐生活的愿望,但其重点不是展现“新乐”、“女乐”欢乐起舞场景。它所展现的,应是礼乐并陈,庄严豪华的祭奠场面,充分体现了曾侯乙后人对他的尊崇之情思念之情,正如楚王镈铭文所揭示,地下的音乐宫殿,其实是地上宗庙之乐的象征。
虽然中室金石乐悬,与众多礼制重器一起体现庄严的宗庙祭祀场面,表明其具有雅乐性质。作为当时宏伟的乐器和乐队,也可以成功演奏新乐,伴奏女乐歌舞。雅乐本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孔子推崇的《诗》,表明颂和大小雅之外的原非“雅乐”的十五国风,已被视为扩展了的“雅乐”。后世宫廷“雅乐”,也同样有大量俗变雅的例证。例如,刘邦用“楚声”(俗乐)演唱的“大风歌”,被120名“小儿”长期合唱于沛县祭奠他的“原庙”(即宗庙)时,便成为汉代重要的汉高祖“庙乐”即“雅乐”。当秦王李世民征伐时的军中歌曲《秦王破阵乐》(俗乐)被高奏于唐太宗登极的大朝会时,李世民也高兴地没料到它们也能“登于雅乐”。
另一方面,原属“雅乐”乐器的金石之乐,也可以在不同场合演奏不同音乐,甚至为郑卫之音、女乐歌舞服务。曾侯乙墓中室金石乐悬也很有可能为墓主生前喜爱的女乐歌舞伴奏,但中室的礼乐陈设,则凸显了它们作宗庙祭祀的地下展示强调了钟磬之乐的雅乐品格。
由曾侯乙墓礼乐地宫,联系文献和出土实物史料,可以看到,礼是区分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维护上下尊卑秩序的一种重要工具,所谓的“礼崩乐坏”只是为统治集团内部等级规定的“被破坏”而发出的哀叹。“礼崩乐坏”的真实结果,不是礼制的全面崩溃,更不是“大夫”与“庶人”走向平等。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礼从内部不断被僭越,显示统治者权势威风和奢华享受的更多富丽堂皇的礼乐大厦接踵矗立。同时,也表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民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越来越深,社会上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这,预示着一场历史的疾风暴雨,即将来临!
①黄翔鹏《古代音乐光辉创造的见证——曾侯乙大墓古乐器见闻》,《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②秦序《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③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的礼乐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④冯洁轩《论郑卫之音》,载冯洁轩音乐文集《金石回响》,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又见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⑤《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又见《论语·微子》、《史记·孔子世家》。
⑥夏征农、陈至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3页。
⑦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华文化概论》(增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李学勤《东周与秦汉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⑨李宏锋《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⑩同⑨,第3页。
秦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孙琛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