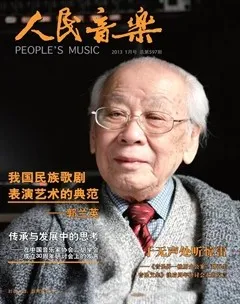声乐表演的新思路
12年5月25—27日,男低音歌唱家田浩江在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举行了三场独具匠心的“演唱会”——个人舞台剧。笔者有幸前往观看,之后心情久不能平静。这不禁使我想到了我国当前的声乐教学状况,声乐教师在培养学生的演唱技术的同时,还应该指导或鼓励学生去关注什么?学习什么?文章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详细介绍与评论这一场别开生面的舞台表演,第二部分重点谈《我歌我哥》对当前声乐表演的反思以及由这场演出所启发出的新思路。
“个人舞台剧”在中国音乐界还是一个较“新鲜”的名词,虽然看上去并不难理解,但究竟该如何定义这个“剧种”,却似乎并非一句话就能说得清楚。一个人在舞台上一个半小时,让观众津津有味地欣赏而不令人生烦,实在是一件难事。即使灯光舞美极其华丽的明星个人演唱会,也需要众多“帮手”的参与。更何况对于一个舞台道具极其简单,多媒体设备只有一个投影和必要时的一些音响配合而已的个人舞台剧,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次演出的舞台设计极其简单,是一个用参差不齐的木板钉制的反“7”形台,台上台下有些零乱地堆积着一些破旧的木箱子,还有一架旧钢琴,在隐蔽处放着一台手风琴和一把吉他,多媒体只有一个投影。这就是最初看到的样子,简单到你不敢相信接下来的表演会是什么样子。故事梗概如下:正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意大利歌剧《艺术家生涯》的华人歌唱家田浩江接到一个北京的越洋电话,得知自己的“哥哥”病危,在他的恳求下,歌剧院答应他回去见哥哥,但绝不可以耽误三天之后的演出。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田浩江回到了北京,见到生命垂危的“哥哥”。在这短短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兄弟二人不仅回忆了很多过去有趣的往事,更重要的是,在交流中他们重新认识了彼此,解开了许多以往困扰在彼此心灵间的谜团。他们最后的谈话,没有悲伤,没有生离死别的绝望,在欢笑和歌声里诉说着最后的眷恋。再次回到纽约的田浩江无法继续下一场的演唱,“哥哥”这样一个充满无限亲情的概念,使他在感悟和回忆中挣扎,不能自拔?熏几乎进入了一种疯狂的状态,最后在他扔掉礼帽,唱出了“哥哥”经常唱过的唱句:“哥呀我,心里多快活……”,投影上是一只正在飘荡着的“哥”承诺给“我”做的小帆船……“时空交错的恍惚、革命歌曲与歌剧文化的对撞挣扎、人性深处的真情袒露,中国变革过程中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使这个剧作充满了戏剧性的力量,也揭示了现今世界许多似已漠视和遗忘的追求和理念。”①
《我歌我哥》是一个叙事与抒情兼而有之的舞台剧。笔者认为,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表演者在叙事过程中,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浓浓的亲情,也正是这种深藏在内心深处多年的兄弟感情,深深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从这一层意义看,其实表演者的叙事过程本事就是一种抒情,或者说是为感情的高潮酝酿情绪的过程。总的来讲,抒情才是这场演出成功的关键。从舞台剧发展历史来看,一开始以叙事为主风格的舞台剧已经随着影视剧的出现而逐渐衰退。其原因在于舞台剧在其叙事方面缺乏时空的真实性,它的时空局限性导致了“其表演必然带有虚拟性和假设性”②,从宏观上讲,舞台剧不能再现真实的自然环境和千军万马;从微观上讲?熏舞台剧没有能力给具有特殊意义的细小事物以特写。但是抒情性舞台剧在经过无数考验之后,到如今依然焕发着其旺盛的生命力,原因在于“演员与观众的情感交流会使二者处于生命力洋溢的抒情状态?熏剧场也因此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场。或者说,剧场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大生命——抒情的、丰满的、完整的大生命。可以想见?熏这种生机勃勃的大戏剧对于观众的诱惑力会有多么大!”③所以,情感的交流需要一个能够接触到彼此的共同的场,这也正是抒情性舞台剧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
抒情是需要技巧的,单一的情感表达很快会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尤其是没完没了的感慨。在这部剧里,表演者的叙述方式以与“哥哥”在病房里三个小时的此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坦诚以对的心理交流为主线,中间穿插了众多“我”与“哥”之间的趣闻轶事,这些“小故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猛一听起来甚至有些杂乱,但是细想起来这正是主创人员想要的效果。试想,如果众多“小故事”能够连起来,整场舞台剧必然成为“一个大故事”,那么必然破坏演出的抒情性,或者说破坏了“病房里兄弟两个心理交流”的这条主线,势必让叙事成为其主导,那么就会削弱这场舞台剧的艺术效果。
抒情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是歌唱,我们不要疏忽了田浩江是颇有实力的歌剧演员,他在话白中插入15首歌,以及“哥哥”的一句唱词(“哥呀我,心里多快活”)、一首歌剧咏叹调(威尔第《唐卡洛斯》中菲利普国王的咏叹调)、用手风琴演奏一首儿歌(《小苹果》)以及解说一首交响曲(贝多芬《第六交响曲》)。有趣的是每一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由于篇幅所致,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歌曲作品并非由某位作曲家专门为田浩江量身定做的声乐作品,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歌曲。他之所以这样选曲,首先对他自己是一种挑战,因为演唱经典作品极有可能出现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这些经典歌曲已经由原唱者深深植入民众的脑海中,所以翻唱就预示着一种冒险,除非能够在原作的基础上力争超越,唱出新意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田浩江对自己有信心,同时这也是一个演员的必备素质。其次,选择这些歌曲的优点在于,大部分在场的观众都是听着这些歌曲长大的,田浩江相信在自己演唱这些歌曲时定能唤起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那份温暖的记忆,而这些恰恰正是能够更好地加强演员与观众之间心灵交流的关键因素。没有这些,很难想象演员如何与观众建立心灵的桥梁?熏而如果一个演员没有与观众在心灵上建立某种联系的能力,那么他的表演也必然面临失败。
田浩江在台上的表演除了他充满魅力的、雄浑结实的男低音音色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对经典作品的重新演绎,而后者才是他成功的秘诀所在。15首经典歌曲的演唱和伴奏都由他一个人来担任,并且在伴奏当中除了钢琴这一件乐器外,还有吉他和手风琴都有精彩展示,他的多才多艺充分展示了作为一个歌唱演员的可贵素质。从观众的心理角度来看,其实观众最想看到的是演员通过自身多方面的才能展示,最终达到一种统一的令人振奋的艺术效果,这才是一种“活”的表演,而不是那种跟着已经制作好的伴奏唱“卡拉OK”,形式僵化无趣。另外,田浩江集演唱、伴奏与表演于一身的舞台形式,更有利于舞台节奏和情绪张弛的控制,以及与观众进行互动。
在他演唱众多歌曲中,囊括了中外20世纪前叶、中叶在激情燃烧的战火纷飞与和平建设的岁月中,集中体现那个时代精神的经典作品。表现内容几乎涉及到了各个方面:体现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的有《我的祖国》;体现对领袖崇敬之情的有《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体现军人情结的有《人民海军向前进》、《军港之夜》、《我是一个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体现战争年代爱情题材的有《山楂树》、《红河谷》、《喀秋莎》;体现年轻人青春活力的有《歌唱动荡中的青春》;体现对儿时美好回忆的有《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小苹果》;体现民族情结的有《洗衣歌》、《三十里铺》。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田浩江的演绎才能。其中《三十里铺》是清唱的,这本来是“哥”在病房中为“我”唱的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歌曲,“我”也就是从这首歌中才真正认识到“哥”原来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天才。在这些作品中,每一首作品都承载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汇集到一起,就是兄弟之间深厚的情义。但是,真正将这些歌曲联系到一起的却是“哥”的那个唱句“哥呀我,心里多快活”,这句唱词集中体现了“哥”豁达乐观的性格。因此,这句唱词在整部剧中共出现了三次,并且一次比一次揪心。第一次出现是“我”到老家山西晋城听到“哥”得意地从麦场走过时唱的;第二次是“我”再次回到大都会后,因对“哥”的逝去而痛心,无法再演唱歌剧唱段时,改唱的这句唱词;第三次是全剧最后一个舞台表演场面,“我”换上陈旧的休闲装光着脚丫坐在地上钓鱼,边钓鱼边“悠闲”地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这句唱词,然后全剧终。
全剧结束后,观众的掌声久鸣不断。田浩江的成功不是偶然,近三十年的演唱生涯造就了他娴熟的歌唱技巧、高超的演绎才能以及超强的与观众互动的能力,这难道不正是一个优秀的歌唱演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吗?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相信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演员永远都应该恪守的准则。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我极力呼吁在声乐教学中让学生多关注一下演唱技巧之外的东西。因为歌唱是一种表演,演唱者必须要有强烈的表演意识,而表演又是一种具有一定综合性的才能展现,而绝非一个演唱技巧所能胜任的。而综合性表演才能的培养需要让学生更多关注技巧以外的东西,比如责任心的建立、情感的培养、文化修养的积累、积极乐观的处事方式、较强的沟通能力等等,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台上表演的效果。事实上当前的声乐教学过分关注技术的灌输,疏忽了歌唱本来就是一门表演艺术。拥有一副动人的歌声固然重要,但作为一种舞台艺术来讲,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舞台艺术本来就是一种集视与听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如果只是听,在家听CD就可以了,何必要上剧院?我记得最近有一场叫做《太阳之王》音乐会,其中有一首曲子《地狱故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原因并不完全在于音乐的组织,倒是演唱者的表演意识深深震撼了我,在场的观众都被她的综合表演才能深深折服。这就说明,表演是一个演员多种才能的综合。
当前音乐学院的声乐硕士在毕业时都要求举行一场个人独唱音乐会,在笔者观摩过多场这样的音乐会之后,甚是失望,几乎场场都是歌曲一首首地唱,甚至很多表情木然,能够看出来演唱者“表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几乎将全部精力放在了体验技术运用情况方面,千遍一律,毫无创意可言。这种“表演”实在不看也罢。其实这些个人独唱音乐会不吸引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演唱者把“表演”看作了“演唱技术”本身,而对音乐会的其他方面则漠然视之。如今,田浩江的个人舞台剧《我歌我哥》却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那就是将看似一些不相干的曲目用一种独具匠心的方法联系起来,让整台音乐会不再是一首首歌曲的联唱。很显然,将独唱音乐会曲目联系成一个具有“剧”性特征的表演,的确需要花费一些心思,这就要求演唱者也许只能专门请人为曲目编“剧”,为表演过程设计动作、情绪以及整体的逻辑关系。但是,这些辛苦的劳动对于演出结束后,所能够达到的全方位完美的艺术效果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①摘自当晚演出的节目单。
②③王晓华《叙事性舞台剧的衰落与抒情性舞台剧的兴起——论舞台剧的命运》,《艺术广角》1999年第3期。
徐红磊 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张丽华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