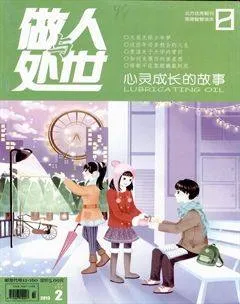唯爱永恒
1927年10月,一阵初秋的骤雨后,宁静肃穆的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诺隐修院,遍地金色的梧桐叶,像飘落一地的心,纷飞,旋转,渐至沉寂。空旷的隐修院大厅内,一场简单又隆重的更衣礼正在举行。一个身材挺拔。气韵高雅,面容沉静的中国人。正缓缓脱下浅灰色的笔挺西服,换上黑色宽松的修士青袍,正式成为隐修院的修士。他就是民国初年煊赫一时的内阁总理陆征祥。这年,他五十六岁。
陆征祥先后八次出任民国外交总长、两次担任内阁总理,是民国传奇人物。可正当春风得意,官运亨通之时,他却奔赴异域遁入空门。而这一切,都与一位名叫培德的比利时女人有关。
1892年,沙俄向清政府提出谈判帕米尔划界问题。这年初冬,二十岁的陆征祥,是北京同文馆优等毕业生,奉清廷指派,担任圣彼得堡驻俄公使馆四等翻译官。陆征祥外文水平极好,又机智伶俐,很快就得到钦使许景澄的赏识,收为门下弟子,随他学习外交礼仪,联络外交使团。圣彼得堡冬宫,是沙皇的宫殿和住所,巴洛克式建筑的典范,金碧辉煌,常举行宫廷酒会。陆征祥精通洋文,熟悉外交礼仪,又善于应酬,许景澄每次受邀,都会带他参加,悉心栽培。弱国无外交,欧洲列强看不起中国,宴会中,许景澄颇受冷落,但少年英俊、谈吐文雅的陆征祥却是另一番风景。陆征祥跟其他清朝驻外官员不同——他没留长辫子,也不戴顶戴花翎,他穿西装,戴领结,气宇轩昂,风度翩翩,尤其一口流利标准的英、法语,谦和而不失庄重的微笑,儒雅而不乏气势的举止,在衣香鬓影、富丽堂皇的社交场合上,不知不觉攫取了人们的目光,各国使节都乐于与他交往。渐渐地,陆征祥成了圣彼得堡社交圈里的活跃人物,博得不少外交官夫人的好感。有一天,他发现,当他翩翩起舞,当他侃侃而谈,甚而,当他默默站立一边,总有一双热情好奇的蓝色眼眸追随着他,而当他终于捕捉到这视线时,瞬间,他的心就被这蓝色的海洋淹没了。眼眸的主人,叫培德。
爱情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让人措手不及。培德女士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她的祖父和父亲均系比利时高级军官,她举止娴雅,又有家传的刚毅,常出入各种宴会,以舞姿优美而倍受青睐。当她第一次得知陆征祥是中国外交官时,颇感惊奇,古老的中国在她眼里,神秘遥远,像猜不透的谜,而眼前的这位中国青年,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一改她对中国人的不良印象,她不知不觉被他亲切却疏离的神色吸引了。在沙皇宫廷圣诞舞会上,她走到他面前,伸出手,邀他共舞。当他挽着培德纤细的腰肢,随着音乐进退旋转,翩翩起舞时,笑容背后,仍是东方人的谨慎。陆征祥虽善与洋人打交道,但始终心存戒备。在他眼里,高鼻金发蓝眸的洋女人总不如东方女人婉约有味。培德却异常地兴奋,她不停地提问,为什么中文这么难?中国人用筷子怎么喝汤?你会功夫吗?她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用法语,还不时蹦出俄语单词。她的问题既怪异又新鲜有趣,逗得陆征祥只想笑。但他仍捺着性子,不失绅士风度,一一作答。一场舞下来,他心中自卑和戒备的壁垒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喜欢上了这个热情大方、率真漂亮的比利时女人。而陆征祥优雅的舞姿和非凡的风度也俘虏了培德的芳心。爱情采得太突然,舞会结束时,两情依依,竟不愿分手。培德提出约会要求,陆征祥满口答应。在随后的约会中,他和她愈来愈倾心,难分难舍,深深坠入爱河。灿烂迷人的涅瓦河畔,庄严宏伟的喀山大教堂,到处留下他们爱情的足迹。一年后,他们决定结为终身伴侣。
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理由,可这理由却往往说服不了尘世中人。那一年,陆征祥24岁,培德46岁,与他母亲同龄。彼时,中国人视洋人和洋货如洪水猛兽,娶外国女子,且是母亲辈的女子,无异于大逆不道,陆征祥的父亲气得一病不起。亲友们也认为,堂堂中国人,娶洋女人为妻,有辱列祖列宗,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生下的混血儿既不能进家族祠堂,也不能入祖坟。清廷使馆上下也反对这门婚事,理由是外交官不能娶外国太太,使馆的朋友提醒他:“你这样做,会断送你的前途。”陆征祥淡然一笑说:“我知道,我不在乎金钱权势,也不要什么锦绣前程,在我心中,唯爱永恒。”
公使许景澄亲自出面极力劝阻,于公于私,他都不愿失去陆征祥这个左膀右臂。陆征祥一向敬重恩师,他深情地说:“我一生能有今日,都是靠着一位贤良的老师。”但这一次,他和恩师辩论起来,他坦言:“我爱培德思想不群,品德高尚,断事有则,立身无私,不畏难,不欺人。”他的心已坚如磐石,他深信,他和培德的灵魂和心灵是为对方而造的,是上天冥冥中的安排。生平中,他第一次拒绝恩师的要求。许景澄十分赏识陆征祥的才华,又视他为己出,他不愿陆征祥因婚姻毁掉前程,更不愿清廷失去一位年轻优秀的外交官,劝阻不成,他便奏明清廷,从利于外交出发,准其联姻。但要求陆征祥,在正式场合,不可带培德出席。
1899年2月12日,陆征祥和培德初相识的纪念日。他们在圣彼得堡圣加利纳大教堂,由天主教神父证婚,在天主教圣歌《因为爱》庄重而温暖的旋律中,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打开心门的钥匙,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爱,让天地无障碍,对别人要关怀,对自己也疼爱,对于未来用心期待。”
幸福婚姻中,年龄从来不是问题,爱才是和谐婚姻中占主导地位的元素。婚后,培德悉心照料陆征祥,她学会了做复杂的“中国菜”,成了一位中国式的“贤内助”。培德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受她的影响,1911年10月,陆征祥受洗加入天主教,他们所能有的最后距离。也从此超越了。后来,陆征祥屡次担任外交总长,她总积极帮衬。每遇大事,都有她在他身边,扶助他,为他指点迷津。但为了避免飞短流长,她从不陪丈夫出入外交场合。陆征祥代表袁世凯在《二十一条》签字后,坦言“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成为历史无辜的牺牲者。他整日闷闷不乐,深深自责:“这是一件碎心的事。每年我们都有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我常要流泪。”培德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她安慰他,轻声细语地说:“多跟天主祈祷吧,天主是最了解真相的,天主会原谅你的。”尽管他们始终无儿无女,但生活和美融洽。在陆征祥心目中,培德的地位跟父母和恩师同等重要,他说:“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裁成我者吾师也。”他们这桩罕见的涉外婚姻,如此和美融洽,令人称奇。
美好的爱情易遭天妒。1922年,向来身体健康的培德竟一病不起,医生建议应往欧洲养病。为了妻子早日康复,陆征祥自愿辞去外交总长的职位,官降三级,担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陪她在风光旖旎的罗珈诺湖畔休养。到瑞士后的第二年,培德病势加重,引起脑溢血。医生以放血法来治疗,陆征祥便将放出来的血,一滴不剩地用瓶子装起,瓶上饰以干郁金香花,留作纪念。培德生病后,陆征祥深受刺激,时刻感觉大厦将倾,只要一想到不久夫妻就将诀别,他都哭得肠断心裂。他每天为她祈祷,希望天主能让奇迹发生,使她重获健康。为了减轻她的病痛,陆征祥亲自到罗马去朝圣,请求教皇为她祝福。一天,陆征祥握住病危中培德的手说:“爱你的心,永远不变,我誓不再娶,你走后,我进修道院隐修终身,期望能得到天主的赦免,到天国和你相见。”培德安然谢世后,陆征祥立即辞去驻瑞士公使的职务,毅然决然地走进圣安德诺隐修院。生命中的最爱已离他而去,他对滚滚红尘已无丝毫眷恋。
欧洲“鹿港小镇”,比利时布鲁日,浩瀚的北海潮起潮落,童话般朗丽的弗拉芒建筑,梦境般的红瓦白墙,风景优美的爱湖常有天鹅嬉戏,互相表达爱意——这是培德少女时代生活的地方。陆征祥选择在布鲁日隐修,直至终老,在他心中,这是离天国最近的地方,也是离爱情最近的地方。他的室内一桌一椅一榻,除经典书籍外,一无所有。在这里,他走的路,她曾走过,他看过的风景,她曾看过,他走在她生命中他来不及参与的岁月里,他仿佛听到她嬉笑的声音,看到她飘逸的裙角。他和培德,即便隔了生死,也从不曾分离。生命会终结,尘世会变幻,唯爱永恒。
编辑 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