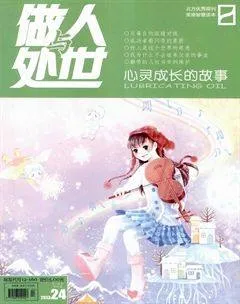成语古今两异义
历史是个小姑娘,理鬓贴花,涂粉抹脂,爱怎么整就怎么整。所以,史上许多人事貌似耳熟能详,可细究本源,往往令人瞠目结舌。不说别的,光是那些司空见惯的成语,古今比较,就别有一番风味。
比方说“推心置腹”,露面的场合十之八九是交谈。两人相见,开诚布公,都掏心窝了,自然能解开心结,消除误会,加强了解,增进情谊。正如前苏联作家温·卡维林所说:“推心置腹的谈话就是心灵的展示。”
可“推心置腹”原本是指刘秀的义胆之举。话说西汉末年,王莽篡政,群雄纷争。被皇室封为萧王的刘秀屡立战功,在大破于邬的农民起义军之后,他答应降军将领都分派官职。可降者心存疑虑,诚惶诚恐。刘秀为安抚人心,不仅给降军统领配备兵马,还亲自轻骑巡行,无丝毫戒备之意。降军将士见状,个个感慨:“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报死乎!”正是有了大量义军的倾心归附,刘秀的宏图霸业才逐渐成就。后人将“推赤心置人腹中”一句概括为“推心置腹”,也就有了这个成语。如今,原始意义上的“推心置腹”虽不复存在,但个中的“诚意”还在,偏离不算严重。
和“推心置腹”一样,“学富五车”也走了样。“学富五车”形容的是一个人学识渊博,也就是读书多、学问大。“五车”就是说读的书可装五辆车子。不管是竹片书,还是木片书,反正是个饱学之士。
然而,当初那个“学富五车”的人,不是读了“五车书”,而是写了“五车书”。《庄子·杂篇》曰:“惠施有方,其书五车。”惠施这家伙热爱思考,道术很多,产量很大,写的书足足有“五车”。按“等身”算,等八个十个绝对没有问题。可庄老头子后面的话是:“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舛,差殊也;驳,杂糅也。也就是说,惠施说的道理多舛误且杂乱,言辞也有不当之处。虽说庄子是个行家,但老头子的话有没有夸大其词,论点是不是恰如其分,还须商榷。不过,“学富五车”与他老人家的原意不一致倒无须争议。
有的成语古今两意大同小异,而有的成语今昔相比相去深远。如“衣冠禽兽”,一说到它,自然是那些道德败坏的人,他们虚有人的外表,行为却如同禽兽,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这样的人,将卑鄙、下流、无耻、恶毒一类的词语全加上去,也不过分。
可“衣冠禽兽”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载,明代对官员的服饰有明确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将官服绘兽。文官的袍子绣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武将的袍子绘麒麟、狮子、老虎、豹子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禽兽,说明品级也不一样。可见,“衣冠禽兽”原指文武官员,是公务员队伍中的领导层、精英层,旁人都羡慕嫉妒恨呢!只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官员贪赃枉法、为非作歹,“衣冠”有“禽兽”者,老百姓当然唾之骂之。
又如“出尔反尔”,在今天也是个贬味十足的成语。它的意思很明了:说了又翻悔,说了却不做,表示言行前后自相矛盾,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固然没有“衣冠禽兽”可耻,却一样可恶。老是忽悠,老是变卦,一次两次还可容忍,次数多了,一定要整整这条“变色龙”。
但是,“出尔反尔”最初却并不让人讨厌。《孟子·梁惠王下》有这样的故事:邹鲁之战,邹国的官员战死了33人,而老百姓却没有一个愿意随长官而去。邹穆公很纠结——如果杀百姓的话,人数太多杀不完;如果不杀的话,又不解心头之恨。于是,他向孟子讨教。孟子的回答很果断:“眼前是饥荒年头,老百姓不是饿死,就是逃亡;可您呢,粮食堆满,金银囤积,您的官员却没有一个人实话实说。这就是对上怠慢国君,对下残害百姓!曾子说:‘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邹穆公这才明白,老百姓见死而不救,是那些官员咎由自取。如果他们当官时能够施行仁政,爱民亲民,能不受百姓能亲近、爱戴?可见,“出尔反尔”的原意是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你。
有的成语,变着变着,到最后面目全非。例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望文生义是:城门起火了,众人纷纷去池塘里取水灭火。火太大,水不够,结果池塘干了,鱼渴死了。这样解读,也合情合理。而翻开汉代应劭写的《风俗通》,“辨惑”一章里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城门失火,祸及池鱼。俗说司门尉姓池名鱼,城门火,救之,烧死,故云然耳。”知道了吧,池鱼不是池塘里的鱼,而是个坚守岗位的守门员,因公殉职,烈士一个。
编辑 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