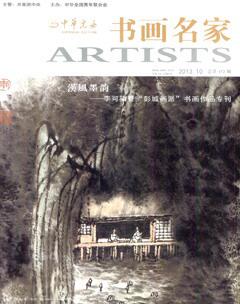地缘文化坐标中的“彭城画坛”
彭城,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徽记;它既是徐州人的栖息地,更是徐州人的精神家园。
正如历史上徐州的版图不断变动着,徐州地域文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它更像一个宽泛的“文化场”,塑造着徐州美术家的个性,影响着徐州美术的面貌。从古至今,徐州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美术家。在现当代时期,徐州地区更是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美术家,其创作成果之丰硕、影响之深远,已得到举世公认。然而,学界迄今对徐州的美术现象、对徐州美术家群体,都缺乏深入、系统的思考和研究。
笔者用“彭城画坛”这个概念来称呼徐州美术界。在本文,它包括绘画,也包括书法;它包括创作实践,也包括相关的学术研究。为了阐述现象,分析因果关系,笔者把“彭城画坛”放在地缘文化坐标中进行审视。一己之见,未必中肯,愿求方家指正。
地缘环境与“彭城画坛”
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地域文化更是与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认为,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结构对一个地区造型艺术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这一理论属于“环境决定论”范畴,它的基本观念源自古希腊,之后,经过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德国地理学家的发展,其理论结构逐渐完善,对学界产生了长远影响。丹纳的理论尽管带有一些局限性,但其合理性也不容忽视。以之考察徐州书画现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徐州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主要以稼穑为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地理环境和农耕生活方式,决定了徐州人性情平和,淳朴坚韧。唐代诗人白居易有《朱陈村》一诗,诗的上半段写道:“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诗句客观反映了唐代徐州的乡村景象,也表达了诗人对与世无争生活方式的憧憬。宋代文学家苏轼知徐州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五首《浣溪沙》,也极为生动地描绘出徐州郊外的田园风情,令人神往。
可是徐州并非世外桃源。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宁静的田园生活屡屡被四起的烽烟所侵扰,历史上黄河的数次改道也对徐州地区的民生造成了负面影响。因而,“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样的豪放派艺术情怀与古彭城的文化性格更吻合。近现代以来,战乱的频仍,政权的更迭,民生的艰辛,也很难让徐州产生“精致”“优雅”或“恬淡”的艺术。
但徐州艺术的豪放与激情隐藏在雍容宽厚的心胸之中。徐州与孔孟故里为邻,儒家文以载道、中庸和谐的思想对徐州地区的影响也很大。徐州的书画家们固然反感抱残守缺的做法,但对传统始终持尊重心理;他们勇于创造,但不愿意“剑走偏锋”,更不习惯于惊世骇俗和标新立异。因而,历史上徐州既鲜见“国粹派”的艺术家,也未出现像八大、徐渭、石鲁那样“反叛式”的艺术怪才。
观察的视野还可放得更宽广一些。徐州地处祖国东部,因此它的文化气质与西北、华北大不相同。向南,它遥接温润秀丽的江南;向西,连接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腹地乃至更远的西北;向北,它呼应大气厚重的北京。徐州有广袤的平原,也不乏绵延的群山,但那只能算是平缓的丘陵。徐州城三面环山,但山丘挡不住人们向外眺望的视野。作为古今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州是人们南来北往、东行西走的大驿站。徐州离北京或上海、杭州的距离不远也不近,以甘柔为代表的吴文化、以温厚尚礼为代表的鲁文化在此交汇,来自南北的绘画思想以及外来的文艺思潮都能波及此地,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眼界,便于艺术家们博采众长,这里的文化因此显得多彩与大气。
徐州的文化特质,无疑得益于地缘优势条件。考量几位徐州籍绘画大家的画风,我们不难发现其从未滑向阴柔和阳刚的两极,而是兼有“北雄南秀”之妙。比如李可染的山水画,在内敛而沉郁的墨色中透出空灵之意趣;王肇民的水彩画,既质朴凝重又华美雅丽;喻继高的工笔花鸟画,形象繁盛充盈,有柔美的一面,更以骨力见长……这种刚柔相济、以柔蕴刚,既不柔弱萎靡也不咄咄逼人的风格特征,与徐州的地理环境相一致。不夸张地说,徐州文艺的特质堪称“取北方之雄而弃其粗鄙,得南国之秀而弃其萎靡”。
徐州书画艺术的发展,也受制于地缘劣势因素。
徐州固然被视做淮海地区的中心,但换个角度看,它却是苏鲁豫皖四省的边缘交汇地带。近现代以来,在南北各大城市中各类文化思潮此起彼伏,但波及徐州后往往势头放缓,波澜不惊。此外,在相当长时间里,徐州缺乏像扬州、南京、苏州那样的吸引力,许多青年人在前往京沪杭等地习艺之后,往往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或留在大城市发展,或远离故土漂洋过海到欧洲发展。
地缘的不利因素使“彭城画坛”在“南望”与“北顾”中游移不定,因此,“彭城画坛”的一般风格始终表现为一种大致的精神倾向而非固定的题材或近似的技法套路,它客观存在,也能让人蒙蒙眬眬地感觉到,但对此又难以进行具体的描述,可以说是“草色遥看近却无”。
“彭城画坛”的传统与徐州地域文化的涵育力
书画艺术十分看重传承。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早在20世纪初,徐州地区就出现了几个较为成熟的文化社团。其中,李可染的启蒙老师钱食芝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发起组办“集益书画社”,文人画士在一起坐而论道,切磋画艺。此类社团,虽为旧式文人雅集活动之余绪,但在传递薪火、启蒙后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不可没。朱德群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但热爱书画,不仅收藏字画,而且在行医之余研墨挥毫,寄托雅兴。由这些史实可以推测,徐州地区的书画文化土壤是肥沃的。
明清以来,书画艺术往往特指文人书画范畴。但倘若把“彭城画坛”的传统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画”传统,那就过于狭隘了,因为我们不能对徐州深沉博大的汉文化遗产、热烈质朴的民间美术视而不见。艺术有门类之别,也有古今之分,但所有的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汉画像石中的形象沉雄粗犷、手法概括而夸张,是对写意精神的另外一种阐述,而白居易、苏轼等历代骚人墨客吟咏徐州的诗词,也堪称“有声画”,让人陶醉。近现代以来,国内各大文化中心城市传及此地的文艺思潮也增加了“彭城画坛”的内涵。千百年来,文人的雅文化与市民文化、乡土文化共同发展,筑就了“彭城画坛”深厚的底蕴。
如果说徐州的文化传统是丰厚的,那么,近现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徐州书画赖以成长的社会条件则远远谈不上优越。连年的兵燹对徐州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徐州不像江南的苏州、杭州那样文人荟萃,也不像北京那样具备吸引文化名流的优势,也不具备上海等城市能得到西方文艺风气之先的优势。李可染曾感慨自己少年时期入私塾而“陋巷无良师,三年无所得”。邹佩珠用一个“难”字来概述李可染青年时代的学艺经历,也是有感于他早年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美术教育。同李可染一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州的艺术学子主要凭着吃苦耐劳、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顽强精神不断打拼,方在艺坛赢得一席之地,而通常意义上的灵气与才气起到的作用还是次要的。
地域文化与地理环境乃至行政区划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与风俗民情、民间信仰、文化积淀关系密切。徐州历史悠久,民间文艺土壤格外深厚而肥沃。这里有拙朴而生动的剪纸艺术和泥塑玩具,艺人如泣如诉的胡琴声,柳琴戏或粗犷奔放或婉转悠扬的唱腔……而且由于地处四省交界处,徐州容易吸收苏鲁豫皖的民间文化优势。这些,都为书画艺术提供了另外一种营养。坚韧而顽强的“草根艺术”对现代艺术书画艺术的影响,看似不起眼,但它起的作用是持久而深入的。现当代徐州素少有孤芳自赏、消极避世的作品,更没有把酸腐当做高雅的做法;徐州的艺术家们固然会遇到种种不如意,但绝不纯然地表现悲苦,更不像封建社会里途穷的文人那样一味地宣泄孤愤。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其实反映了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对于徐州的书画家而言,无论纸上的作品还是实际生活,都是活泼而充满生机的。这种积极的创作心态和达观的心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徐州民间文化的滋养。
徐州的地域文化,为“彭城画坛”的孕育、萌芽与生长提供了土壤;反过来,“彭城画坛”也是徐州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丰富了徐州文化。
特定的文化土壤涵育出特定的艺术家群体。总体来看,徐州艺术家生性和谐平稳,他们根植一方沃土,但思想不封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批青年画家力图探索前卫道路,但他们对于艺术趣味和幻想,对于现代形式感的追求,都是有节制的。即便他们在创作中有时会采取一些现代的形式语汇,但绝不会走极端。这是一种创作心态上的“中庸之道”,落实在画面上,则显得质朴而雄健、灵秀而沉郁,精神容量宽宏,这就是“彭城画坛”的基本特色。
彪炳史册的八位徐州籍艺术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深陷外有侵略、内有压迫的双重危机。面对社会现实,“为大众而艺术”的思想应运而生。正是在这种带有明确革命精神的艺术观的感召下,徐州相继走出了一批杰出的书画家、雕塑家和艺术史论学者,其中包括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刘开渠、李可染、朱德群、王肇民、朱丹。这八人际遇不同,探索领域各异,但皆有大成,对现当代美术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伯英跨越晚清与民国两个时代,但总体上他属于旧式文人,他以“纳帖入碑”的作法留名书史。晚清至民国时期,在康有为等人倡导下,“尊碑抑帖”的观念强烈地冲击着书坛,成为时尚。张伯英的可贵之处在于不盲从时风,他敏锐地意识到“尊碑抑帖”有矫枉过正的危险,于是同时探究“碑”与“帖”的优长与不足,成功地做到了“碑帖兼融”,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艺术创作主要是个人行为,但书画家的命运与家国、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这一点,在王子云、刘开渠、李可染、王肇民、朱丹五位艺术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1930年王子云以西湖艺术学院驻欧洲代表名义留学法国。他既是雕塑家、画家,也是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在群雄逐鹿、“丛林法则”盛行的民国时期,他屡遭劫难而对艺术痴心不改。他对祖国美术遗产的热忱,对学术事业的专注,都让人感佩。他的专著《中国雕塑艺术史》填补了我国雕塑史研究的空白,成为雕塑史研究领域的一块基石。
刘开渠1929年考入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在风格上他选择了古典主义学院派雕塑。他的雕塑造型严整而简练,理性特色浓郁。他主持的大型人物群雕情节完整,具有史诗性的宏大气势。他关注人生,自觉地服务于社会,将中国传统雕塑语言融入西方古典雕塑手法中,对新中国的城市雕塑事业贡献巨大。
王肇民在素描、版画等诸多领域都有不凡的建树。在战争年代,他以笔为枪,积极宣传进步思想。他的水彩画在晚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尤为学界所推崇。迟轲认为王肇民“善于把透明流动的色彩与坚实厚重的色彩结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色彩的力度”;“有选择地汲取了现代艺术在色彩和构成方面的某些经验,故他的画可成为东方和西方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出色成果之一。他的水彩画是具象美与抽象美高度统一,把西方艺术的色彩美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笔法美融为一体。”(迟轲《<光华璀璨,博大精深——王肇民水彩画集>序》)王肇民走出了象牙塔,但他心底始终追求艺术创作的纯粹性,从未把艺术创作庸俗化。
李可染的艺术,很早就显示出革新的秉性。尽管他最钟情于国画创作,但在全民抗战的潮流下,他创作了大批宣传画。和平时期,他才得以全身心投入山水画创作,推动了山水画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他的创作理念是“为祖国河山立传”,但故乡徐州为他的创作打上了或深或浅的印记。
朱丹是一位集画家、理论家、学者、美术教育家、美术活动组织者于一身的人物,中国的“红色美术”历程与他有着紧密的联系。朱丹于1935年考入南开大学,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入党,此后一直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抗战时期,他在西安主办《战地新闻》,后来任延安市美术工作者协会负责人。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东北画报》副社长、社长,创作了大量漫画、宣传画。新中国几乎所有重要艺术机构包括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画研究院(国家画院的前身)的筹建,都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他在绘画创作、诗歌创作、艺术理论研究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但组织美术活动、开展美术书刊出版等事务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致使他的个性风格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如同文艺界许多名流一样,他在政治运动中身不由己,几度浮沉,但对艺术的热爱始终不渝。数十年前他植下的艺术之树已经蓊郁成林,今天的许多名家栖身其中,受益颇多;他当年辅导的学生早已成长为美术界骨干,在学术研究、书画创作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青芳在中国画、篆刻、木刻等许多领域都有涉猎而且皆有过人之处,但由于过早辞世,他的个人风格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一大遗憾。
朱德群青年之后远离故土并最终成名于法国。他晚年的画作近乎抽象,具体的形象不再重要,色彩与图形只是他审美创造所赖以呈现的媒介。他的画境恍兮惚兮,渺幻如梦,似乎蕴含着故土的情韵。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这样评价朱德群:“他的艺术充满着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力和自我表达心灵的激情。”“他将东方文化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绘画的形式语言与西方抽象绘画的优长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东方艺术精神和内涵的抽象风格,反映出一种超越时空和跨文化边界的创造。”但他在精神上一直与祖国的文化息息相通。
目前,学界对八位艺术家的研究,只有关于李可染的研究较成规模,对于刘开渠的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而对于其他几位的研究,资料的搜集等基础工作至今尚未准备好。八位艺术家与世纪同行,他们的记忆中曾留存着珍贵的史料,从他们跌宕起伏的经历中无疑可以管窥百年激荡的社会风云。而如今,除了朱德群外,其他七位艺术家都已陆续辞世,因此许多珍贵的史料也就无可挽回地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令人扼腕。
与他们同时期,徐州走出去的艺术家还有萧龙士、王琴舫、朱竹筠、王仲博、钱书樵、张金石、王寄舟、刘梦笔、王明泉、李畹、马南圃、杨墨泉等。他们先后走出徐州到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武汉等地的艺术学校求学,开阔了视野;他们对西方艺术体系特征有了直接的认识,学成后再返回家乡,以教育传播新知,播下美育的种子。这些画家长期专注于耕耘而不求闻达,培养了许多艺术人才,虽然他们的影响不及一些在外地发展的徐州籍艺术名家,但他们对徐州地域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更直接也更加重要。
萧龙士沿传统道路而行,他把徐州民间绘画趣味融入文人画的格调中,雅俗共赏。他笔下的兰草、荷花,注重大对比,形象简洁而墨色温润。他另一贡献是影响、培养了一大批写意花鸟画家,丰富了徐州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活动。
王寄舟于1938年参加“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1942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木刻研究会”,新中国成立后生活于徐州,曾任徐州四中美术教师。他的木刻,尺幅通常不大,但贴近生活,远离了小情小调,画面质朴感人。他早年的代表作《雪地行军》追求奏刀裂木之美,但畅快的笔法下隐藏着沉重感。他以徐州农村生产劳动为题材的木刻,乡土文化气息浓郁。
走出地缘范畴的后继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创建,也意味着民国时期的文化生态的终结。就徐州文化而言,还没有一所专门的艺术创作机构,书画家大多集中在徐州各中学做教员。在没有高等美术教育机构的情况下,喻继高、张立辰、郭公达、马世晓、陈开民、王为政等都是在当地中学美术老师培养下,通过考学校或工作调动走出了家乡。延至到上世纪80年代,徐州地区走出的画家还有赵绪成、江文湛、程大利、朱振庚、贺成、马波生、徐培辰、周京新等,他们先后定居北京、南京、合肥、西安、杭州、武汉、深圳等文化中心城市,并逐渐成长为艺术名家。
张立辰的大写意花鸟画,造型干净利索无冗笔,墨色饱满而酣畅。在布局上,他以大的气势取胜;在韵味上,他在浙派的秀雅中融入北方的雄强之气。郭公达的山水画,注重走笔的书写性以及水墨效果的氤氲感,画境在简约中见丰实。马世晓的草书,笔画连贯却不给人枝节缠绕之感,有骨力,也有神采,秀逸多姿,为书坛所重。
贺成以水墨人物画著称,他描绘古今人物都游刃有余。他笔下的唐代仕女,风姿绰约,雍容华贵;他描绘当代人物,结构准确,变形合理,动态生动。程大利先后在江苏美术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推动了艺术思潮的传播和创作成果的推广。在个人创作方面,他坚持借古开今的理念,在山水画领域孜孜以求。
朱振庚和周京新虽然从年龄上属于两代人,但都强烈追求绘画的时代感。朱振庚主攻人物画,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既遥接贯休等人的造型传统,也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语言。他晚年的作品中流露出神秘莫测的情调,令人观后难忘;周京新受欧洲表现主义画风影响颇大,但墨的韵味与走笔的书写性却源于中国画传统,他近期的水墨花鸟、人物、风景皆别开生面,在当代画坛独树一帜。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10余年间,徐州油画在方冰山、虞建、李建国、陈少立、李广才、魏鲁宁等人的影响和带领下,一方面,他们坚持从欧洲写实油画的传统与当代西方写实油画大师语言中直接获取创作技艺与语言;另一方面,他们深入生活,注重对当代人物日常生活的捕捉,创作出了一批真实而朴素的反映了那个年代的生活画卷。徐州的油画创作一度在江苏省内影响很大。另外,水彩、水粉和版画在陈健升、孙田成、王九诗等人的带动下也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在艺术上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油画中坚力量大部分调出徐州,方冰山、虞建、李建国、陈少立调往南京,李广才去了北京,徐州地区油画创作的势头由此减缓。地缘的不利因素似乎再次发挥了作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还有几位徐州籍艺术家、学者从家乡走出到外地求学,毕业后也成为了一些重要艺术机构的中坚力量。他们是:陈传席、李建国、王其钧、翁剑青、秦俭、高天民、尚辉、朱虹子、徐沛君、崔伟等。
文艺幼苗在徐州萌生,却在外地成长为大树。这是徐州的荣幸,也是徐州的遗憾。
立足本土的画家群
20世纪80年代初,徐州的美术开始走上繁荣发展的快车道,各种美术团体、艺术教育机构都在创建或恢复中,徐州文联下属的美术工作者协会得以建立,吴俊友、王冰石、李建国主持美术工作。1985年,文联所属协会完成换届工作,姜舟任徐州市美协主席,王冰石任徐州市书协主席。
徐州国画院在张之仁、贺成的筹备下于1980年成立,乔俊生、姜舟、马奉信、欧阳龙、杨正伟、周长海、王其钧、马波生、张剑华、刘山民、王广明、曹乘龙都是建院后最早调入画院的一批画家(画院在成立初期还聘任吴俊友、李怀林、朱天杰、王志铭、黄秉乙为兼职画家)。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作为一个专业艺术群体的集中体现,在文化上强调继承性与连贯性,“传统”对他们而言不带有“保守”的含义,而仅是一种状态的表述。他们注重于对传统营养的吸收,如何从厚重的文化氛围中冲突出来,也是这些画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实践证明,在以后的10余年间,他们利用自己的传统笔墨功底,在山水、人物、花鸟等不同的艺术领域里创作出来一批大气厚重、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徐州美术的发展正是与这些画家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表现分不开的。
如果说上一代画家的奋斗是时代环境的激发,那么以后调入画院的50后、60后、70后,甚至80后的画家则是在西方现代文化参照系的观照下,对传统绘画具有反思精神的一代人。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绘画本体的回归和开拓成为高洪啸、孙茂祥、吴江、刘宏、周林平等以及后来考入画院的赵方方、梁雨、张平静三位年轻画家面临的课题。在国画语言的探索上,他们更注重从传统艺术资源中挖掘出新的可能,将之与当代视觉经验进行结合与转化,在创作心态上更注重表达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在表现手段上强调视觉张力,注重现代审美图式效果。目前画院的10多位画家,以鲜明的个性和饱满的创作激情,开展创作,加强与外界交流,推动了徐州美术多样性格局的发展。可以说,30多年来徐州画院在张之仁、欧阳龙、马奉信、高洪啸四任院长的领导下,在不同时间段内为徐州美术的繁荣做了大量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秩序的调整,美术与社会的联结机制在多层面上显现出可能性,徐州地区的美术创作以及高等美术教育机构不断地增加与完善。1992年,徐州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前身)正式成立美术系,姜舟调任系主任。作为一位受过传统书画思想浸润的花鸟画家,姜舟没有让西式美术教学模式全面覆盖师大美术系的教学体系,而是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系统接受传统书画的熏陶。师大国画专业还有杨振廷、惠剑等知名教授,他们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在创作实践方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驻徐部队系统的画家杨进民创作了许多形式新颖、语言独特,以西部山水为主题的作品,在全国性的美展中多次获奖,为徐州画界赢得了荣誉。
此间,新建的李可染艺术馆作为徐州对外文化的交流窗口,通过让广大的观众对李可染作品的“视觉阅读”,在美的巡礼中感受到艺术大师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徐州报业集团借助媒体资源,以徐州艺术馆为平台,面向社会实施审美教育,实现文化的启蒙意义,促进了美术的发展。由此,徐州艺术创作呈现出多元共生的良好格局。
朱天杰长期致力于艺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修养全面,视野开阔。作为徐州报业集团资深媒体人,他利用媒体优势,积极宣传当代徐州书画的创作成就,不断介绍新人新作。2004年,他当选为徐州市美协主席,在团结美术工作者和组织美术活动方面付出了许多心血。朱天杰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关系,近10年来,他多次邀请国内外学者、艺术家、文化名人来徐州讲学,开阔了徐州美术工作者的视野。同时,他在山水画的创作上努力把握和强化自己的艺术气质和绘画风格,在形式上不断进行新的尝试而被学术界关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给了徐州本土的青年艺术家以极大的创作自由,在“新潮美术”的影响下,本地的前卫艺术一度活跃。不过,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徐州的前卫艺术数年之后归于沉寂,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省略号。
呼唤“彭城画派”
按照通常的标准,文艺流派通常是自然形成而且能在历史上产生长久影响的艺术创作群体。但凡称“派”者,都有相对固定的成员,他们有着共同或相近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往往以结社的形式维持彼此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位或几位领军人物。以上述标准来看,徐州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域画派。
但“彭城画派”的出现是有可能的。先贤们志存高远,大胆地追求时代气象,自觉地把传统笔墨语言与汉文化精神相结合,在审美取向上有着一定的共同性或共通性,已经为当代徐州地方画派的萌生做了铺垫;而随着徐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文艺赖以发展的物质条件也优于以往任何时候。徐州地区的书画家队伍空前壮大而且大多有聚成“画派”的主观愿望,“彭城画派”呼之欲出。
推出“彭城画派”,也是时代的客观要求。目前,随着交通运输、资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快,地域文化趋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此种环境下,珍视本土的文艺传统,深挖地方文化资源,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已然成为学界的自觉呼声。就江苏省的文化发展格局来看,“南重北轻”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扶持“彭城画派”,有助于优化美术格局。对徐州而言,果敢地打出“彭城画派”的旗帜,适时推出一批优秀艺术家,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或许“彭城画派”的提法以及“培育”画派的做法会招致批评,但主动发出声音总比一味沉默要好。
“彭城画派”的培育与扶持,无疑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当前,许多地方都在积极培育自己的画派,且屡屡遭到诟病。“彭城画派”很容易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我们真诚的声音也容易被外界误解成炒作的噱头。新的社会环境也对徐州画家的脱颖而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0年前,书画家一旦有作品获得国家级大奖,往往就意味着迎来坦途;而如今,评奖活动的过多过滥已经大大损害了奖项的严肃性,而大量的商业操作行为也让一些本来颇有潜力的艺术人才放弃了理想。
以笔者浅见,在浮躁成为社会通病的情况下,构建徐州地方画派,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挖井”——从徐州的历史与当代生活寻找题材,探索与之适应的形式语言,有倾向性地开展创作。艺术美并非俯拾皆是,美术创作需要作者具备感受美的心灵,拥有一双慧眼以及独到的表现手段。徐州地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矿藏资源”,画家们可以咏怀历史,也可以抒发情感。尤为重要的是,要创作一批反映徐州城乡现实生活的优秀画作,要借新的笔墨语言来呈现新时期的徐州文化精神,表现本地的风土人情,让个人体悟与地域文化产生共鸣,让心象与纸面上的图画形迹共振。
其次是加强徐州画家的凝聚力。可以定期举办论坛、展览,使之成为徐州艺术家们展示才华的平台与交流的园地。在坚持严肃学术性的基础上,适当地将艺术作品推向市场,使市场与学术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要特别重视理论研究,“彭城画派”的学术品格固然要通过创作实践来彰显,更要借助系统的理论研究加以总结。
再次是推出代表人物。徐州不乏优秀的艺术家,但缺少的是对人才的发现以及宣传。“彭城画坛”首先需要推出自己的领袖人物,没有这样一位旗手,“彭城画派”不能长久地产生影响。这样的领军人物,最好从依然活跃在徐州地区的艺术家中培育出来。
另外,要创造条件,密切艺术家与徐州的关系。“彭城画派”与徐州应该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就如同新安画派与古徽州、巴比松画派与巴比松村的关系;“彭城画派”旗手与徐州也应该具有不可剥离的关系,就如同莫言与高密乡、波德莱尔和巴黎、博尔赫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要求“彭城画派”的艺术家始终固守在徐州一地,但他在精神上要与徐州维系着恒久的关系,至少要做到“风筝不断线”。
笔者相信,如果上述几点都能做得到位,“彭城画派”这朵地域美术奇葩不仅会绽放,而且可以对当代中国美术发展格局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中国美术馆》杂志执行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