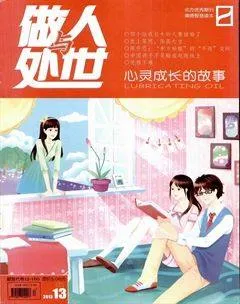我与杨振宁先生的一次见面
我有幸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两次拜会杨振宁先生。能与我仰慕多年的科学偶像有两个多小时的亲密接触,这是我一生最珍贵的美妙回忆。
2012年11月13日,这是一个值得我永远铭记心头的日子。那一天上午11点,我坐到了杨振宁先生的身旁。当我第一眼见到这位耋耄之年的长者时,丝毫没有察觉到90年的时光从他身上划过的痕迹。初次见面令我的内心有如被阿拉丁神灯梦幻般点亮的感觉。
杨先生先首先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在哪儿念书,学校在哪个位置,我一一作答。从这些对话中我感觉到,杨先生不仅思维清晰敏捷,而且对如我这样的反应迟钝者还很体贴照顾。杨先生接着跟我聊起了关于风格(style)的问题,这是我们见面的起因。我曾经从《杨振宁文集》里读到下面一段话:“在创造性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里,一个人的品位,加上他的能力、气质和际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品位和风格又进一步决定了他的贡献。乍听起来,一个人的品位和风格竟然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如此关系密切,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一般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质世界有它的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某些特点的憎恶,正是他形成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品位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这段话引发我的兴趣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文学领域内的不同风格的论述随处可见,科学家之间也有不同的风格,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杨振宁先生在接下来的话里进一步提到他在西南联大里最重要的一个体会就是,他开始懂得了欣赏他的三位偶像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的不同风格。
他说比较欣赏薛定谔的风格,而海森堡的风格则不能引起他的共鸣。看到这句话我又释然了:之所以很多数学书我看不下去,原来是因为作者的风格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啊!
杨先生说,在他所知的所有理论物理学家中,他与Dyson风格其实很不一样。例如,从写文章来看,Dyson能够写出很长的文章,而他的文章一般都很短,因为用每一个字都要想很久才肯动笔。当时我立即想到,杨先生这种惜墨如金的写作风格是不是受了高斯“少而精”的原则的影响。高斯写文章的风格可以用一句古话来形容:“良工不示人以朴。”就是说,最后呈现给读者的一定是最精简最完美的成品。
杨先生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能对关于风格与兴趣的比较这类问题感兴趣是很可喜的。他还提到,其实在数学家的风格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华罗庚先生与陈省身先生就很不相同,不论是在做人、兴趣,还是能力方面,两人都截然不同。
于是,我问杨先生能不能给出这样的几次研究经历来。他讲了四次这样的经历,包括1951年发现单位圆定理的证明,1954年与Mills合作完成的规范场论方面的奠基性工作,1975年与吴大峻提出不可积相因子与规范场论的整体表述的工作,以及当他了解到陈省身先生在几何拓扑方面的示性类工作时,他都有这种美妙的感觉,他先后用到了“不可思议”“妙不可言”“奇妙无比”“很震撼”的说法。杨先生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他1951年证明单位圆定理的情形,他说:“我清楚地记得12月份的某个晚上,之前尝试的各种想法纷至沓来,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清晰的思路,谜底解开了。”
他突然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当时我要考虑多项式的根吗?”“不知道。”他又问:“你没有看过我最近在复旦大学给物理系教师作的一个报告?”“没有。”他立即让许晨秘书给打印一篇文章,并解释说,他在那次报告中提到,他之所以想到要考虑多项式的根,是因为从小他父亲就告诉他一个基本定理——这个好像叫作代数基本定理,这个定理说每一个多项式都可以唯一分解为一次因子的乘积。他从小就知道了这个定理的美妙,于是只要一看到多项式就自然想到它的根。
在谈到他与吴大峻1975年合作的文章时,他抑制不住兴奋跟我讲起他最近的一项新发现。他拿给我一份预印本,介绍说这篇文章是最近写的,还没有来得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分析出来这样一个结论。他最后把这篇预印本也送给了我,并给了我一份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并说:“很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是先有了中文版再译成英文的。”也许在他而言,回国定居之后用中文写作也是一个返璞归真的勇敢尝试吧。
我接下来从《数学大师》里选取了哈密尔顿(Hamilton)来同杨先生探讨,因为杨先生曾在他的科学论文选集中为哈密尔顿鸣过不平。说起哈密尔顿的四元数,杨先生跟我讲了泰特(P.G.Tait)与麦克斯韦(Maxwell)的故事。
当我正准备聊第三个数学家时,许晨秘书提醒杨先生时间不早了。于是,杨先生说:“看来你的问题还很多,一时也聊不完,不然我们用E-mail联系或者方便的时候再见一次吧。”但我最后还是忍不住再问了他几个学术问题。因为与他的工作紧密相关,他问我是不是可以将那些材料给他,他说有空会看一下。给了杨先生资料,我便起身告别,大约是12点15分。
记得当我们结束谈话时,许晨秘书来说:“刚才某校长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等不到就先走了,说下次再来。”我感觉自己像尊贵的客人一样得到了先生的礼遇。
杨先生给我的感觉可以用“春风大雅能容物”来形容。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对人的真诚,特别是对年轻人的提携与鼓励的不遗余力,对大自然之微妙的欣赏与赞叹,对历史演变的宏观把握。而这其中,杨先生的真诚是最特别的,同时也是每个人都值得学习的。
见面时,我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激动,不过其间仍免不了失控。当我骑车回来时,我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经过北大时我突然想起,杯子好像落在杨先生办公室的茶几上了,看来我得下次再去一趟,希望能再与先生见一面。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