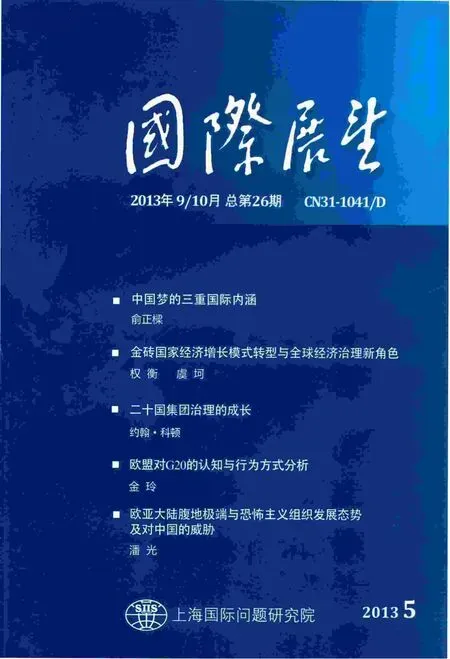二十国集团治理的成长——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使然
约翰·科顿
1999年12月15—16日,世界上19个最具体系重要性的国家及欧盟的财长和央行行长聚会德国柏林,举行二十国集团(G20)首次会议,①John J. 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Farnham: Ashgate, 2013.以执行七国集团(G7)财长和八国集团(G8)领导人该年年初的决定。该倡议最初由G7中最小的国家加拿大的财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和最大的国家美国的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他们两位及其G20的同事当初提出此倡议又是出于对1997年6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应。该危机随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1997年末迅速蔓延至印尼和韩国,并于1998年秋席卷俄罗斯、巴西和美国。后者以其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为标志。这一连串的危机表明既有G7/8及更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无力为一个新的全球化金融时代提供金融稳定;同时,需要建立一个既包括既有强国又包括新兴经济体的更广泛和更长期的集团来提供这一全球公共产品。
十年后的2008年11月14—15日,世界上同样最具体系重要性的国家以及欧盟的领导人聚会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首次G20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这次新的论坛并未获得G7/8授权。但是,同1975年G7峰会的问世如出一辙,两次峰会都是由法国和美国所倡议。一如1975年,美国这次也坚持超越既有排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俱乐部,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国家集团来应对当下的复合型危机。美国总统小布什决定,这次峰会由所有G20成员参加并由美国做东。所有G20成员国领导人欣然接受邀请。这些国家即将应对一场由美国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破坏性超过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本次危机起因于“美国大街”(main street,即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并迅速扩散到一个业已全球化的世界的所有方面。这表明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峰会级别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心,以此通过金融管制、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和发展等来提供金融稳定。这一任务其实也构成了 G7/8自成立以来的核心议程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第一次G20峰会确定了原则性方向、执行程序及95项具体决定,包括很快举行下一次峰会。英国首相布朗于2009年4月1—2日在伦敦主持召开第二次峰会,出台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9月24—25日在匹兹堡主持召开第三次峰会,宣布G20将从此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的首要平台。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于2010年6月26—27日主持召开第四次峰会。本次峰会获得了一项来之不易的协议:中期内退出过度的财政刺激计划。
韩国总统李明博于2010年11月11—12日主持召开第五次峰会,此举见证了东道国从G8国家转向新兴的非G8但仍然是民主国家之一的亚太国家。第六次峰会加强了这种平衡趋势:2011年11月3—4日戛纳峰会由法国总统萨科齐主持召开;第七次峰会于2012年6月18—19日在洛斯卡沃斯由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主持召开。第八次峰会预计在2013年9月5—6日在圣彼得堡由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2010年初爆发的欧洲金融危机——由希腊恶性主权债务危机引发并可能威胁到欧洲以外的世界而成为13年来的第三次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警示了这一常设G20峰会治理的必要性。
因此,G20提供了一个应对全球金融震荡的终极有效的方式:1997—1999年和2008—2009年的两次应对是反应性的,而后2010—2013年的反应是预防性的。因为,自2003年起,G20超越原有的G7/8或者后来的G8+5集团(G8加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南非)扩大成为一个其成员国更广泛、更全球化、更强大、更平等的来自发达世界和新兴世界的国家集团。它改变了成员国的标准。这标准过去是来自基于实力的单纯强国,而现在是来自既基于实力又基于联系性的和体系重要性的国家。它的作用和议程已经迅速扩大:从一个应对危机的委员会转变为一个预防危机和指导金融与经济、社会政策及如恐怖主义等政治安全问题的委员会。同时,既不同于排斥日本的联合国安理会,也不同于排斥中国的G8,G20接纳了这两个亚洲国家——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大国——以及冉冉上升的韩国、印尼和澳大利亚,将其作为居于全球中心的全球治理集团的平等成员。
一、对G20治理的评估众说纷纭
如何判断G20治理的道路、宗旨和成效已成为激烈争论的论题并形成五大流派。最初,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于G20和G8这一对新老机制的关系。
第一种流派可称作“多余论”,认为从长远来看G20是多余的,不是因为它成员国太庞杂以及机制上太不正式,就是因为它等于促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和G8重振旗鼓并收复失地。①Ibid., pp. 5-6.该流派指出,G20只是对1997—1999年金融危机的机制性反应,并不能预测和防止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且有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缺席了第四次峰会,峰会会期也从一年两次减为一年一次。同时,一年一次的G8峰会也开始吸收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并自2010年起将金融和经济作为其议程的一部分,毕竟在2013年6月17—18日由英国主办的厄恩湖峰会上是如此。随着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IMF和金融行动专责委员会现已担当具体的金融和经济改革工作,一个多余的G20峰会即将淡出首要论坛功能。
第二个流派可称作“拒绝论”,拒绝承认G20声称自己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中心。②Ibid., pp. 6-8.有法律程序偏见的人从一开始就预言金融G20注定失败。他们的论据是:超级大国的存在、那些老牌法定多边机制的极佳表现、G20身上存在的可怕的机制性缺陷和老的G7在新的G20中的主导地位。因此,他们指出G20峰会缺乏合法性。它只是一个小型的、毛遂自荐的机构,没有清晰的成员国资格标准、没有治理章程、没有其他任何方面或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授权,而且对G8成员没有多少好处。
第三种流派可称作“强化论”,认为G20强化了G8和类似集团。③Ibid., pp. 8-10; Andrew F. Cooper, “Working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G20, BRICS and the United Nations,”in John J. Kirton and Madeline Koch eds., The UK Summit: The G8 at Lough Erne 2013, London: Newsdesk, 2013; Andrew F. Cooper and Ramesh Thakur, Group of Twenty(G20), London: Routledge, 2013; Susanna Vogt, “A Progressive Idea of Style Awaiting Its Embodiment: Global Governance between G8 and G20,” International Reports, No. 2010.其论据是G20在其两大任务——提供金融稳定和使全球化造福全人类,干得非常出色。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增加了新兴国家的参与——这正是G8所欠缺的——从而兑现了它逐渐发展为一个危机预防框架机制的承诺。许多早期“加强论”者主张增设一个领导人级别的“G20领导人峰会(L20)”。他们因而极力推崇G20峰会的上好表现:从危机治理委员会转化为指导委员会,同G8的合作及其正逐渐扩大的效能,特别是如果能作一系列改革的话。
第四个流派提出“替代论”。④Ibid., pp. 1-12.该观点认为G20部长级会议以及G20领导人峰会可以代替已经、即将或者应该淡出的 G7/8;振兴一个业已僵化的联合国;甚至实际上代替联合国安理会五常。
第五个流派可称作“衰退论”,也是目前的主流派,认为G20自其峰会开创以来出现衰退。①Ignazio Angeloni, “The Group of 20: Trial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imes of Crisis,”Bruegel Working Paper, No. 12, 2011; Alistair Darling, Back from the Brink: 1000 Days at Number 11,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1; Stephen Pickford, “The G20 and Beyond,”unpublished paper, Chatham House, London, 2013; Rowan Callick, “US, Chinese Leaders Must Pull Off Market-Oriented Magic When They Meet in California,” Australian, 2013,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opinion/columnists/us-chinese-leaders-must-pull-off-market-ori ented-magic-when-they-meet-in-california/story-e6frg9fo-1226658099963.其论据为:G20最初在2008—2009年应对危机时表现不凡,但此后开始衰落。有人指出G20的某些方面衰退,如特别是2010年峰会在关于财政整顿和银行资本的承诺问题上举棋不定,悬而不决。还有人指出G20在宏观经济政策表现上有所衰退,这同它在处理日益棘手的发达国家金融管制问题上表现出的日益成功形成鲜明对照。②Pickford, “The G20 and Beyond”; Masahiro Kawai, “The G20 Leaders' Process Five Years On:An Assessment from an Asian Perspective,” Opening remarks at a conference on "The G20 Leaders' Process Five Years On: An Assessment from an Asian Perspective,"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y, Sydney, http://www.adbi.org/files/speech.2013.05.22.opening.remarks.kawai.g20.leaders.five.years.on.asian.perspective.pdf.
上述这些流派都认为G20存在严重缺陷,尽管系统论述G20的第一批书才刚出版。③Risto E. J. Penttilä, Multilateralism Light: The Rise of Informal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2009; Karoline Postel-Vinay, Le G20, laboratoire d'un monde émergent, Paris: Le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1; 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Peter I. Hajnal, The G8 System and the G20: Evolution, Role, and Documentation, 2nd ed., Aldershot: Ashgate, 2013.他们几乎没有对14年来G20在一系列国际机制功能上的行为作具体、系统和实证的研究。他们几乎对这样一个国际机制如何、为何能出现、其发展和行为的概念和理论一无所知。他们几乎未能提供一个有具体案例和系统考证的、关于G20的发生、演变、表现和前景的分析解释。
本研究试图成为满足上述标准的第一本系统论著,④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认为:G20是作为体系性的峰会枢纽而诞生的,其作用正不断上升,涉及范围日益拓展、要求日益提高、日益涉足国内议程并涵盖此类国际机制的所有应有机制功能。G20的作用日益扩大缘于各种对所有国家来说施加了新的同等脆弱的冲击的加速增长,旧国际机制的应对失败,非G7成员国的日益增加的能力和日益开放的政治,参与方所展示的国内团结及其对在全球治理网络枢纽仍显紧凑的 G20俱乐部的理性支持。
更为具体地,自1999年以来,G20成长既迅速又灵活,以至开始治理原本属于G7/8的广泛议程,包括如恐怖融资、腐败和善治等核心安全问题。尤其是自2008年峰会起,G20已经从起初注重国内政治管理、审议和方向设置转为注重全球治理的决策、落实和发展。这里,全球治理的发展既包括 G20内部,也包括其外部。G20在2008-2009年成功应对危机后,又成功地转向有效地预防危机,防止欧元危机向全球蔓延,同意IMF和世界银行改革,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演变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争,并推动发展、保护环境和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控制腐败。尽管大多数G20成员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G20仍然努力争取使全球化惠及所有国家。
这一过程最早是由一连串的冲击驱动的,最初是1997-2001年期间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内的冲击,后来是2007-2010年的冲击,然后是小一点的、但形式上大同小异的金融冲击——从2010年1月的希腊到2013年的塞浦路斯。促成G20成功的因素还可以包括2001年以来的恐怖主义冲击和2007年以来的能源和环境危机。这些冲击的规模不断上升,迅速向所有国家和部门蔓延,并对现在仍是名义上的主权国家的内部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到2007年这些冲击的发源地也已经变化:从一个新兴的亚洲到曾经的霸权但现在已极度脆弱的美国和欧洲。这些冲击表明全球化已从物质和社会两方面将世界改造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的体系,以复合关联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
面临这些冲击,大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且其脆弱程度不相上下。即使是美国及其大西洋盟友于20世纪40年代构筑的正式的多边组织也无济于事。甚至那些自1975年兴起的更具选择性的由G7/8领导的往往是非正式的多元机构也对此束手无策。而G20则不同于众多的竞争性国际机构。G20成员国都是完整和平等的国家,后者正日益拥有应对冲击所需要的集体主导力和相对均衡的国内能力。而且,这些成员国正日益——尽管不是齐头并进地——成为更加开放的民主政体,其动力来自于外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G8的指导以及G20内部的社会化。G20又进一步得益于成员国的国内政治控制、资本、连续性和竞争力。
总而言之,在其创始人马丁的领导下,先是从1997—2001年然后是从2003—2005年,G20已经成为一个成员数量稳定、参与度有限的俱乐部:这有利于降低老资格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营造学习环境和促进社会化,从而使它们获得地位、认同和新的制度性利益的观念。这种资格只有成为一个高层次的俱乐部的成员国后才能获得,又随着2008年秋天以来交流的增强而增强。此外,G20已成为日益发展的全球交流网络中心。其中,一方面是G20内部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相互结合,另一方面则是G20作为整体同其他相互交织的全球性多元多边机构的相互连接,使G20成为整个世界的核心。
二、G20的问世和衍变
创立G20的愿景始于1988年6月21日的加拿大多伦多。当时在那里,G7领导人提及一个新的、他们称之为“全球化”的现象。他们还提出同新兴亚洲国家进行建设性对话,讨论“宏观经济、货币、结构改革和贸易等问题,从而达到有利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所应进行的国际调整”。他们同时还鼓励将能“推进多边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营造必要的合作”的进程。①G7, “Toronto Economic Summit Economic Declaration,” Toronto, June 1988, http://www.g8.utoronto.ca/summit/1988toronto/communique.html.
9年后的1997年,G7已经打赢冷战并将民主革命带入后苏联世界,还掀起了涉及更多人的全球化。但是当G7领导人相聚丹佛市时,同时又多了一个现已民主化的俄罗斯,他们并没有预见到当时的东道主克林顿后来所称的 21世纪的第一场危机。丹佛峰会几周后,泰国金融体系崩溃,随后于9月和12月先后蔓延至印尼和韩国。然后是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崩溃;9月,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10月,巴西金融崩溃;以及后来几年里土耳其和阿根廷相继金融崩溃。
G7的两位财长,加拿大的马丁和美国的萨默斯,认定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来治理现已紧密相连的世界。新机构的成员将仍然保持绝对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内相对最大的能力。但他们仍然拥有最大的相对联系性,因为他们中只要有一个国家失控,那么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国家也将立即跟着失控。这种新型的“体系性重要”国家已经不再仅仅来自老牌的欧洲—大西洋列强,也来自亚洲、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新兴大国。它们绝大多数都将是民主国家,因为开放政体是有效和合法治理一个经济社会开放、相互关联的世界所不可或缺的。于是,萨默斯和马丁选择了G8中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民主化国家俄罗斯以及全部成员国都是民主国家的且仍在不断扩大的欧盟作为G20成员国。他们还选择了现在称之为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然后又纳入金融危机中的印尼和韩国以及当时表现不错的土耳其和阿根廷,最后是沙特、墨西哥和澳大利亚。此外,为了增加代表性和专业性,他们又增加了 1944年以来世界性的非政府间组织的IMF和世界银行,分别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和使全球化造福所有国家。
G20的第一次会议于1999年由加拿大主办但地点选在柏林,主要讨论金融稳定。①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pp. 55-92.第二次会议于2000年10月在蒙特利尔举行,强调全球化造福所有国家。②Ibid., pp. 93-114.G20因其2001年11月渥太华的第三次会议而成为全球治理中心。此前不久的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分子袭击了事后证明极其脆弱的美国。③Ibid., pp. 115-135.在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楼和华盛顿特区五角大楼的残垣仍在冒烟的背景下,无论是联合国还是IMF和世界银行都不可能正常工作。只有G20可正常运转并举行会议阻止恐怖融资。尽管G20成员国在各方面参差不齐,但依然团结一致共同对付针对全人类的现实威胁。此时,世界上最强大同时也最脆弱的国家美国开始依靠沙特、印尼和土耳其等来了解恐怖主义金融网络的运作及其控制方式。此刻,G20成员国便临时性地结成了这样一条纽带:将G20从一个机制性的俱乐部转变为一个人际交往的俱乐部。
G20变相成了一个真正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国家集团。④Ibid., pp. 137-225.主办国资格相继交给了新兴国家成员国——印度(2002年)、墨西哥(2003年)、中国(2005年)、南非(2007年)和巴西(2008年)。新兴国家还取得了长期追求但被拒绝的、由大西洋国家控制的IMF和世界银行的一份协议:将部分投票权从老牌大国移交给新兴大国。G20的成功推动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从2004年到2005年呼吁将G20会议提升为峰会,用以预防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所肯定会带来的危机。他终于得到了除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外所有G20同事的支持。
当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爆由大西洋向全球扩散的金融危机时,G20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切实的运作经验和举行峰会能力的全球治理中心。①Ibid., pp. 227-268.8天后,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联合国大会建议举行有中国、印度和巴西参加的G8特别峰会以应对金融危机。布什认为应该先举行一次G7峰会以应对金融危机,日本也持同样立场。但很快,在金融崩溃和密集的高层外交下,G20胜出:因为它早已存在,还因为即将离职的布什总统也知道G20是有效的,因为在G20刚创立不久的2001年秋,G20就已经获得成功。因此,同样是这些国家,面临同样的任务,现在又在领导人级别上,于2008年11月14—15日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一如2001年秋,没有任何其他全球性国际机构有能力或有意愿举办峰会来应对迫在眉睫的重大危机。
三、G20峰会治理
第一次峰会于2008年11月14—15日在华盛顿举行并获得圆满成功。②Ibid.第一次有这么多高级领导人汇聚一堂讨论经济和金融问题。③Pickford, “The G20 and Beyond”.他们集中讨论了如何确保金融稳定并采取标本兼治的国内金融管制。他们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例如,必须加强金融管制并且进行国际协调和国际监管。为此,他们已经涉入成员国的主权范围和私人部门:处理信贷违约掉期、场外交易衍生品、信用评级机构、银行家薪酬和会计准则等。他们还谴责了保护主义。他们直面避税天堂问题。领导人制定了一个附有具体截止日期和落实措施的程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在不到24小时内救赎全球经济。他们提出将于四个半月后再举行第二次峰会。
2009年4月1—2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功。④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pp. 269-296; Darling, Back from the Brink.全球经济收缩的速度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谷底时期。在金融冲击迅速蔓延及其破坏性的经济后果的逼迫下,G20的铁杆老兵、英国首相布朗加上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依靠了坦率且不设框框的决定,而且是领导人之间直接做出的决定;这也是奥巴马的首次重要出访。他们鼓励自己的中央银行提供巨额货币和政策刺激计划,一致同意大规模、同步、慷慨的财政刺激计划,并且为遭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筹集了共 1.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IMF 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5000亿美元的新借款安排、2500亿美元的贸易融资以及世界银行的1000亿美元。他们同意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所有G20成员国都是其会员——负责监管所有体系性重要的金融机构并且改革IMF的配额和投票权。他们更强烈地谴责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对避税天堂的行动。他们增加了议题,例如在布朗的英联邦非洲伙伴的敦促下增加了气候变化控制的议题。
6个月后,即2009年9月24—25日,G20领导人在匹兹堡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①Ibid., pp. 297-320.鉴于全球金融危机得到控制,他们改防御为进攻。他们宣布G20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的首要平台,并为此出台了宏观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和“相互评估程序”。他们同意将至少5%的IMF份额由老牌大国让与新兴大国。他们给IMF制定了一个灵活的预留信用额度来加强该机构的金融安全网。他们同意对银行资本制定新的规则、实施金融稳定理事会标准和完成场外交易衍生品改革。②Pickford, “The G20 and Beyond”.他们又进一步拓宽了议题和行动:同意中期内分阶段退出石油补贴,旨在实质性地利好气候变化控制、财政稳定、母婴健康和反腐。奥巴马作为东道主利用峰会向伊朗显示:如果伊朗继续实施核武器计划,那么它将面临更多的制裁。
第四次峰会于9个月后,即2010年6月26—27日在多伦多举行,也取得圆满成功。③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pp. 321-372.希腊爆发的新的金融危机得到控制。开始从财政刺激转向退出战略。鉴于美国不愿意调整,因此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同意削减财政赤字占GDP比率的一半,并且承诺到2016年前停止累积债务占GDP比率的增长。领导人宣布今后三年不得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他们同意给多边发展银行增加3500万美元资本金、取消海地债务、按照规定日期2015年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成立一个发展工作小组以推动新发展方式以及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新的金融安全网络。多伦多峰会开始将市民社会纳入G20治理,为此成立了商业G20、青年企业家峰会和G20国家议员的峰会后会议。
多伦多峰会标志着一个多方面的巨大转型。G20领导人从一个相对容易的任务,即应对一个已经发生的大型全球经济危机,转移到防止起始于小小希腊的下一场危机进一步侵袭整个欧洲乃至全球。领导人从一个相对容易的任务,即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转移到相对困难、政治上艰难的任务:削减慷慨的财政支出。多伦多峰会实现了另一个转变:从过去由帝国主义强国如美国和英国来领导、主办和主持峰会转变为由一个较小的大国来主办,尽管后者仍然是一个G7成员。多伦多峰会的议题进一步扩大,包含了新兴国家成员国的重点议题。它以制度化、不断推进的方式将市民社会纳入G20治理。由于G20劳工和就业部长级会议在2010年4月举行,它把部长级会议推广到金融议题之外,并且严肃地聚焦于指导如何创造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此外,由于一年一次的G8峰会在G20峰会前夕举行,而且会址离多伦多不远,那么多伦多峰会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合作分工和相得益彰。
第五次G20峰会于2010年11月11—12日在首尔举行,并获得圆满成功。①Ibid., pp. 383-384.这是 G20峰会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由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主办,而且由于APEC领导人会议不久前在日本举行,两者有联动作用。
首尔峰会既要守护脆弱且不平衡的全球经济复苏并遏制另一场在本次峰会前夕在冰岛引爆的欧洲金融危机,还要避免一场迫在眉睫的“货币战”,后者的主要诱因是美国和日本庞大的量化宽松、中国的人民币低估和最近巴西对热钱流入进行征税。G20领导人还必须遏制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并且向尚存怀疑的市场表明决心。这里,市场的怀疑是指市场看到了债台高筑的欧洲国家和民众抗议法国和英国采取令人痛苦的紧缩措施;G20领导人表明决心是指他们将不会改变在多伦多峰会做出的削减中期财政赤字和财务的承诺。
他们不仅基本做到了上述这些事情,还按期履行了当时做出的推进金融稳定的核心决定。②Nicholas Bayne and Stephen Woolcock, “The Fut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in Nicholas Bayne and Stephen Woolcock eds., New Economic Diplomacy: Decision-Making 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Farnham: Ashgate, 2011, pp. 359–378.他们同意进行第二阶段IMF份额改革并且同意在今后几年里改进重新分配配额机制,使之更加开放。他们还对第三版巴塞尔协议达成一致:金融机构将拥有更多的资本金和流动性比率。他们推迟了从冰岛迅速向全欧洲扩散的欧元区危机的进一步升级。为使全球化造福全人类,他们创造了首尔发展共识,具体包括促进发展和就业的25条承诺,以及建立了预留信用额度作为另一个防范金融安全的网络。
领导人已将G20从一个理性筹划的俱乐部转变为一个抒发个人情感的俱乐部。峰会期间对他们敬爱的、但即将离去的巴西总统表示敬意,会场自发地爆发出阵阵掌声;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的丈夫此前不久去世,领导人也对她个人表示哀悼。
整整一年后第6次G20峰会于2011年11月3—4日在法国戛纳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①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pp. 384-385.峰会遭遇并控制了一场岌岌可危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该危机最先始于日本,即 3月的地震、海啸加上核泄漏;然后是美国的主权债务信用降级;最后是欧洲主权债务遭到怀疑,主要国家包括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以及一家法国—比利时银行破产。峰会还必须阻止全球经济增长急速放慢、加强对正处于压力下的银行和全球系统性金融机构的金融管制和监管以及为IMF提供新的工具和资源,遏制一切具有传染性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峰会还推进了法国总统萨科齐作为2010年8月峰会主办人和主持人所提出的三个重点议题:国内货币体系必须加以现代化以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平抑动荡的资源商品市场;改善G20和联合国范围内的全球治理。
峰会期间,G20领导人完全忙于欧洲危机的处理。该危机再一次因希腊而面临紧要关头;正当领导人到达戛纳时意大利告急。他们用“打是疼、骂是爱”的方法来帮助希腊决定留在欧元区内;帮助意大利接受更严厉的金融监管以及要求意大利领导人贝卢斯科尼离开。他们采取行动扩大IMF的资源、加强金融稳定理事会的资源、作用和地位并任命马克·卡尼为其新主席,因为他肯定能用更聪明、更公正、更包容的金融管制和监管方式来领导金融稳定理事会。于是,领导人终于在最后关头遏制住希腊和意大利的金融危机,力挽狂澜于既倒,将一个几经自救而不能的欧洲救出火海。
领导人再次致力于首先取得中期财政稳固、随时出台短期财政刺激以及更切实灵活的汇率。他们绕过过时10年之久的世贸组织多哈会谈成果而专注更小规模的贸易自由化措施,以拯救最穷国家。他们否决了一种全球金融交易税,因为此刻欧洲特别需要更便宜的资金从国外流入欧洲;他们还否决了成立G20秘书处的提议。该提议要求将由国际行政官员以领导人的名义来代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领导人行使该俱乐部的权力。
第七次峰会于2012年6月18—19日在洛斯卡沃斯举行。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①Ibid., pp. 385-386; John J. Kirton, “Winning Together: Advanced Countries' Approach to G20 Governanc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G20 Semina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13, http://www.g20.utoronto.ca/biblio/kirton-sisu-2013.html; John J. Kirton,“G20-G8 Partnership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ackground paper for a conference on"From the G8 to the G20 and Beyond: Setting a Course for Economic Global Governance,"Chatham House, London, 2013, http://www.g8.utoronto.ca/scholar/kirton-chathamhouse-2013.html; John J. Kirton, “How the G20 Has Escaped Diminishing Returns,” Paper prepared for a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imes of Global Crisis: Views from G20 Countries,"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Moscow, 2012,http://www.g20.utoronto.ca/biblio/kirton-hse-2012.pdf; John J. Kirton, “Democratizing G20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Possibilities,” Paper prepared for a meeting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Network on “Global Governance versus Global Government: Worldwide Democracy and the G20,” Flemish Research Foundation, Leuven, Belgium, 2012, http://www.g20.utoronto.ca/biblio/kirton-leuven-2012.pdf; John J. Kirton, “The G20's Global Governance: Working for the World,” Lecture at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G20 and the Democratic Challenges of Global Governance,” Leuven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uven,Leuven, Belgium, 2012, http://www.g20.utoronto.ca/biblio/kirton-leuven-lecture-2012.html;John J. Kirton, Julia Kulik, and Caroline Bracht, “G20 Social Governance,” Paper prepared for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Global Social Law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Bremen, Bremen,2013.G20从此由一个仅仅是危机反应型委员会转变为一个既是危机反应型又是危机预防型委员会和全球指导委员会。它带来了全球亟须的双倍的红利:最终控制住不断升级的欧元区危机并阻止了它向全球扩散;并出台了一整套有重点的、机制性的议题,大为拓展了G20治理。
G20峰会再次忙于处理欧元危机:西班牙债务缠身,甚至法国也同希腊和意大利一样出现在投资人需谨慎的名单上。G20领导人敦促欧洲国家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创立地区性机构和机制来控制它们的问题。领导人承诺支持希腊的改革和可持续的道路。G20的欧元区成员承诺在规定的短时间内迅速采取行动,包括欧洲超国家银行管制和储蓄保险,并且采取“一切必要的政策措施保障地区统一和稳定”。②G20, “G20 Leaders Declaration,” Los Cabos, June 2012, http://www.g20.utoronto.ca/2012/2012-0619-loscabos.html.此承诺立即给西班牙和意大利当时高企的借贷成本带来持续的下降。到2013年4月为止,意大利的两年期国债成本降至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并且西班牙以史上最低收益率售出国债。
在洛斯卡沃斯峰会上,除美国和加拿大外,所有成员国都对IMF的新救援基金提供资金,以解救欧洲国家。本次峰会制定了一个可信的、强调经济刺激的战略以及不久将出台财政整顿计划,并且为此决定采取更宽松、更自动的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结构改革。它加强了就业和社会保障、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设施、金融管制和共享、食品安全和资源商品价格波动、发展、绿色经济增长、反腐和G20治理以及第一次涉及性别问题。
为落实日益增多的细节性且难以执行的干预国内政策的决定,领导人批准了洛斯卡沃斯责任评估框架,通过一个同行评审程序和国际组织的具体评估报告,以评估G20成员国履行承诺的进展。峰会重申并加强了主席国和主办国的轮流制传统,在G8成员和一个新兴非G8成员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墨西哥成为第一个分别在不同年份主持部长级和领导人级别的新兴成员国。墨西哥把韩国创立的先例进一步制度化:即由非G8成员国主办,主要来自民主国家和刚接纳南非的金砖国家集团等更强大的新兴国家。这一传统随后得以巩固:2013年9月俄罗斯主办峰会,2014年将返回亚太地区由澳大利亚主办,然后再于2015年移至土耳其、2016年又回到亚洲。
墨西哥主办的G20峰会也同G8峰会形成联动,这不是国家层面的联动,而是地区层面的联动:因为美国在一个月前,即5月18—19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办了 G8峰会,恰逢奥巴马即将准备连任竞选。作为一个创建于 1994年美洲国家峰会和创建于2005年北美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员国,墨西哥又获得了上述两个峰会以外的另一全球治理中心G20的主办国地位。
四、G20峰会的成效指标,2008—2013
对G20治理的成效指标作一个系统分析可以证明G20峰会的工作成效节节攀升。①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pp. 439-441.
指标一:国内政治管理。比较而言,前期领导人出席情况有所退步。最早三次峰会均全员出席。但由于多伦多峰会澳大利亚和巴西领导人没有出席,以及此后沙特领导人因病缺席,上述的完满记录被打破。不过,从峰会公报中对各国评价的第二项指标来看,前三次峰会的隐形缺席又大为不同:多伦多7席、首尔3席、戛纳11席以及洛斯卡沃斯6席。
指标二:交谈和结论中的审议结果。峰会公报结论中的公共部分在长度上稳步上升:华盛顿峰会共3,567词、伦敦6,155词、匹兹堡9,257词和多伦多11,078词。这部分地反映出该集团的议题和雄心日益扩大。首尔峰会发表了前所未有的15,776词、戛纳峰会14,107词以及洛斯卡沃斯峰会12,682词。
指标三:基于共识制定方向。作为对民主和人权原则的肯定,原则性和规范性方向的制定也有所上升。在匹兹堡峰会和首尔峰会上,这一指标跃至29条,而洛斯卡沃斯峰会则达到前所未有的34条。
指标四:决策和承诺。通过精确的、强制性的、面向未来的承诺所作出的峰会决策,也出现上升。第一个高峰是在匹兹堡,达到 128条。首尔峰会后一次比一次高,戛纳峰会达到 282条。这些承诺涵盖了广泛的议题,但基本只是继续最初关注的以经济和金融为核心的议题。在2012年洛斯卡沃斯峰会上,180条承诺涵盖14个问题领域,为首的是宏观经济,占37%,然后是金融监管、劳工和就业问题以及贸易问题,各占10%。
指标五:落实承诺。落实承诺分为三阶段,目前为止有87条重点承诺获得评估。获得评估的重点承诺的落实率是较高的:华盛顿峰会达到 77%,以及伦敦峰会 71%。此后,匹兹堡和多伦多峰会均下降至 64%。但到首尔峰会又回升至75%,戛纳峰会再上升至77%。截至距执行期满尚有5个月时间的2013年4月8日洛斯卡沃斯峰会,这项指标估计达到74%。
指标六: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G20内部制度发展的组成部分在公报文献中稳步上升,在多伦多峰会上跃至71条,并在首尔峰会上达到峰值99条。G20以外的机制的文献数量也同样上升,首尔峰会文献即达到31。
指标七:已完成的独特任务。G20的独特任务的完成情况也有所上升。第一个任务是金融稳定,首先是对2008—2009年危机的有效应对,然后到2010年移至预防国内危机。自2010年起,除了一些非G20的欧洲大陆小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外,此任务完成得相当不错。
全球化造福全人类的任务也有扩展,尽管开头较慢。自匹兹堡峰会起,G20开始日益关注就业问题。在发展问题上,多伦多峰会创建了发展工作小组,在首尔峰会上通过了首尔发展共识,并且在2013年峰会上增加了2015年后千年发展目标作为其10大议题之一。但是,G20峰会对解决大多数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的日益上升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却很少过问。①Civil 20 Task Force on Inequality, Civil 20 Proposals for Strong, Sustainable, Balanced and Inclusive Growth, CIvil 20, Moscow, 2013, http://www.g20.utoronto.ca/c20/C20_proposals_2013_final.pdf.
五、G20初获成效的原因:体系枢纽模型
G20成效日渐提升的原因可以从全球治理体系枢纽模型(Systemic Hub Model)中找到。②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pp. 444-470.
G20初获成效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因冲击激活的脆弱性,特别是金融和经济的共同核心领域的脆弱性。1997—2001年期间由亚洲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该集团 1999年的诞生和早期成功至关重要。而在没有金融危机的 2004—2005年间致力于升级G20的努力失败之后,美国触发的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该集团 2008年升级为领导人级别也就极为重要。欧元区危机的持续升级,从早期2010年的希腊到2013年的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推动了2010—1013年的全球危机预防的成功,因为G20如今已经对同样的冲击和这些冲击在当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迅速升级所能带来的全球破坏力极为敏感。
导致脆弱性的第二组冲击来自恐怖主义。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推进了渥太华部长级会议的成功、G20后来的工作以及布什当局选择于2008年举办G20峰会的最终决定。2005年7月7日伦敦恐怖主义袭击使所有领导人一致同意于2004—2005年保罗·马丁竞选结束后举行一次峰会,仅一人例外。激发G20成功的小型冲击还包括食品和能源涨价、石油钻井平台泄漏以及类似海地由地震和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
这些前后相连的冲击向所有成员国和其他国家显示,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面对来自一个相互联系密切、不确定和全球化世界的非国家威胁时也是脆弱的,因为这种威胁已不受时空限制。金融危机和次一级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强度和连续性可以解释G20何以从有效的危机反应转为有效的危机预防,但却不能解释其议题何以从粮食、能源和环境扩展到上述包括金融安全主题以外的政治安全领域。
G20成效日渐提升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创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正式多边组织和创建于1975年的更加非正式的多元多边机构均无力有效地应对这类冲击。欧洲主导的IMF和G7未能控制亚洲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在日益上升的亚洲大国的众目睽睽下,这催生了G20并超越了金融稳定论坛和IMF的国际金融和货币委员会。“9·11”恐怖袭击有力证明了羽翼未丰的G20是有成效的,而G7和IMF的成效不过是沾光而已。IMF和G8+5集团的欠缺和不足导致布什总统决定放弃G7选择G20峰会来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G20成立于1999年,但只是到了G20峰会召开,IMF才放弃其同G20竞争的战略;只有这样,它对G20来说才是不可或缺的。IMF和世界银行因此给了G20一个关键的正式的“192国集团”(G192)支持者,向 G20的非正式盟友 G7看齐。欧盟由于未能控制2010-2013年不断升级的地区危机而导致G20不断出手干预并取得成功。
原因之三,全球主导性和内部均衡化的能力,有助于解释这些特别的G20成员国何以能创建一个从1999年至2010年都保持成员不变的集团并取得成功;而反观G7、G8、IMF和等组织,其成员一再扩大。G20成员国赋予该集团一个至关重要的集体优势、内部相对能力逐渐均衡以及成员国的全球联系性,这是任何国际组织都无法替代的。萨默斯和马丁对新集体的成员取舍、接纳南非和阿根廷并将最终成员数定在19个国家,都表明选择的标准是相对能力和全球联系性,证明“体系重要性”这种新的定义确实恰如其分。对于一个失去时空限制的全球化了的世界来说,这是一个高度准确的、也是一个有高度预见性的标准和选择,因为1997-2011年金融安全的主要受益者印尼、韩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都理性地、负责地成为2008-2013年金融安全的提供者,只有欧洲人另择它途。亚洲大国中国、日本和印度一直是最大的稳定因素,如今都是这个最高层集团的平等成员,自1997年起便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的推动者。
G20成效日彰的原因之四,共通理念即各成员国的国内原则、政治开放实践及其基本要素和后果的日渐趋同。①Marc F. Plattner, “From the G8 to the G20,”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2, No. 1, 2011, pp.31–38.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并非所有体系性重要的候选国都可以成为正式成员。一开始,是印尼而非尼日利亚通过了公认的民主化政体施政的附加测评。后来,尼日利亚也通过了上述测评,但G20成员国已经按照今天人们熟知的数量予以冻结。无人同意一个非民主的埃及可以作为替补。两个非民主成员国沙特和中国同G20其他成员国一样拥有共同的核心理念,即以社会稳定和经济金融稳定为基础的政治稳定的中心作用。七国集团领导人在1975年后的亚洲、美洲、俄罗斯的民主革命,1997-2001年土耳其的民主革命以及2008-2013年的欧洲一直坚守这一原则。
原因之五是成员国国内的政治凝聚力,特别是参与者的政治资本、控制力、持续力、金融经济实力以及对G20论坛的个人担当,这有助于解释该组织在2001年和2008—2013年的两次飞跃。他们的带头人保罗·马丁从政前是一名首席执行官、1993—2002年是加拿大财长并于2003—2006年为加拿大领导人。与马丁为伴的是曾于1999—2001年担任美国财长和2009—2010年担任奥巴马经济顾问的萨默斯。鼎力相助他俩的是曾于1997—2007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和2007—2010年担任英国首相的布朗、于2001—2008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三次担任印度财长并自2004年起担任印度总理的辛格,以及自2003年到2012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
最后,G20逐渐成为一个日益扩大的全球治理网络的枢纽。它是一个高效合法的俱乐部。它营造出一种对全球性问题的敏锐性和共同掌权的方式,有利于许多成员国出于自身利益和更大的全球公益而领导、调整和治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代表们也是许多其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多元多边峰会的领导人。他们的结合是那么强烈的紧密、多样化、重叠,以致他们最后开始慢慢地将分散的个人绑在一起,从而将G20变成一个人际关系俱乐部。他们很在乎这个俱乐部。他们把这个俱乐部当成他们个人感兴趣、甚至在某些方面体现他们个人身份的核心元素。
结 论
从1999年危机催生到2013年成为全球中心,G20经历了国际机制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9—2001年的创建阶段:G20成为一个由运作性平等成员组成的有效集团,以加拿大、美国和其他G7成员国为主,治理并造就了金融稳定和造福所有人的全球化以及遏制恐怖融资;第二阶段是 2002—2007年的影响力均衡化:G20成为一个成员国更为平等的团体,包括真正平等地主办和主持会议,拥抱新兴成员国的政策优先并实现议题拓展,从新兴成员国发现能获得成功的议题倡议,等等;第三阶段是2008—2009年创建应对危机的峰会:G20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级别的、居于中心地位的全球治理集团,因为迅速崛起的新兴国家成员国相对完好无损并成功地拯救如今已经遍体鳞伤的发达国家美国—大西洋—欧洲成员国;第四阶段是2010—2013年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危机预防和指导的集团:G20的主办权移至新兴成员国,议题拓展至新兴成员国的重点问题和政治安全问题,对财政整顿、银行资本和IMF改革等问题作出重大决定以及不断升级的欧元危机获得控制。另外,G20慢慢成为一个各国领导人的个人俱乐部,不只是一个只顾推进本国利益的临时性论坛,而是一个可兼顾领导人自身、其国家公民及整个全球社会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