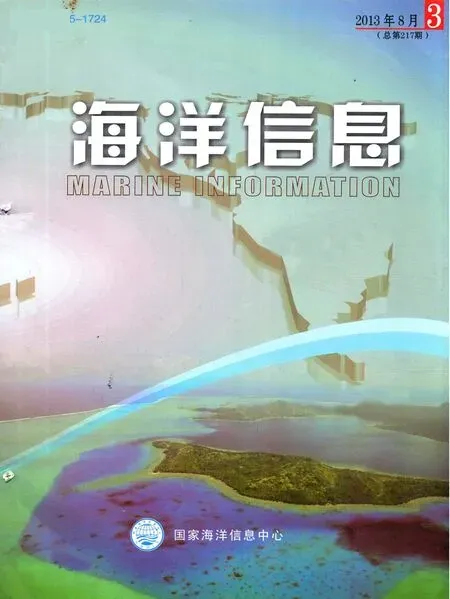古代海洋档案管窥
方 泉,薛惠芬
(中国海洋档案馆 天津市 300171)
1 古代海洋档案的视角
1.1 海洋档案是海洋文明的载体
在人类历史中,档案作为独特的文化载体,渗透着人类历史的血脉,潜移默化地向后人唤醒前辈的文化基因,向子孙后代展示传世的文明成果,而子孙后代则在自觉不自觉的成长中从各种文化基因遗传中汲取营养和动力,既传承历史,又创造历史,向着更加文明和进步而奋斗,同时产生新的档案,保留新的历史记忆,如此生生不息。
海洋乃人类摇篮。海洋档案,作为档案的组成部分,有着奇特的作用,并与人类进化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海洋档案记录了人类认识海洋、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真实反映了人类海洋活动的轨迹。古往今来,人类为海之蓝,洋之阔,浪高流急,水深物丰,神秘多变,而畏敬、感叹、溢美、抗争、探究、兴利避害,存留了浩瀚无垠的历史记录或称蓝色记忆,同时创造了不朽的海洋文化,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向前,向着更高、更广、更文明的阶段发展。
1.2 研究古代海洋档案的视角
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其具有原始性或原始的历史记录性,档案是文献中具有原始记录性的那部分。这部分文献不仅具有文献的一般性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历史凭证性价值。文献作为档案的属概念,即档案是文献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原始性的历史文献。并举例我国元代大航海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现已有国内外多个版本,无论它是否为善本,均不能认定为档案,只能称为历史海洋文献之一。而只有《岛夷志略》的手稿方可入围海洋档案[1]。这是符合档案的定义和档案学理论要求的。按照这个定义去界定古代海洋档案,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存世古代海洋档案稀有,但这并不等于我国古代海洋档案稀有,只是罕见那些古代海洋档案的原始实体和原生态信息而已。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献,历数百至数千年,屡遭厄难,能够幸存下来,实属不易,年代越久远越显珍稀。据历史记载,仅明清之前的1 000 多年历史中,我国古代的图书文献,就先后遭到了10 次大的厄运,小的厄运和破坏就更多,否则现在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将有可能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现在[2]。而档案文献比其他历史文献的命运更为凄惨,因其原件或原本唯一,稍有不慎或“风吹草动”,则可“毙命”而不可再生。它不像图书文献那样,会有许多复本“分身”而可能幸免于难。一言以蔽之,相对图书,传世档案确实很少,其中古代海洋档案实体尤其稀缺。那么,在缺乏档案原件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海洋档案呢?窃以为可“以变应变”,调节我们研究古代海洋档案的视角。
时过境迁,万物皆变。古代海洋档案同其他档案文献一样也在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古代海洋档案在它们产生和产生后的一定时段内,都是有原始实物(实体)存在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环境的影响,才导致大部分档案原件毁佚的。这部分档案虽已“皮之不存”,但是,其内容却可能“毛将有附”——被收录在其他历史文献中。这时的档案记录脱离了原档案实体,发生了原生档案信息的“依附性转移”。尽管该“依附性转移”中可能造成一定的信息误差,但是内容信息基本能转存下来而流传后世,这与连同其载体一起毁佚而致档案失传有天壤之别,它们再经历代文人学者的不断考释与纠错,在文字记录上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还原。因此,除了档案原件的介质和记录原样在“依附性转移”中有所变化外,记事档案的内容信息能基本保持不变。这种海洋档案信息“依附性转移”的历史现象,以及海洋文化的不间断传承,为我们研究古代海洋档案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切入点。
总体而言,古代海洋档案应包括其档案形式和记录内容2 个方面。档案形式包括物质载体形式和记录形式,这是档案的外在因素;只有记录内容是档案的内在信息,因此记录内容是档案的主要方面。由于古代海洋档案一般隐含于其他档案实体之中,其本身的外在因素并无特别之处。所以,当研究中缺少古代海洋档案的外在形式时,可以参考同时期传世的其他领域的档案物质与形式,而略知其概貌。当然,缺少原件,无直接的感官效果,会使研究不够全面,但只要能够发现和掌握古代海洋档案在“依附性转移”后的内容文献,我们研究古代海洋档案,则抓住了主要方面,就有了可以依托的根基。换言之,在缺少海洋档案的原始件时,不仅可从其他历史文献中发现许许多多古代海洋档案信息,而且可以此来反证我国古代海洋档案的丰富及其海洋文明的先进。其实,从档案编纂学到档案编研学,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理论支撑,只不过需要“倒视”而已。
在档案编研中,参照图书馆学理论,档案界将原始记录类的档案文献(如手稿、底稿等)称为零次档案文献(即一般意义上的档案),而随着加工层次的深入而有档案汇编、汇集类的一次档案文献,文摘、索引和目录类的二次档案文献,志书、年鉴、传纪类的三次档案文献等。由于一次、二次、三次档案文献均已脱离了原始档案实体,内容上随着加工深度的递增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在本质属性上,它们已经不再是原生态档案,而已经退化成了一般历史文献。本质区别就是它们在退化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档案本质的原始记录性。但是,当再无其他可更好地证明同样海洋活动的史料时,这类海洋文献已然无出其右地成为唯一选择。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透视”法,特别是在内容信息方面,依托和参考一、二、三次海洋文献去研究古代海洋档案,从而透过古代海洋文献来折射古代海洋档案的辉煌。
2 古代海洋档案管窥
我们将以历史朝代为序,以一次海洋档案文献为主,分别介绍以一、两种海洋文献,并以此管窥古代海洋档案。

图1 古绘《禹贡》九州图之部分
2.1 《禹贡》——中国最早的海洋档案
《禹贡》出自《尚书》,并作为中国地理志之始祖为历代学者所公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禹贡》千余字,贵有多处涉及海洋记录。诸如记录九州中有冀、兖、青、徐、扬五州临海;记录沿海径流“朝宗于海”或“入于海”或“东入于海”;九州疆域“东渐于海”等;记录沿海土壤、植被情况、肥沃程度、物产和赋税等;记录贡品中有多种多样海产品包括盐、鱼和贝锦、皮服等;记录东南沿海岛民穿着草编的服装;记录贡船或入渤海,临碣石再入黄河,或行济水,通漯水而达黄河,或沿长江,经黄海转达淮河、泗水等。由此可见,《禹贡》当属历史海洋文献无疑。然而,《禹贡》是否是最早的海洋档案文献呢?
我们说,《尚书》公认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历史文献。其中,《禹贡》以其成书之早、记载之全面,自面世以来一直为学人所推崇。《国语》、《墨子》、《孟子》、《荀子》、《周礼》等先秦文籍都曾引用《禹贡》的内容。到汉代司马迁将其全文录入《史记·夏本纪》一直流传至今。最新研究(以现代考古学者邵望平先生为代表)认为,《禹贡》之蓝本可能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或是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的追记;也有可能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而《禹贡》九州部分蓝本当出于公元前2000年,以后又经多次加工、修订,其基本定稿当在西周早期[3]。因此,《禹贡》可以认定为迄今发现最早的一次海洋档案文献。其原件可能是甲骨、简牍刻辞,亦可能为金文玉册形式,起码秦汉以后未见其物,仅可推测之。
2.2 《盐铁论》——中国最早涉及海洋管理的会议录
西汉昭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召开盐、铁会议,论辩双方藉论盐、铁为名,来“舒六艺之风”,实际上是儒法之争。由于这次召对是对话和对策同时并行,《盐铁论》即是会议对话记录。综观《尚书》、《左传》、《同语》、《战国策》、《史记》、《汉书》记载的夏、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历代王朝、侯国举行的重要会议,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争论问题之广泛,双方辩论之激烈,无出盐铁会议之右者。专记盐铁会议全过程的原始记录《盐铁论》,在现存作为古代档案文献的会议录中独树一帜,其卷帙之大,字数之巨,辩题之多,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任何会议记录也难望其项背[4]。就在这篇历史档案文献中,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即盐、铁、均输是官营还是私营。如“令(朝廷法令)意总一盐、铁”,“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盐铁论·复古》)“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盐铁论·轻重》)。其中论及的“盐”既包括海盐也包括陆盐(湖盐、井盐等),而盐专营的国策法令,一直被历代所推崇,至今不改,可见此策影响之深远。除了提及的海盐之外,《盐铁论》还记录了珊瑚为国宝(《盐铁论·力耕》)、海贝为钱币(《盐铁论·错币》)等多处涉海记录。但是,因其涉及海盐资源的管理制度与政策,而且是国家层面上的政策论证,可谓是我国海洋管理理论之先驱。
2.3 《论衡·书虚》——古代哲学家看海潮
东汉王充作《论衡》,约成书于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现存文85 篇(其中《招致》存目轶文)。王充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无神论精神,成为古代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两汉时代,是一个灾异符瑞盛行的迷信时代。王充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否定了天与鬼神,使迷信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在《论衡》抨击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24 篇文章,《书虚》为其中一篇。在《书虚》篇中,王充开门见山指出,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竹简与丝织品)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其实,有一些书,就是其作者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而已,并非与事实相符,接着王充举例而证。
在《书虚》一系列论证中,有一大段篇幅论及钱塘江等江河潮汐现象。王充说:“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且夫水难驱而人易从也。”王充在辩驳书言的逻辑混乱后,根据他自己的研究,着重指出,“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潮汐)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经曰‘江、汉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涛,竟以隘狭也。”“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在此,王充短短数语,将潮汐现象解释得深入浅出,玲珑剔透,即便现代海洋学家亦当诚服,而此乃2000年前的潮汐科普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更可贵的是,他提及其研究借助了前人成果的同时,又有新的创见。“江汉朝宗于海”出自《尚书·禹贡》,后人多解释为长江与汉水犹如诸侯朝见天子注入大海[5]。由上下文不难看出,王充的解释显然是长江与汉水之潮水来自大海。“宗于海”应理解为大海乃江汉潮水之源。可见,上古时代,中华先祖则对潮汐现象就有较深入研究的。而王充进一步指出了潮汐与地形、潮汐与天体的关系,其原理与现代潮汐科学基本一致。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古代学者多“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王充作为大哲学家更是如此。而且,王充乃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在钱塘江边土生土长,为官亦长期不离故土,故对钱塘大潮,应有长期观测与研究,以致对整个潮汐现象才有此真知灼见。王充“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后汉书·王充传》),见事而作著《论衡》。《论衡》稿本初为简牍百篇,始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至范晔写《后汉书》时仅可见到85 篇了。《论衡》在宋代以前无定本。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进士杨文昌用当时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与史馆本三十卷对校,“改正涂注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称为善本。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存最早刊印的全本[6]。总之,作为零次档案的《论衡》简牍稿本早已不知去向,现存善本和其他印本均为一次档案文献。
2.4 《佛国记》——东晋高僧法显的海国游记
《佛国记》,又名《高僧法显传》、《法显传》、《高僧传》、《历游天竺记传》等,为东晋高僧法显赴天竺(印度)艰难求经记录。法显去程从陆,返程浮海,往返凡15年,历经30 余国。同行僧人或分或合,或先返,独法显由天竺渡海到锡兰,乘商船回国,先遇风暴漂到爪哇岛,航向广州途中又遇暴风,于东晋末义熙八年(公元412年)终登陆青州长广郡(今青岛一带)。法显记录“即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船,海行艰险,以备大船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二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主人恐人来多,即斫绳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著水中。法显亦以军持及澡灌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弥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且不言其余涉海记录,仅此可知,当时海船较大,遇风暴而不毁,能利用信风使船,尚未使用罗盘,靠天文和地标导航,稳行西洋航线,航海技术娴熟。这与《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记载的过南海、经马六甲、穿越孟加拉湾而抵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附近的西洋航线基本一致。《佛国记》为研究南亚和东南亚沿海诸国和南海地区的历史、地理和古代中外海上交通提供了重要史料。
2.5 唐书——正史中的海洋档案记录举例
作为正史,唐书有新旧之分。旧唐书200卷,(后晋)刘昫等著;新唐书225 卷,(宋)欧阳修、宋祁著。均为纪传体,沿用太史公体例。我们《新唐书》为主,结合《旧唐书》的相关内容,说明史料中海洋档案记录的特点及其丰富程度,当然,这些均属“零次”以外的档案记录,至于究竟应属哪一次档案文献,要看具体的出处和引用内容。直接引用的内容当为一次档案文献,如在“帝本纪”中,常有下行文“制、敕、册、令”等格式和上行文“表、状、笺、启”等格式的引用内容;在“五行志”和“艺文志”中,常有来自原始档案的文摘、提要或题录式的内容,这些内容当属二次档案文献;而在诸多“列传”中,内容则混杂有一次、二次和三次档案文献的形式。仅以“海溢”(今称风暴潮或海啸)为例,唐书中海溢记录共有8 条,新旧唐书中对同一次海溢均见记录的仅5 条。《新唐书》较《旧唐书》记录条目多,《旧唐书》记录内容则较《新唐书》详细。但是,海溢条目均非想象中的被集中于一处列出,而是按纪元时间,有的出现在“帝本纪”中,有的出现在“五行志”中;有的重复出现在“帝本纪”和“五行志”中,有的则无对应记录。相对而言,在《新唐书》中的海溢记录尚较集中,仅出现在“帝本纪”和“五行志”两处。而其他有关海洋记录,则多出现在“五行志”、“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艺文志”和“列传”中,甚为隐散凌乱,欲阅检,实属不易。
2.6 《海潮赋》——唐代状元的海洋科学研究
《海潮赋》为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状元卢肇所著。《海潮赋》4 000 余言(赋序671字、赋文3487 字),为赋体形式的海洋科技专论。卢赋自序云:“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虚,系乎月也。”“肇观乎日月之运,乃识海潮之道,识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之辞”。又卢肇《进〈海潮赋〉状》云:“是敢窃以所撰前件《潮赋》并图进上。臣为此赋以二十余年,前后详参,实符象数。”在20 多年“识海潮之道”上,考虑了日月的天体引潮力,卢肇较之东汉王充又进一步。但在潮生于日的结论方面有欠科学。尽管如此,仍然轰动朝野。卢肇进献《海潮赋》后,受到懿宗皇帝褒奖,宣付史馆收藏,《新唐书·艺文志》亦有著录。
2.7 《梦溪笔谈》——宋代科学家沈括笔下的海洋记录
沈括乃宋代大科学家,《梦溪笔谈》成为记述他自己科研成果和实证其亲历见闻的不朽著作。“故所考虽杂而人不病其杂,所记虽细而人不病其细,上至天文地理、国典朝章,下至人伦日用、族群风俗,以至种种人不经意的物理现象,一经其手便皆成学问”[7]。《梦溪笔谈》最初刻的30 卷本,内容比今本要多,但早已散佚,仅26 卷本经宋元明清刊刻,流传下来。宋代有扬州刻本,乾道二年又曾重刻行世,惜宋刻今皆不存,更不必说其稿本了。目前最古的版本就是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代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难得的是,《梦溪笔谈》留给后人数条海洋记录。记录涉及海盐食用地域、盐税和运输费率的“宋代食盐”条(卷十一·官政一);记述海蚀现象的“巨嵎山震动”条和“海市蜃楼”条(卷二十一·异事(异疾附));记录海洋生物的“海蛮师”(即海狮)(卷二十一·异事异疾附)、“巨贝车渠(即砗磲)”条(卷二十二·谬误谲诈附);研究地质变化的“海陆变迁”条(卷二十四·杂志一);首次记录地磁及磁偏现象的“指南针”条(卷二十四·杂志一)和“磁针有指北者”条(卷二十六·补笔谈卷二),(至(宋)吴自牧著《梦粱录》时,已记载航海“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指南针在南宋航海中得到广泛应用);记录造船技术的“龙船坞”条(卷二十六·补笔谈卷二);研究潮汐现象及其子午潮的“海潮”条(卷二十六·补笔谈卷二)指出:“卢肇论海潮,以谓日出没所激而成,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当每日有常,安得复有早晚?予尝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月正午而生者为潮,则正子而生者为汐;正子而生者为潮,则正午而生者为汐。”纠正了卢肇《海潮赋》中的某些不科学论述。

图2 陈仁子东山书院《梦溪笔谈》刻本
2.8 《岛夷志略》——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亲历东西洋手记
说到元代海洋档案文献,不能不提及航海家汪大渊所撰的《岛夷志略》(有称《岛夷志》),其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无人能及。上承唐宋自不必言,而启下影响尤深。明代马欢在《瀛涯胜览》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于是编次成帙”说明马欢在随郑和出使西洋前,曾认真研读过《岛夷志略》,出使后经历海外各国中证实了汪大渊所记之详实,因而启发他撰写了《瀛涯胜览》,马欢叙事虽细,然涉猎地域不及《岛夷志略》所述之广。至于费信所撰《星槎胜览》,内容多抄自《岛夷志略》;而巩珍《西洋番国志》,条目内容雷同《瀛涯胜览》,“行文瞻雅”而已[8]。《岛夷志略》初为元末作者在南昌的单行刻本,已佚不存。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藏本均为其明代抄本,直至中华书局等之印本,虽经校注,也难免有别于单行刻本而现谬误之处。故而,仅可视为其“一次档案文献”。
2.9 《筹海图编》——16 世纪明代海防指南
《筹海图编》十三卷,图(包括地图、舰船、武器图等)172 幅,文约30 余万字。由郑若曾、邵芳绘图并撰写,胡宗宪编审,得到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人相助[9]。成书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国家图书馆藏有是年初刊本,属较典型的一次档案文献。《筹海图编》主要叙述了沿海的地理形势、倭寇的情况、明代的海防设置、海防方略、选兵、择将、治军原则以及当时的武器装备等。如何加强海防、抵御倭寇的入侵,是其论述的重点。《筹海图编》既辑录了当时的一些文臣武将提出的抗倭政治措施,又记录了这些文臣武将阐述的海防军事谋略。提出了“良吏优于良将,善政优于善战”(《筹海图编卷十一·叙寇原》)的政治思想,和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筹海图编卷十二·御海洋》),实行“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筹海图编卷十二·御海洋》)的军事方针,以及实行海陆结合、攻守结合、军民结合,利用近海、海岸和陆上要点的多层次的歼敌方略。《筹海图编》堪为当时抗倭战海指南性海洋档案文献。

图3 《海国记》抄本手稿
2.10 《海国记》——清代文学家、书法家笔下的海洋档案
《海国记》,《中山记历》的原名,乃清代文学家沈复《浮生六记》(即《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之五。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浮生六记》被人发现时“六记已缺二”。今《养生记道》仍佚,而《海国记》为文献收藏家彭令于2005年在南京发现,其被清代著名学者、大书法家钱梅溪转抄于名为《记事珠》的手稿中。该《记事珠》笔记为经折装,整体拉册,前后楠木硬封。其纸质为典型的清代竹纸。整部4 册计28 面,而抄录沈复《浮生六记》占18 面,约6 200 余字[10]。特别是《册封琉球国记略》一篇,更被多位学者认定为失传《海国记》抄本的原始件。沈复作为太史的“司笔砚”(类录事文书),随同正使齐鲲(太史)、副使费锡章(侍御官)从福建出发,分乘二船出使琉球国,专事大清王朝颁旨册封琉球国王之公干。途中,沈复以生动简洁的笔触记下了在钓鱼岛领域祭海的场景:“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因此,《海国记》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等档案文献一起,成为钓鱼岛乃我国固有领土的凭证而闻名于世。
3 古代海洋档案概况
3.1 古代海洋档案形式与内容
古代海洋档案是我们的祖先在对海洋认识及其海洋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总体而言,古代海洋档案同其他档案一样,其记录方式从口头传说到结绳记事,发明文字后则有手写、刀刻、印刷等;档案形式有文件、簿册、图纸等;档案的载体由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直至纸张等;载体从简单到复杂、从笨重到轻便、容量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无不体现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也标志着我国海洋文明的超前与飞跃。档案的数量也随着载体形式的变化与海洋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增加。
上文所列举了古代海洋文献内容信息,并作了相关背景介绍。这几件,只是古代海洋文献的九牛一毛。但可从一个侧面证明,古代海洋档案的内容十分丰富,且种类齐全,几乎涵盖古代海洋利用与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渔盐养殖、舟楫船造、港口航运、军事水战、滨海旅游和海洋科学技术研究等,并在15 世纪以前一直居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
3.2 古代海洋档案的显著特点
(1)原件稀有性。古代海洋档案原件存世罕稀,越古档案实体越少,甚至上古年代的档案实体几乎“绝迹”。迄今较近几百年间的部分海洋档案原件,尚可见诸于有关馆藏中,其余流传于世的古代海洋档案,其内容一般收录于早已实现“依附性转移”的刻本、抄本以及近现代印刷本文献中。
(2)内容隐蔽性。所谓古代海洋档案,只是记录内容涉及海洋领域的档案。而这些海洋记录并无专门辑录,因此,它们相当隐蔽,不易从古代文献的题名、子题名中直接被析出,必须阅读其原文的“章节字段”,才有可能发现。如前文所及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顾起元《客座赘语》、钱谷《续吴都文萃》等。
(3)母体分散性。古代海洋档案具有内容隐蔽性的同时,其内容可能的隐身之处即母体档案文献,或为一般的官方文书,或为民间隐士的随记,或为史志纪略,或为辞赋文学,或为其他等,可谓极其广布,不一而居,不择而栖。
(4)记录零星性。我国古代人类海洋活动记录,或长或短,短者只有几个字,长者亦有专著,更多的是片段或少量文字。
古代海洋档案的这些特点可从其他海洋文献的引文中总结。这些特点,决定了研究古代海洋档案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要研究古代海洋档案,除了个人必要的知识和严谨的学风外,还应更具毅力和耐心,更需要感兴趣的志士同仁,组成薪火相传的研究队伍,“沙里淘金”般地去寻觅、分析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开发与利用好古代海洋档案,从而将古代海洋档案文献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阶段,全面支撑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和我国海洋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1] 方泉,杜建军.海上风云激荡维权浪潮 神州文明钩沉蓝色记忆[J].海洋信息,2012(4):14-23.
[2] 桑健.图书馆学概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60-61.
[3] 容天伟,汪前进.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6(1):30-39,52.
[4] 吴荣政.专记盐铁会议的档案文献汇编《盐铁论》初探[J].档案学通讯,2010,(5):95-99.
[5] 江汉朝宗[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816984.htm.
[6] 论衡[EB/OL].http://shici.chazidian.com/shi31984/.htm.
[7] 梦溪笔谈[EB/OL].http://www.docin.com/p-428993181.htm.
[8] [元]汪大渊原著,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筹海图编[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441840.htm.
[10] 记事诛[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27410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