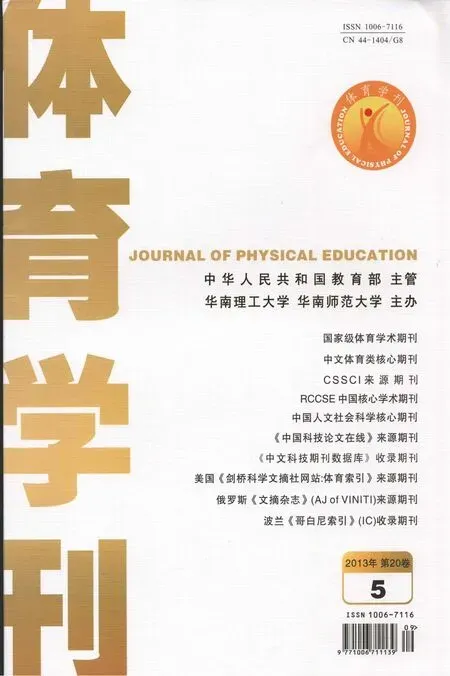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的传入及其对我国当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启示
梁立启,邓星华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同的学校体育思想相继传入,并呈现出时代性特征。回顾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百年历程,阐述不同历史阶段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的源流以及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思想对当代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启示具有现实意义。
1 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及影响
1.1 清末民初时期军国民体育思想
军国民教育源于德国,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想于20世纪初经日本传入我国。日本军国民教育的本质是通过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磨练军国主义精神,达到养成“忠良臣民”的国民教化目的;是把军国主义国家意志强行灌输给国民,并形成军国主义国民性格的教育。与此相适应的教育方法,第一是灌输,尤其是以“德目主义”(思想教育的标准)为中心的政治性教育,第二是行为锻炼,尤其是以“兵式体操”为中心的军事教练[1]。军国民教育思想传入我国,最初是由留日学生蔡锷、蒋百里在《新民丛报》先后发表言论,梁启超撰文支持;留日学生所办刊物,亦竞相提倡,以为呼应,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及《浙江潮》等刊物,都陆续发表有关军国民教育的相关文章,极力鼓吹[2];在清政府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要求小学、中学及高等学堂都开设“体操”科,让学生不间断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使“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在学校体育中得以具体体现,占据了体育教育的主导地位[3],逐渐演化为我国学校体育思想。
中华民国成立后,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指出:“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4]蔡元培所提倡的“军国民教育”就是“体育”,是通过对学生和全体民众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素质的训练,使他们具有军人的品德和体质,以达到抵御外侮、寓兵于民之目的的教育[5]。在民国初年由传统封建教育向资产阶级新教育转变时期,军国民体育思想仍然符合资产阶级“强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愿望,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赋予了“强国强兵、救亡图存”使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主导着清末民初时期学校体育的发展,发挥着应有价值。清王朝以军国民体育思想为指导,以培养“忠勇”之士,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在小学、中学及高等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6];民国初期出于外抗强敌、内抑军阀的政治需要,在各级学校继续推行军国民体育,培养身强体健的保家卫国人才。
军国民体育思想是近代以来首例引入我国的国外学校体育思想,其初步表达了我国学校体育与世界接轨的意愿,体现了自觉学习国外学校体育理念的态度,打开了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新局面。但军国民体育思想指导下的学校体育,其课程内容以兵式体操为主,教学形式机械呆板,体育课堂毫无生气,不仅抹煞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1.2 新文化运动后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
“五四”前夕爆发的“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空前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积极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掀起了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理念和制度的热潮。此时,建立在自卢梭以来的自然教育思想和约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基础上的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托马斯·伍德(Thomas D. Wood)、古利克(L. H.Gulick)、赫塞林顿(C.W. Hetherington)倡导,逐渐发展、完善,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校体育理论。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在“五四”前后自美国传入中国,它主要是通过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宣讲“实用主义”、教会在中国开展体育传播活动、留美学生回国宣传等途径来实现。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末,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等一批留美体育学者学成归国,纷纷著书立说,广泛传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努力开辟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生存的中国土壤。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强调体育的科学化、体育的教育化、体育教学的个体化、体育教学环境的自然化、体育内容的游戏化等[7],反对形式化的体操,提倡自然的体育运动,主张在体育教育实践中应从青少年儿童兴趣出发,以儿童为中心来安排体育课程[8],较之于军国民体育思想指导下的体育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均有明显的进步。“近鉴于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9],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甫入中国,即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者谋求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文化的需要相结合,在学校体育系统得到高度重视。因此,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取代军国民体育思想,并成为我国20世纪上半叶学校体育的主流思想,积极影响着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它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近代体育现代化进程,使中国独立的体育思想和体育体系得以形成;另一方面,从教学内容及教学形式与手段等方面都丰富了学校体育,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体育学科的发展[10]。
1.3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体育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提出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学校体育开始引入苏联体育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主智主义”体育理论。主智主义体育理论是在凯洛夫教育理论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学校体育学说,它强调体育教育的阶级性、工具论和统一性;重视传授知识、技能、技巧;重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主张教学手段多样化,面向全体学生;强调教学过程中的组织性和纪律性[11]。苏联学校体育理论主要包括“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教学思想和体质教育思想。1953年,我国教育部门组织翻译了苏联十年制学校体育教学大纲。以苏联《教学大纲》为蓝本,1956年我国制订了自己的《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和《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从1954年起,我国参照苏联的做法,首先在学校中实行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12]。
主智主义体育理论的传入,不仅使我们明确了学校体育是共产主义的教育手段,还为我国制定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和体质测试标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国学校体育都是在苏联学校体育理论的影响下,以增强学生体质思想为主导,以学习体育的基本知识、技术、技能及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为基本任务,运用“三段式”(准备、基本、结束三部分)课堂教学结构和凯洛夫教学原则开展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当时的学校体育教学秩序。但是,主智主义体育理论极端重视社会价值取向,强调体育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浓厚的政治色彩限制了学校体育的正常开展;注重运动技术教学,很容易忽视学生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强调教学以“课堂、教师、教材”为中心,弱化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因此,主智主义体育理论本身固有的片面性和我国不加批判的全盘引进,不利于该时期学校体育的持续发展。
1.4 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学校体育思想
从1978年开始历时3年多时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为“扬州会议”的召开奠定思想基础,明确了学校体育工作的思路,摆正了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还积极鼓励学校体育思想的大解放,掀起学习国外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大高潮,促进了此后学校体育思想多元并存局面的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体质教育思想、运动技术教育思想、快乐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健康教育思想、成功体育思想等纷纷登上了学校体育的舞台。
源于日本的快乐体育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过一些译著、日本学校体育专家来华讲学、赴日体育留学生的介绍以及一些短期访日人员的观后感等途径传入中国。快乐体育是以终身体育(生涯体育)观念在日本的传播和扩大、“运动手段论”向“运动内容论”体育价值观的转变以及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和国外游戏理论中尊重儿童个性的体现为理论基础。其立足点是“学生为中心主义”[13]。让学生在运动中充分体验运动的乐趣,培养内在喜欢体育的动机,从而掌握运动知识、技能,发展自我表现能力,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等,使学生内在参加体育的动机充满全过程[14]。由于快乐体育既是一个口号,也是一种体育教学指导思想,还是一个包括较完整的教材理论和教学方法论的教学实践体系[15],因此,快乐体育思想在学校体育领域占居一定地位,至今仍然影响着日本学校体育的发展。快乐体育思想提倡以激发学生运动兴趣为目标组织体育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运动,体验运动乐趣,使我国学校体育教学呈现出新思路、新方法。然而,由于传播者对快乐体育思想的片面解读和国内学者对新生思想的盲目跟风,在未完全准确把握快乐体育本意的前提下,使得我国学校体育教学操作过程中出现过度强调学生兴趣而忽视运动负荷的现象,这在国内也引起不小的争议。
终身体育思想是当前普遍流行的体育思想,并且成为各国学校体育改革的世界动向。法国成人教育家保尔·朗格朗(Paul Lengrand)在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第三届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终身教育议案”,明确提出“终身教育”学说,视教育为贯穿整个人生的、促进个体“学会学习”的全新概念,从而打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间彼此隔离的状态,构筑起民主化的终身教育体系。受终身教育思想的启发,国内外一些学者提出“终身体育”观念;前苏联A·V克诺布柯夫等人提出了“从0岁到100岁为止锻炼身体”的终身体育观点;日本学者早川太芳等人提出终身体育(日本又称“生涯体育”)的概念是“从幼儿到高龄阶段的生涯中所进行的体育”;我国学者王则珊[16]提出“终身体育,是指一个人终身进行体育锻炼和接受体育教育。”终身体育思想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体育贯穿人的一生,是生活中始终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阶段。虽然终身体育思想至今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以培养学生终身体育习惯为学校体育目标的理念是符合当前学校体育发展趋势的。因此,在深化学校体育改革之际,人们开始接受并尝试使用终身体育思想来指导学校体育的改革。终身体育思想立足于将学校体育的近期效应和长远效应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意识、习惯和能力,这是推动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接轨,对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积极、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17]。这一思想自传入即得到国内学校体育界的广泛认可,并迅猛发展。这一点可以从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得到全面反映。
2 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当代启示
审视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百年历程,不难发现没有哪一种国外学校体育思想能够在中国学校体育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各种国外学校体育思想在引入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功能。近代传入我国的学校体育思想被赋予“强种强国”的使命,即通过开展学校体育,强壮民族体格,抗击外族侵略,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富强;现代传入我国的学校体育思想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学生的发展,即通过学校体育教学,使学生收获健康和快乐,释放个性潜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从学校体育思想演变的轨迹来审视当前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现状,清晰地显现“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将统率各种学校体育思想,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目标,直接作用于我国学校体育的实践。
2.1 “健康第一”思想在现阶段必将占据指导地位
“健康第一”思想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针对性。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主席毛泽东针对学生营养不足,健康状况不良的实际,两次致信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指示“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为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当时的政务院在1951年8月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要求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改善学生健康状况。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经济十分困难,难以保证开展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条件,“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得到很好的贯彻和体现。
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来,具有极端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现象悄然出现,并影响到学校体育工作的正常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严重。针对此现象,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9年6月做出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强调“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至此,“健康第一”思想作为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地位得以明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校体育思想都可以成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只有具备了全面性(对学校体育各方面工作都能起主导作用),时代性(反映当代学校体育的先进思想和理念),长期性[18]等特征,并且能够直接反映国家对学校体育发展要求的体育思想才可以成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
“健康第一”思想明确提出健康是第一位的,强调健康的重要性,突出反映了当前人们对健康的正确理解和追求,不仅是国家强盛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学校教育和学校体育的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9]。从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各种思想的长期影响必须关注学校体育的对象,即学生,否则就无法长期存在。“健康第一”思想落实在学校体育实践中,将运动、健康、快乐等元素与学生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完美结合起来,全面体现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符合学校体育发展的规律;“健康第一”思想的根本思路是以学校体育为突破口,以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基础,最终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体现出着眼全局、着眼未来的大智慧。因此,“健康第一”思想在现阶段学校体育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并将更加牢固。
2.2 “健康第一”思想指导下的多元思想并存局面将长期存在
居于指导地位的学校体育思想是一定时期内学校体育思想的高度凝集。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多元体育思想与“健康第一”思想的关系如同“树枝”与“树干”的关系,“健康第一”思想强调学生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涵盖了体质教育思想、技术教育思想、快乐体育思想、成功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之要义。
用“健康第一”思想统领其他学校体育思想,既能避免认识的不足、思想的混乱、贯彻的不力,又能协调好各种学校体育思想的关系,使各种体育思想在不同学段、不同领域、不同水平层次皆能体现各自的价值。如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目标的快乐体育思想、成功体育思想,可以运用到教学组织中,成为实用性很强的课堂教学思想;终身体育思想以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习惯为目标,引入到高校体育教学中,便于将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接轨。
事实上,各种学校体育思想都是以育人为目的提出的,它们存在或交叉或相互渗透或从属或主导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相容的,“健康第一”思想为指导的多元思想并存局面会继续维持。
2.3 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将受到全面本土化改造
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的传入为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理念,尤其是21世纪初实施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学校体育的发展思路。尤其在感受到民族危机和意识到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时候,中国人是非常乐于学习一切先进事物,包括西方体育文化,只是他们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对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20]。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国内学校体育思想与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土洋体育”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用较短的时间快步走上了发达国家用了近百年时间探索的学校体育发展道路。但是,以国外学校体育思想来指引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方向,并不能针对我国学校体育现实状况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又容易使我国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在多元理念的背景下迷失自我及无所适从。因此,立足本土实际,进一步深化对学校体育本质、规律、价值的认识,对传入我国的国外学校体育思想进行科学的改造,确保国外学校体育思想适应并服务于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战略决策确立,在整个社会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在扬州召开,“扬州会议”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端正了人们对学校体育本质和功能的认识。继而从80年代开始,国外学校体育思想陆续传入我国,并形成多元并存的局面,共同作用于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但这一时期对不同学校体育思想的引进与实践大多停留在表浅层次和盲目模仿,缺乏分析与判断,急于照搬和挪用,结合我国的国情不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和体育实践层面的混乱[21]。因此,进一步深化对学校体育本质、规律、价值的认识,对传入我国的国外学校体育思想进行科学的改造,建立具有本土特质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才能确保国外学校体育思想服务于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2.4 学校体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22]。同样,学校体育思想的变化也与国情变化、时代发展相关联。纵观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我国的历程,无不与国情变化相关。军国民体育思想出现在清王朝封建统治即将衰亡之际;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借新文化运动发生之机传入;全盘引入苏联主智主义体育理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快乐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等学校体育思想多元并存格局出现在新时期思想大解放之后。由此可见,先前发生在政治领域的每一次历史转变,必然要求改革教育思想观念,变革学校体育发展思路,从而形成新的学校体育思想。当前“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是基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形成的,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2001年开始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明确“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理念,《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经过“研制—试行—修订”等环节,成为体育课程与教学实践的指导性文件。随着体育课程与教学实践的持续、深入开展,“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学校体育思想体系也趋于完善。
纵览国外学校体育思想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浓缩国外学校体育发展理念、符合我国特定阶段学校体育发展需要的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经过自主选择、主动引入、本土改造,深刻影响着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伴随着学校体育的理论升华和实践创新,未来我国各种学校体育思想仍将在“健康第一”思想指导下多元并存,共同作用于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1] 赵亚夫. 日本的军国民教育(1868—1945)[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2:13.
[2] 林儒,袁海军. 军国民教育思想下近代中国身体教育的主张与实践[J]. 体育与科学,2012,33(1):111,115-117.
[3] 傅砚农,吴丽华. “军国民思潮”主导学校体育的社会背景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2005(6):70-72.
[4]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4:130-136.
[5] 杨天平. 民国初年教育宗旨的理论基础[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7(4):77-80.
[6]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10.
[7] 赵諓华. 论自然体育及其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J]. 体育文史,1998(3):32-35.
[8] 潘志琛,王凯珍. 论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对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J]. 中国学校体育,1994(1):65-67.
[9] 王其慧,李宁. 中外体育史[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77.
[10] 王毅. 论民国时期自然体育思想对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J]. 前沿,2012(6):155-156.
[11] 陈建绩. 体育教学新论[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54-67.
[12] 毕世明. 论50年代学习苏联体育经验[J]. 体育科学,1992,12(3):9-12.
[13] 罗时铭. 快乐体育论[J]. 体育文史,1998(4):49-50.
[14] 刘绍曾. 日本“生涯体育”、“快乐体育”思想述评[J]. 体育科学,1993,13(5):29-30.
[15] 毛振明. 快乐体育的理论及产生背景[J]. 中国学校体育,1996(6):61-63.
[16] 王则珊. 终身体育[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4:13-14..
[17] 陈琦. 从终身体育思想审视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J]. 体育科学,2004,24(1):40-43.
[18] 陈琦. 以终身体育思想作为学校体育主导思想的研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05-111.
[19] 邓星华,杨文轩. “健康第一”的理论依据与学校体育的新使命[J]. 体育学刊,2002,9(1):12-14.
[20] 谭华. 70年前的一场中国体育发展道路之争[J].体育文化导刊,2005(7):62-65.
[21] 谷红红,陈玉忠,孟凡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2008(11):96-98.
[22] 叶澜. 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19(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