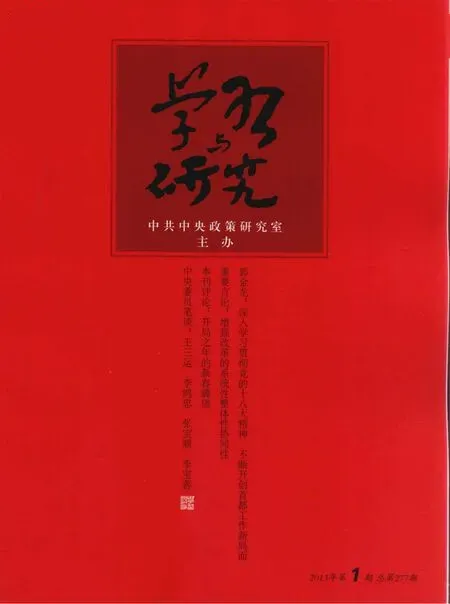分化的村庄与分化的农民
宋丽娜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村庄分化与农民分化彰显了乡村社会正在处于巨大的转型中,分化成为了理解农村社会众多政治社会现象的基础。本文试图在村庄经验的基础上呈现出村庄分化和农民的分化的样态,并且在相互关联的经验中理解这些样态的不同运作机理。所采用的典型是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渔村,著名的“鱼米之乡”,全村紧抱洪湖。全场共有养殖面积8200亩,其中渔场4200亩,大湖围栏生态养殖4000亩,全场有340户,7个村民小组,人口1500人,劳动力880个。笔者在2011年1月8日至20日在渔村做了为期12天的农村社会调查。本文运用在渔村得到的材料来表现农村社会的分化状况,并且在村庄的语境中探讨分化的社会机制以及分化产生的社会后果。
一、村庄分化
村庄层面的分化主要体现在农民经济和政治上的分化,即农民的收入结构和社会身份上开始出现分化。村庄分化的意义在于,这种分化成为村庄中的结构性因素,制约着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村庄分化是村庄作为整体而出现的社会变化新趋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
渔村的村庄分化集中发生在世纪之交。在2000年之前,渔村农民的经济收入分化并不明显,农民相互之间的经济平衡能够得到低度的维系。渔村的农民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是典型的“渔民”。2000年之前,渔村的农民在经济收入上有着自己的分工体系:一部分农民通过抓阄拥有自家的池子,而另一部分农民则在洪湖上捕鱼。这两种生存方式各有利弊,相互平衡。拥有自家池子的农民可以有计划的养殖鱼、螃蟹等,他们要向村组集体交纳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的一部分用于上缴农业税费,另一部分要分配给村民组中没有池子的农民。一个10亩的池子在2000年之前最高一年要缴纳高达4000元的费用。而另一部分农民没有池子,他们就在大湖(即洪湖)上以捕天然鱼为生,这种方式不需要向村集体加纳任何费用,并且没有额外的生产成本。在2000年之前,两种生产方式是相互平衡的,拥有池子的人家要付出较高的生产成本,而没有池子的人家也能在大湖上获得不菲的收入,农民相互之间的经济差距并不大。
在2000年之后,特别是2003年国家进行税费改革之后,渔村经济收入上的平衡就被打破了。首先是因为鱼蟹销售行情变好,价格上涨,特别是螃蟹的行情尤其好,一部分拥有较多池子,并且勤劳的农民在经济收入上的优越性越来越凸显出来;一部分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渔产生意人也迅速变得富有。其次的原因是国家税费改革取消了涉农税费,并且给予当地农民“柴油补贴”,这使得拥有池子的农民更加得利。再次是因为农民在洪湖里捕天然鱼的成本则越来越高,一方面因为过度捕鱼和水质污染的问题,天然鱼的数量急剧减少,另一方面,少数较“狠”的农民抢先在洪湖中占据面子,他们用竹竿围起来,通过耍狠来维系自身的利益,这使得可以捕鱼的公共面积越来越少。因为洪湖的问题而引起的相当一部分没有池子的农民成为了“赤贫”状态。最后,“讲狠”越来越成为当地社会获得经济好处的途径,一部分讲狠的农民通过设立“关卡”收费、强占大湖面子、涉足公共事务、做渔产生意等方式来获得经济收入,又狠又乖①的人成为了村庄中的“大老板”,他们拥有财富,并且干涉村庄公共事务。
渔村的村庄分化集中表现在经济上的分化,如今的渔村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村庄中有钱的少数大老板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处于第一层级的农民一般都是45岁以下的青壮年;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赤贫”的农民,他们没有池子,又没有其他生存的技能,只能到大湖里以捕天然鱼为生,但是如今捕鱼越来越难了,他们的收入很不稳定。下表是渔村的经济分化情况:

表1 渔村的经济收入分化
经济收入上的分化引起了村庄各个层面的分化表现:在村庄政治上,经济收入高的农民谋求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部分人是村庄中收入最高的人群,同时又是较“狠”的人,他们不仅倾心于自身生意的发达,对于公共利益也多有染指。而在位的村干部在分配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的时候更是对于富人不敢小视,甚至要偷偷为富人和狠人分配一定的公共利益以安抚他们。可以说,村庄中的富人、狠人和干部有相互结盟的趋势。与此同时,其他的农民则有极强的情绪,他们经济收入较差,或者没有池子,也或者没有占到公共利益的好处,也有些人本身应有的权益也无法保证,这些农民处于弱势,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各种资源都是匮乏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村庄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即在村庄中形成了明显的断层。
影响村庄分化的有三个不同的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关于经济上的,主要体现在是否拥有池子、是否有技能、是否有做生意的头脑等,拥有池子、并且有头脑且技能较高的人就容易处于高位,而没有池子又头脑“不乖”的人则被甩在边缘。第二个系统是政治上的,主要体现在村组干部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渔村集体田地(即池子)的分配就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也是矛盾的集中爆发点。此外,分配给渔村集体的大湖面积(有1800亩)也以不同的方式“承包”到户。这个系统主要是政治权力分配公共资源的问题,而这些资源一旦分配到户就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应,即这个系统也能间接地产生经济效应。第三个系统是关于“狠人”的,即关于混混的社会系统。村庄中的某些人通过“耍狠”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他们不按照规则办事,“狠”就是他们办事的规则,即谁越狠获得的好处越多。比如有些人因为“狠”强占集体的多个池子,并且多年不出让给别人,就算是他本人不经营也转包给别人,从而获得转包费用。也有些人在生意中“强买强卖”,低价收购高价出售,在本村的码头设立“关卡”,以暴力为后盾强迫农民低价出售。甚至有的大老板雇用混混来“做生意”,以此谋求利益。村庄中的“狠人”还涉足公共利益,村集体的各种招标项目,以及公共的池子和大湖面积都少不了他们的介入。甚至,村庄中的狠人群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利益分配的平衡机制,比如,2009年渔村有国家下拨的项目90万元,是修下水道的,项目招标的全过程都有狠人的参与,他们甚至操作整个过程。最后的结果是村庄中的“狠人”每人获得了一份大约5000元的好处费,而工程由其中的一个人来做。其中一个获得好处的农民向笔者透漏,共有15人左右获得了好处。这部分人就是村庄中的狠人群体,他们染指公共利益,对于村组干部恩威并施;在长期的利益博弈过程中,他们已经形成了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
以上三个系统共同指向的是经济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在笔者看来,第一个系统是较为正常的经济资源生产和分配的系统,能够促进“勤劳致富”的正向价值观的形成。第二个系统受到第三个系统的强烈渗透,政治权力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受制于“狠人”的社会系统。其中的逻辑是,政治权力为了平衡利益关系,为了获得对于社会的一时治理就拿公共资源作为交换,正式的公共规则无法实施,这助长了以“狠”为特征的社会风气,长此以往,形势将越来越无法收拾。目前的渔村就是三套系统的混合并用,处于第一层级的农民多数都是靠“狠”发家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依靠自身的勤劳和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而第二和第三层级的农民多数都与公共利益无关,是弱势的大多数。三套系统中,第一套系统导向社会正向的价值观,而第三套系统则导向了以暴力为基础的负向价值观,这对于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巨大。第二套系统国家承认的正式制度设置,本应是运用权力来导向正向的价值观和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促发第一套系统、抑制第三套系统,然而在渔村其正常运作却越来越受制于第三套系统。
村庄层面的分化以经济收入上的分化为表现形式,分为三个不同的层级,而这些经济分层的背后却有三套不同的生产和分配机制。渔村的村庄分化表明,农民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同层级的结构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在经济收入不断增长的形势下,村庄分化是必然要产生的社会现象,重要的是社会要导向关于分化的正向价值观,即经济资源的生产和分配要获得多数农民的认可,要顾及公平和正义的原则。而村庄分化中第三套系统的运作则产生了较大的坏处,不仅使得基层治理陷入恶性循环,而且暴力的逻辑使得公理和公正的价值体系在农民的心目中轰然倒塌,村庄分化的正当性也随之受到农民观念体系的抵触。
二、农民分化
村庄分化是整体层面的社会事实,而农民的分化却是具体层面的社会事实。在村庄分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农村社会的文化也发生了异变,农民的观念世界正在发生着一场革命,这场思想的革命影响到了农民的行为逻辑,从而使得原本生活于“乡土社会”的农民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在渔村表现为老人、妇女、青少年、青壮年等显示出明显的群体特征,家庭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孝道、夫妻伦理、节俭、责任等不再成为主导农民行为逻辑的文化基因。农民的分化就是在以上文化异变的背景下发生的社会事实。
在渔村调查期间,给予笔者印象最深的要数老人的处境,他们独居低矮的房子以及“自觉”的心态,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前,渔村的老人一般都是独居,与儿女分住。可是诡异的是,子女的房子一般都是两层或者两层以上的楼房,而老人则多是低矮的平房。笔者在渔村调查期间发现,老人一般都居住在池子旁边,即在池子旁边搭建一个简单的房子,老人居住于此,并且要替儿女看护池子②。而事实上,儿女住的楼房也多是父母辛劳多年的积蓄所建,在子女结婚之后父母就要自动搬出这个新家。农民对于此的理由是,父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不方便”:老人要吃软饭,而子女则喜欢吃硬饭;老人不讲究卫生,而年轻人却要非常干净;老人喜欢节俭,而年轻人则大手大脚;老人喜欢“说三道四”,而年轻人对此却非常反感。如果居住在一起,两代之间在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上的矛盾会时常爆发。由于老人的体力和精力、以及经济上都处于弱势,矛盾的解决往往是以老人的失败而告终,在这种不断博弈的过程中,老人不断变得“自觉”,自觉的承担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自觉的以子女、特别是以儿媳妇为中心,自觉的帮助儿女劳动,自觉的搬到矮小的房子里。如今,老人的“自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行为模式,他们认为,“自觉”的老人是“聪明”的。在渔村,笔者遇见这样一对老人。老人不是本村人,在渔村也没有房子,而是居住在船上长达6年之久了。他们是附近村庄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但是却没有老人的容身之地。于是,两个老人就在渔村的码头找到一个可居住的渔船安家。已经超过70岁的老人如今每天都出湖打渔,以挣取维系自身生存的费用。提到自己的两个儿子,老人没有任何抱怨,反而替儿子说话,说两个儿子的条件都不好,生活负担大等等。老人对于儿女的“自觉”,对于生活的无奈和寒心,与儿女对于老人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老人的“自觉”对照的是妇女的生活状态。渔村已婚妇女很少有正式的工作,除了日常家务劳动之外,她们多是在家与丈夫一起养鱼、养螃蟹以及做生意,只有10%~20%的妇女在附近的工厂以及服务业中工作。而事实上,如果农民养殖,一年中就有半年以上的空闲时间,他们往往在开春的3月份投苗,期间稍加管理、并且投放饲料,在下半年的9~11月份收获,收获之后就无劳动可干。如果做渔产生意,空闲时间更多,他们只需要在收获季节(9~11月)集中繁忙三个月即可,其余时间都无事可做。对于在家的妇女来说,她们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如今的渔村盛行打牌打麻将,平日里无事的农民,特别是妇女都“以打牌为业”,她们借以打发无聊的时光。据笔者在村庄中的调查,有一半左右的妇女经常打牌,有约1/3的妇女则有“牌瘾”,即每日“以打牌为业”,甚至家庭生活中正常的家务劳动和日常三餐都不愿意多问。她们饿了就随便吃些东西,或者到小餐馆中吃饭,经常不为家里做饭做家务,家中的丈夫和孩子因此并没有正常吃饭。甚至有的妇女对于年幼的孩子也不闻不问,提到孩子的时候她们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打牌成为了妇女打发无聊时光的主要形式,可是打牌却对于家庭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家务劳动和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也会出现问题,孩子的家庭生活环境恶化,妇女、以及整个社会的家庭责任感都有所下降。妇女的“无聊”生活彰显着的不仅仅是大量的空闲时光,也是意义世界的缺失。“以打牌为业”彰显了她们精神上的空虚,在这样的生活中,她们自身无法建立起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感和责任感,无法承担起社会和家庭赋予她们的责任。
渔村的青少年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2000年前后,村庄内部的青少年群体开始集中出现“混社会”的情况,如今,这种村庄内部的“江湖社会”已经颇具规模。当地的青少年多数都是初中毕业,有一部分人继续读书,相当部分则进入社会。然而,这些青少年年少气盛,争强好胜,向往干净、轻松和体面的生活,都不愿意如同他们的父辈一样勤勤恳恳地劳动。早早进入社会的青少年或者依靠家里供养,或者逐步开始“混社会”。他们开始想尽办法“挣钱”,彼此之间都不甘示弱,时常会借助于暴力解决彼此之间的事情。如今的渔村,有30~40个没有固定工作的青少年,他们往往依附于村庄内部的“老板”,充当“打手”,即老板有事要解决的时候喊他们,并且给予他们一些好处。这些青少年也对于集体资源和公共事务有所染指,简单地说就是,只要有好处的事情他们都要干。渔村2000年之后共有10多人“犯事”,打群架、强奸,甚至在暴力冲突中将别人打死,其中有8人已被判刑,还有几人至今还在外逃,而参与过暴力冲突的青少年就更多了。他们的逻辑是“不抢不狠就搞不到钱”。2008年渔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户人家的儿子“犯事”了,结果被当地公安控制,家中的父母居然在村庄中挨家挨户要求群众出钱,他们说,“你们不出钱,我儿子就要枪毙了!”农民都讲究邻里情面,尽管觉得此事别扭,但是别人上门求助的时候他们并不好拒绝,每户都至少出了50元。当年还有一户人家整了一场酒,其缘由是儿子坐牢回来了,没有钱谋生,趁着整酒的机会收一些钱以供以后的生活费用。尽管以上的事情在村庄中还是少数,尽管混社会的青少年并不是全部,可是,他们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巨大。农村的青少年在进行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没有受到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后果,关于“暴力”的逻辑大行其道。然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却是社会提供给青少年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急剧缩减,年幼的青少年对于未来少有预期,他们在小小的年纪便发现了父辈信奉的一切都已经不再可能了,而要在既有的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方式便是混社会,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整个村庄和周围社会的和谐氛围。
渔村的青壮年是直接受经济分化影响的群体,他们最深切感到了村庄分化带给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同一个村庄中,少数个别的人成为“老板”,家财万贯,笼络了一批青少年为其卖命;而也有少数人依附于各个老板,以“狠”为特征,在既有的村庄治理格局中求得生存的空间;大多数的农民则只有被动的接受既有的利益格局和分配规则,他们固守自家的池子,勤恳劳作,以求得家庭和个人的发展;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则是“赤贫”阶层,他们没有池子,也无突出的本领,不善于劳作,只得生活在村庄的夹缝中,或者出湖打渔,或者以打工度日。青壮年的面部表情就是他们心理落差的反应,老板们趾高气扬,红光满面,连说话的声音都要大一些;而普通的农民则处处谨小慎微,和气而谦逊;最为特殊的是那些赤贫的农民,他们大多面目麻木,不敢多言,听天由命。青壮年是一个社区的中坚力量,他们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然而,财富分配体系的不公正,以及劳动伦理和基层治理的恶化都使得他们变成了村庄中怨声最大的群体。笔者在渔村调查期间,几乎所有的中青年农民都在抱怨世道的不公,狠人直言抱怨官员和政府的无为,而普通农民则有更多的抱怨:政府的无为和狠人的猖獗。一时间,基层政府似乎成为了众矢之的,村庄中的各种势力和各种人群都在抱怨。基层政府是公共事务和集体资源的分配者,他们为了“和谐”就给予村庄中的灰黑势力一定的好处,这一方面有损于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却也没有达到息事宁人的效果,因为灰黑势力的胃口是不能被填饱的,基层治理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内卷化”(贺雪峰,2011),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村庄中的各种势力都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基层政府。青壮年群体中充斥着强烈的由于社会不公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渔村农民分化的群体特征明显,农民之间彼此按照青少年、青壮年、妇女、老人等归类,相互之间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圈子,青少年多与青少年一起活动,老人也只有与老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说上一些话。农民的分化意味着农民已经与传统的家庭关系脱离了,原本用于连接和规范家庭关系的伦理观念(孝道、妇道、家庭责任和义务等)已经日渐失效。家庭和子女不再是老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如今的老人自产自食,很少从子女那里得到生活的成本,聪明的老人往往在尚能够劳动的时候便开始为自己存钱养老了。老人不再指望子女的赡养,可是他们却要像以往一样为子女付出自己的所有。身为父母,对于孩子的管教也越来越吃力,要让青少年像老一辈农民那么勤恳劳作、安分守己也已经越来越难了,青少年不服父母的管教,不肯踏踏实实的劳动,又不肯过着节衣缩食的穷苦日子,他们有相当一部分组织了自身的“江湖社会”,在社会的灰色地带谋求一份不光彩的生计。而今的妇女也不像在传统时代一样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她们以自己的行动改换了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她们不必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对于孩子的管教也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常年休闲的妇女只好以打牌来消磨自己的“无聊时光”。青壮年群体则主要受到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影响,而产生强烈的抱怨情绪。
按照年龄和性别的不同,村庄中的农民分化为了不同的群体,并且群体特征明显。农民受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的影响日益减少,而与自身相仿的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却日渐增多。这意味着,传统的家庭伦理已经不再能够成为整合农民日常生活的中心,已经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意义依托。农民的分化成为村庄中的一个基本事实。
三、分化的社会机制
村庄分化和农民分化已经成为广大中国农村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只是因为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有的农村分化程度大,而有的则分化程度小。然而,分化却是不同农村的共同特征。笔者把村庄中的分化机制分为两部分来讨论,一是村庄整体层面的分化,主要体现在村庄经济分化上,由此造成农民之间的贫富悬殊;二是农民在群体特征上的分化,主要体现在老人、妇女、青少年和青壮年相互之间的隔离。
经济分化主要体现在经济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体制上,其社会后果是产生贫富之间的差距。对于经历过社会主义平等传统的中国农民而言,村庄中的贫富差距要维系在一定的限度,并且要获得经济生产和分配的正当性。然而,笔者在渔村观察到的现实中,贫富差距越来越超越于一定的限度了,而经济生产和分配的正当性也正在不断受到挑战。经济分化具有积累的效应,农民的经济收入是其村庄生活的基础,经济收入不仅关联着农民的生计,也是农民获得自信和做人尊严的载体,更是农民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和获得生活意义的依托。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分化的拉大不仅对于农民个体,而且对于村庄结构和村庄未来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农民分化是与经济分化相伴而生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变迁在文化层面的反应。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不再是农民处理家庭事务的行为准则,农民越来越挣脱家庭伦理的束缚,代际关系发生了异变,集中表现在老人的弱势地位;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减弱,表现在妇女的“无聊生活”,青少年的“混社会”等。农民的分化表明,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性别的农民被家庭整合的可能性日趋降低,而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生活却成为他们另外一个重要的生活场合。然而,群体之间的生活只能满足农民在社会交往上的需要,农民的经济收入、生长环境、亲情和关爱、对未来的寄托却无法在群体生活中获得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农民的分化喜忧参半。
通过对渔村村庄分化和农民分化的研究,笔者试图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社会命题:分化已经成为了农村社会的既成事实。如何把经济分化维系到一定的限度,并且重建经济资源分配的正当性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课题;而如何规范农民的分化,建立有利于农民个体成长的社会环境,重建农民的价值体系,和建立对未来长远预期的家庭环境是另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乖”是湖北方言,带有贬义,意思是头脑灵活、狡猾奸诈之人。
② 在池子里养鱼和养螃蟹都需要人看护,以防在成熟的季节被人偷去。
[1]杨建华.论社会分化的三个维度[J].浙江学刊,2010,(1).
[2]陈文玲.道德分层与村民的“脸面”[J].江西社会科学,2009,(11).
[3]张乐天.农村社区中的社会分化与整合——以浙北农村为例的调查[J].战略与管理,1994,(4).
[4]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5]贺雪峰.基层治理内卷化[J].开放时代,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