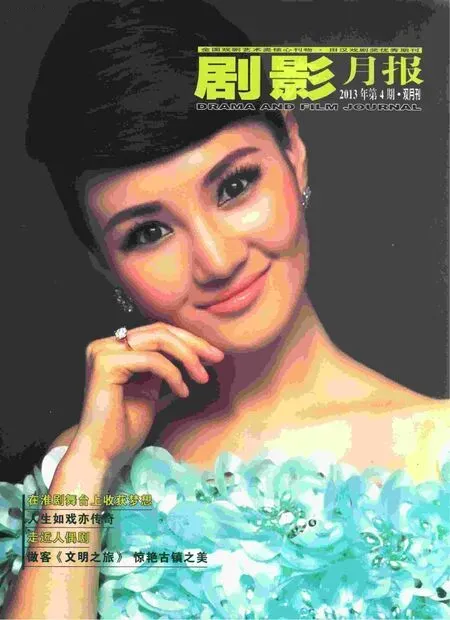浅论戏曲道具的符号性
■吕建平
戏曲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处处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审美情趣。戏曲对中华文化审美情趣所提炼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程式性。戏曲的程式性表现于其各个方面,而戏曲表演中的道具使用,就是戏曲程式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中国戏曲的程式化特点,总让我会想到西方的符号学的概念。符号学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符号学虽然是一个外来的理论,但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戏曲时,不妨套用一下西方的概念,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戏曲程式化特点具有符号学的特征,我仅从中国传统戏曲的道具使用上,谈谈戏曲道具所具有的符号学上的意义。
与西方的文化审美不同,中国的文化审美讲究的是将实物虚拟化,这种审美特点广泛地体现在了中国的绘画、音乐、文学创作等各个方面。中国的文化审美要求的不是逼真,而是神似,再加上我们国家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因此众口难调,所以很多时候,会取各方面的最大公约数,即每个地方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与自己的文化圈相似的地方,但这种最大公约数的文化又不曾与哪个具体的文化圈完全一致。而这种所谓的“大约相同”正是中国传统戏曲能具有程式性特征的基础。
体现在传统戏曲道具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种传统戏曲道具的程式性具有强烈的符号性。而道具的这种符号性可谓是深入人心,出现在舞台上时,配合着演员的程式化动作,观众们便可心领神会,无需多解。比如说,用马鞭代替骑马,用船桨代替船,用车旗代替车,用帐子代替床等等,都是用实物的某一部份来代替实物整体。
可以说,在戏曲舞台上,很多时候,所使用的道具与真实生活中的很不相同,有时候,这些道具也比真实生活中的物体简单了不少。有些物体被全部或大部分虚拟掉了,而采用一些约定俗成的动作来表演。而这些物体的取代物便具有了符号性。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讲究留白,如果放在戏曲舞台上的时候,讲究的是净台,所以传统戏曲中,道具都不算复杂,但如果哪件道具被运用于舞台上,往往这件道具的使用就有了符号学上的意义,最为典型的,就是扇子的运用。
扇子是戏曲中最为常见的道具,被广泛地运用在戏曲中。扇子不仅仅是装饰,有时还和戏里的情节有关,对演员的身段动作也能起到辅助作用,在表达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喜怒哀乐的情绪方面,扇子大有文章可做。而扇子也具有其特定的符号性。正如,我们看到舞台上的人物画的是红脸,我们就知道这是个英雄,画个白脸,我们就知道这人是奸臣一样,其实,我们同样可以从人物使用的扇子中,知道人物的身份。用折扇的一定的大家闺秀,比如杜丽娘、杨玉环。如果用的是团扇,那一定是丫环,比如春香和红娘。用大折扇的不是净就是丑,而且通常不是什么好人。而且如果在大折扇上画上大牡丹,则表明,所执扇子的人不光很有权势,而且还特别喜好女色,比如《艳阳楼》中的高登、《溪皇庄》中的花得雷。
再比如戏曲舞台常有布景和道具合二为一的表现手法,借此解决表演与空间布景之间的矛盾问题。如《琼林宴》中范仲禹被灌醉,关在书房里,桌上只一支蜡烛,而这支蜡烛同样也具有了符号性。范仲禹拿着它满房巡视了一下,此时蜡烛是演员手里的道具,但当演员唱“叹飘零……”倾诉冤情时,这支蜡烛又渲染了被囚禁的悲凉氛围,产生“景”的效果。
然而,随着当代舞台上声光电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戏曲舞台上的道具使用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新问题。很多时候,舞台上的道具用得太实。亭台楼阁桥船车都能出现在舞台上。然而,大制作不等于花大钱,有时候,不是说道具花钱越多,效果就越好。在传统戏曲舞台上过多的运用过实的道具,就会使道具的符号性减弱,也就达不到了中华文化所追求的虚拟化、写意性的美感。
戏曲是古老而又面向未来的艺术,如何在戏曲发展的过程中保存戏曲道具个性和特性的传承,扬长避短、顺应时代要求的创新是其生命力所在。这就如同任何艺术都需要发展创新,但不管如何创造,终归是不能离开道具所具有符号性特点中所体现出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