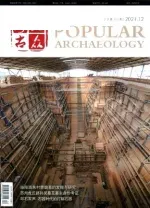黄土、考古与中国文化
文/曹兵武

曹兵武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学部毕业,是中国首位环境考古学方向硕士。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工作,从事过水下考古、田野考古、环境考古、文博管理、编辑等不同的职业,现任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考古学:追寻人类遗失的过去》、《考古与文化》、《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踏古寻幽》等,另主持翻译了《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生于黄土地,长于黄土地,小时候却从没有认真地观察过黄土地、思考过黄土地,而重新发现和认识黄土地,则是在从事考古工作之后了。
1988年,我从一所南国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以后,在参观、发掘过一些南方红土地上的考古遗址之后,第一次以考古学家的身份,重新走进了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工作后的第一个工地是在一个名曰古城的地方。那是一个坐落在中条山深处黄河岸边的小镇,历史上曾经长期作过山西垣曲的县城。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说,这里不能算是一个小地方。汽车从晋南的历史名城侯马出发,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四五个小时,才把我们这几个北京来客送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下了车,抬头四望,周围全是高山,唯一的缺口就是从西向东黄河穿流于群山之中的那条狭谷。黄河的水紧贴着两边陡峭的山壁流过。而在一条小溪注入黄河的交界之处,有一块不大的黄土台地,就是古城的所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先人在这儿留下了一座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雄伟的城堡。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佟伟华女士的带领下,一群年轻的考古学家要对这里进行系统发掘。
看着那熟悉又陌生的黄土,猜想着地底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文物和遗迹,真是一件奇异的事情。
我们一帮人在这儿安营扎寨,一干多年。后边的考古成果,也早已为业界所知。
从此以后,我和黄土地的考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少次,我们在沟壑地边寻找古代遗址的线索,希望古代袒露埋藏多年的秘密;多少次,亲眼看到随着自己的一声令下,农民兄弟用飞快的利刃斩倒绿油油的禾苗,我们在新鲜芳香的泥土中布置下发掘的探方,心中总有一阵阵的惆怅。但是,这种惆怅很快就被发现的喜悦所替代。黄土地,这块千年万年生养了中国古老文化及其文明的母土,掩埋的古代遗址几乎比现代的村庄还要密集。常有的情况是,较晚的村子把较早的村子破坏了,就地建立起新的村子;后来,更晚的村子破坏了更早的聚落,而现代的村子则叠压着所有的废墟。一个遗址,从古到今的堆积,往往要深到几米。农民们快快乐乐地跳进我们早已规划好的方方正正的探方里,他们的头消失在看不见的地平线下,而一铲一铲的黄土被从地底下甩上来,秘密和惊讶也就一个跟一个地暴露出来。
1990年的初夏,为了在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区内寻找一个适于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最后选择了河南渑池的班村),以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倡导的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的试验场所,我和几位同事驱车从郑州到三门峡,在群山以及山间的盆地和河谷沟叉中往来穿梭,几乎踏遍了这段区间内黄河岸边的每一处古代的遗址。这一带从地貌上应该属于黄土高原的东南缘,在距今200多万年以前的第四纪,呼啸的北风从漠北戈壁将沙尘源源不断地运来,像天女散花一样将沙尘匀称地洒在古老的地台上,又经过河流的冲刷切割和搬运堆积,山间河谷几乎都是厚厚的黄土台地,它们就是古老文化遗址繁荣的土地基础。好几次,汽车于炎炎的盛午穿行在千年万年里流水切割出来的黄土沟沟中,那几十、上百米厚的黄土堆积,刀劈斧削般耸立在眼前。我觉得,在这一瞬间,黄土地真是将自己彻底地暴露给了我们。它身上的层层堆积,经过雨水的不断刷新,直裸而鲜艳,一道一道地积满了岁月的尘垢和沧桑,任我们的眼睛在午间毒辣辣的阳光下恣意打量。我们乘坐的猩红色的丰田越野汽车,就像胎儿浮动在母腹中一样,孤寂、安全而富于生命的营养。
在从洛阳去往1921年中国政府聘请的地质矿产顾问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先生掀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第一篇章的渑池县仰韶村的路上,恰恰就有这么一条黄土大沟。当汽车喘息着下了大沟,七拐八绕,又喘息着沿着陡而曲折的黄土路从另一边慢慢地浮现上来时,仰韶遗址的起伏不平的台地就已经到了眼前。整个台地被青绿色的五月的麦苗覆盖着,微风一过,满眼都是一波接一波的麦浪,黄土地的巨大的伤疤被一种丰收的希望掩在身后。而在麦田与麦田之间的地边沟坎上,仰韶与龙山文化特有的硕大的袋形灰坑、五颜六色的彩陶碎片,则不时地撞入我们的眼帘。或许是闲散的农人正在午休,村子里静寂无人,纪念仰韶发掘的巨大石碑的倾斜的阴影,随着我们的脚步在脚底下晃来晃去。一时间,藉着这阳光和影子,古代与现代,似乎完整无罅地交织在一起。
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也和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黄河浇灌的黄土地上长出黄澄澄的谷子和黍子,养育了一群黄皮肤的人;他们崇黄尚黄,以黄帝为始祖;他们的人王——历代的皇帝,也是身着黄袍,胸绣黄龙,脚登黄靴;历代王都社稷坛的五色土中,黄土总是位居中央,被其他土色所环绕。黄土地的所在,显然就是中国文化世界观中天地四方的中心。
如果以安特生1921年发掘仰韶村作为中国考古学之始,那么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通过考古学家的一锨一铲,中国的古史已经从扑朔迷离的传说时代中逐步解脱出来。商周二世已经由于殷墟、甲骨文、周原等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成为信史;夏人与夏政也由于二里头文化等的发现而接近明朗;华夏传统的源头已经经过龙山、仰韶,直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时代乃至陶器起源、农业发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故的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1911~1997年)曾经说,中国文化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上万年的文明起步,超百万年的根系”,一字一句,都是以考古学的发现作注脚的。
今天,考古学的知识通过教科书、日益迅捷的媒体,也在迅速地转化为公众的日常知识,仰韶、龙山、殷墟等古代遗址与文化,已经逐渐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由于科学发展专业化的趋向和考古学自身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由于我们面对古代时所抱持的文化态度,使得考古这门学问和公众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得考古学的知识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日常生活之间,仍然横亘着一种隔膜。古代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外在于我们,或者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像一块面团随意揉搓,模糊着国人的视线和思维。一百多年了,中国文化仍然像一叶浮萍,在古代与未来的航道上艰难地漂泊、探路,难以对准现代化的航道。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五千年文明史的轨迹,为前行的文化与心灵定位。学术的使命绝不仅仅是为人民的生活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历史也并不是一个不穿衣服的小姑娘,可以任人随意打扮。文化上的现代是历史的延续,未来是现代人从种种生存之可能性中所作的取舍;而只有历史才是人类生存可能性的宝贵库存,是一连串的经过了取舍的可能性的累积。
考古学研究是以今求古,而求古的目的是“借尸还魂”,以魂养魂。这样,考古学就不再是个别考古学家的职业,不应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点缀或者人类历史的寄生虫,而应是全体人类的一种精神体操。通过这样的操练,人类凿通时空的局限,扩展了自己的视域。当代人类面对未来的抉择,就不再是孤独而艰难的尝试和冒进。从这一点上说,历史确保了未来,人类获得了自己独有的历史品性。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向黄土地的深处求索,那里掩埋着我们整个民族的秘密。A

俞伟超在渑池班村遗址的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曹兵武 张建林 李秀国 裴安平 姜捷俞伟超 王建新 张广如 )渑池班村遗址是一处涵盖新石器时代、战国、唐宋时期,出土器物丰富的大型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 。发掘工作从1992年开始由俞伟超先生主持,一直持续到1999年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