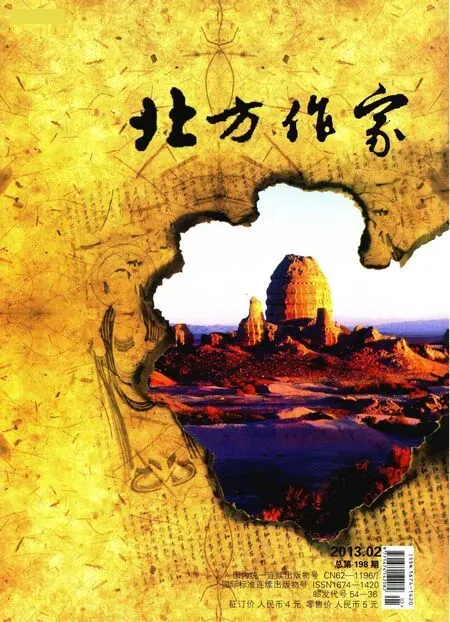黑母熊
甘肃肃南达隆东智(裕固族)
黑母熊
甘肃肃南达隆东智(裕固族)
一
塔克依然怀旧和伤感,可悲的是黑母熊失去了它的伙伴公熊,与仅剩的两只小熊相依为命。他知道,黑母熊常卧在那棵脱了皮的苍老的大树下。树皮被太阳晒得枯黄枯黄的,泛出灰白的光泽,又被它撕烂后铺在毛茸茸的身下,泛出野性的腥臭和土气味。那棵血红的大树,是图尔巴斯山上最大的皂荚树,红彤彤的果子被黑母熊食光,叶子被风吹散,树杆和枝子上挂满莹莹雪花。
那一晚,风呼啦啦地吹着,老天爷把一场大雪降到塔克的冬营地。从黑漆漆的夜里传来了砰砰的两声枪响,公熊被露宿的猎人疯狂捕杀。黑母熊从皑皑的山峦中打着尖啸般的响鼻走来,雪被踩得咯吱吱地响,林子里噼里啪啦像捅破了天一样。那是塔克的旧营地,有稀稀的牛羊粪,有缠绵的青草被风雪掠过慢慢的橙黄。黑母熊走的是旧营地的小径,是千百个昼夜闯荡过的林地,在塔克的心里真真切切,没有一丝噪音,只有风中传来的响鼻声,伴着迷失方向的雁鸣声擦帐而过,让他在冷飕飕的帐篷里彻夜难眠。
那个疾风吹着雪花弥漫的夜晚,黑母熊掠着一股猎猎的劲风,踏着脆亮的雪地“咯吱,咯吱”地蹒跚而来,羊群被哗哗哗地惊走,乳牛群哞叫着围在一起。塔克掀起门帘,打亮电筒,只见黑母熊甩着一地长鬃长毛,晃晃悠悠地从旧营地走来,毫不在乎黄褐色公狗的吠叫,漠然徘徊在黑漆漆的夜里。夜半,黑母熊的伙伴公熊在飕飕的风中,打着惊天的响鼻,慢慢的撇开羊群直奔旧营地,鬃毛上沾染着黏糊的血迹,腋窝下拖着一只白绒绒的绵羊。突然,一阵风掠过旧营地,响起了群牛的哞叫。在离塔克帐篷不远处,砰,砰的两声枪响,塔克焦虑不安地从冰凉的皮被里爬起,公熊嗷嗷地嗥叫了几声,轰隆的好像撞倒什么物件。然后,又悄无声息。
凌晨,塔克骑着白玉肚马,跌跌撞撞地向着昨晚公熊嗥叫的方向驰去,迎风吹来一股血腥气和粪便味。他老远看见公熊倒在皑皑的雪野中,像一颗磐石落在旧营地南面的柏树台上。塔克发现,公熊是被过路的猎人用英式土枪捕杀的,是被猎人选中的柏树台走向北面的小径支起枪,枪口对准猎物的腋窝,将一股马尾巴毛拧成的绳子紧绷在野兽的去路上,又将另一端拴在猎枪的扳机上,用猎人自己的步子丈量了尺度。是公熊的爪掌揽在绳子上碰发了扳机,子弹从毛茸茸的腋窝里击穿,血从尖嘴中喷出,又染红了白绒绒的胸口。公熊四肢隆起,鬃毛落地,被开腔刨肚后切走了熊胆,雪中淤了一地殷红的血迹,熊掌也被割走了,绒毛被血黏糊在风中吹起。
塔克望着蔚蓝色的苍穹,心里无限惆怅,语气苍白地说,图尔巴斯山上还没有这么差劲的猎人,是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捕杀了公熊?就在那一晚那一刻,塔克就听见从图尔巴斯山脉的北方,一股苍凉的声音飘来,嗷嗷地嚎叫了两声,像一阵酷烈的风吹呼着,穿过柏树林阳坡的墨褐色土洼,穿过那片血红的皂荚林,又穿响在布满柴垛和牛粪堆的旧营地。塔克毫不犹豫地意识到,那一声踏破林地的声音,是来自图尔巴斯山脉上空远古的天籁之音,是来自那片血红皂荚林里黑母熊乳白色绒绒嘴唇。它是从风中嗅到公熊的汗气,从雪中嗅到血腥和土气味后疯狂而来的;是听到秃鹫和黑鸟在空中的呼啸,是循着远方传来乌鸦和喜鹊的鸣叫声,是迎着塔克旧营地依稀传来群牛刨着血地的哞叫而来的。黑母熊的嗥叫声慢慢地从阳坡的柏树洼地传来,踩着雪地咯吱咯吱地响开,偶尔传来枝丫和灌木噼噼啪啪的折断声。突然,轰隆一声巨响,那只黑母熊从柏树洼地中飞奔而来,刨挖着黑洼地的冻土,用巨爪将一棵棵大树刨挖,又嗷嗷地嗥叫了几声,将一棵大树连根拔起,黑母熊的嗥叫声和树枝的折断声轰响在一起,穿响了林子和旧营地上空,连空中飞旋的秃鹫和黑鸟也被惊飞。又轰隆一声,黑母熊连树一起倒在离公熊不远的柏树台上,飞起了一股尘土和碎柴片,黑母熊从木头噼里啪啦的响声中爬起,抖动着长鬃长毛,径直地向公熊的尸体走去,它一边迈步,一面边用前爪刨起地上的土坯和碎柴,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又低头喘着粗气嗅着公熊的血气和肉腥味。
塔克知道,那只黑母熊的长鬃长毛里隐藏着一种天籁的血性,与土黄色的山林融为黑红色,像皂荚树林泛起红彤彤的光泽,敷着一身黄色土坯以及柏树枝条和纷乱的杂草,与母熊浑厚的汗气和血性的内力融为一体。它和那只公熊刚刚来到图尔巴斯山上时,皂荚树林是一片稀稀疏疏的小树,有的树还没有它们高大,枝丫只长叶子不结果子,还没有长出一棵荀子木来。它们一起去芳草地捕捉直立行走的旱獭,一起去拾山坡上的草莓和野果。
后来,那两只小熊在一场苍茫的大雪中失踪。有人猜测,它们离开了图尔巴斯腹地,还有人猜测,它们根本就没有躲过猎人们的劫杀。黑母熊依然像沟壑里的江河一样咆哮,向苍茫的图尔巴斯山嚎叫,为了寻找幼崽,黑母熊一路摇翻了多少棵树,撕落了多少条枝叶,唯独它没有撕碎和刨动那片血红的皂荚林。
那一刻,黑母熊没有多少力气,它摇翻了好几棵大树,又声嘶力竭的嗥叫着,有气无力地用毛茸茸的舌头舔着公熊血淋淋的尸体,不断的嗅着那股土气和血腥味。面对哞叫的群牛和刨蹄的白玉肚马,还有塔克,它没有忧郁和畏惧,而是猛然抬起沉重的头颅,用厚重的眼神凝望了片刻,又转身径直地走了,风猎呼呼的吹着它雄风的长鬃长毛。
二
黑母熊离开了它的依存伙伴公熊被猎杀的旧营地,独自走进了那片茂密的皂荚树林,它没有去悠悠芳草地捕猎,更没有刨挖柏树洼地里的厥麻。它听不到大雁的飞鸣声,以及雄鹿雄风的鸣叫声,只等待叶落和草黄的节气。那是一场大雪落完后,它才去了那棵苍老的大树底下的土洞里冬眠。黑母熊听到的是那股雪水河被风吹起浪花发出潺潺的声音,比秋天的水声柔弱而又静宁,水流过崎岖的沟壑有气无力,又哗哗哗地淌着。
黑母熊有气无力地卧在那棵苍树下,静静地等待着那场大雪的吹落。在寒风飒飒,大雪飘落的时刻,它的周围是一片狼藉和荒凉,皂荚树的叶子被风吹起,野果被秋后的一场大雪打落,由火红变为金黄色。经不起风吹雪落的枝丫被折断,柔软的牧草变得干枯,黑母熊凭着肥壮的身体和无穷的气力,熬过了秋后的时光,等到了最后的一场大雪。那场大雪伴着一股猎猎的劲风呼啸;是带着一阵雄鹿狂放的鸣叫和林间抵架的撞击声飘零;是一簌簌野花凋谢后被风吹起的香气飘零;是一只只离群的大雁飞过落雪的柏树又飞往原地,发出刺耳碎心的声音而落地;是一群群从远处迁徙的大角岩羊迎着暮色而来的。风吹起黑母熊的长鬃长毛,又听到大雪落地的声音,一个恐怖而奇异的声音在黑母熊毛茸茸的耳边响起。它意识到,苍茫的草地就要封冻,溶入睡眠似的静态,一股风吹来的雪簌簌的落在黑母熊的长鬃长毛上,淤着冷气慢慢的结成盈盈冰晶,冻结在母熊的鬃毛上。黑母熊纹丝不动地趴在大树下的洞口,用两个熊掌托着下巴,鼻孔里喘着白乎乎的热气又发出鼻鼾声,像吹散周围的树枝和枯叶,头皮笨重地耷拉在眼睛上,乳白色的鼻头好似嗅到了冻土的气味。突然,黑母熊意识到,一股风向在它的前方吹呼,绒毛被吹散,身体被冷却,再不进入洞穴,有可能被残雪和疾风吞噬。一股风吹雪落地的尖啸声又在母熊的耳边呼啦啦、唰唰地吹响,黑母熊胀起内力又鼓足勇气,猛然起身从容地走进洞穴,走时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背后呼出一股白雾般的哈气,像一层白露露的霜凝结在洞口。
春天,图尔巴斯山上的积雪融化,冰河解冻,塔克依然没有发现黑母熊的踪迹。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饥饿发疯的老鹰像旋风似的飞往高空,又顺着山势落到地上,剑一样的目光盯着守护的羔羊。那些直立行走的旱獭,像冬天的野草一样金黄,从口角中呼出白露露的哈气,在风中发出猛烈的呼啸。那一颗发黑油腻的石子下,有一团墨黑色的蛇群盘缠着,塔克知道那是从梦睡的冬眠中醒来后第一次在风地里交尾。是几十条蛇在同一刻交尾。在此时此刻,塔克的脑海里应验了祖父的一句话,老鹰、黑熊、旱獭、蛇以及所有冬眠的动物同一天出眠,同一刻蠕蠕而动,偶尔黑熊跟其他动物出眠得早一些,但奇异的是那天没有见到黑母熊的踪影。
三
那一年春天,塔克骑着白玉肚马爬上了一座山岗,一股烈烈的疾风吹落了飘飘然的大雪,风中的黑母熊嗷嗷地嗥叫着,踩着脆亮的积雪,咯吱咯吱地向着塔克走来,他谨慎的勒住白玉肚马,立在银白的雪地里向四处张望,一串串雪花唰唰的从树上掉落到地下,又溅起一簌水花,在苍郁的树下发出淡青色光芒。
黑母熊虎视眈眈的坐在塔克前方的路上,好似向冥冥中的塔克示威,从迎面吹来熊的土气和血腥味,有一种恐怖的窒息扑面而来,身临其境的塔克在此时此刻好像有一种天籁的勇气浑身烧燃,他没有退却,没有畏惧,反而燃着一股雄风的威力。他既没有下马,也没有从宽广的肩上挎下烟气熏黑的猎枪,他依然气昂昂地骑在马背上,一动也不动地看着黑母熊。那只黑母熊像饥饿发疯的秃鹫,目光锐利剑一样的盯着塔克和白玉肚马,它毫不示弱又泰然自若的坐在银白的地下,又嗷嗷地嗥叫了几声。白玉肚马呼呼地打着响亮的喷嚏,噘着嚼子用前蹄刨着银白的雪地。塔克今天没有功夫跟黑母熊较劲,也不想伤害它,更不想惊动它刚刚产下的幼崽,它也许还在那个冬眠的土洞里呼呼的鼾睡,也许趴在洞穴里托着厚重的眼皮微微盹醒,也许拖着黑茸茸的长毛从洞里爬出来,又踩着银白的雪地卧在红茸茸的皂荚树下。总之,在塔克的心里很茫然又伤感,一种灰蒙蒙的失落感在吹落的雪中涌起。
每次路过那片皂荚林他都会撞上黑母熊,那只黑母熊就气势汹汹地看着他,有时候呲牙咧嘴地呼出白乎乎的哈气,锐利的眼神里敷满杀戮,好像是塔克劫杀了它的两只小熊一样。
黑母熊依然坐在大路的中间,迎着皑皑的雪地,嗷嗷地嗥叫着,塔克在无可奈何时急中生智,一转身摸着铮亮的枪机拔出火捻,又随手点燃了火捻,像一股炊烟在风中袅袅升燃。黑母熊看着一股蓝烟在马背上升起,又从吹来的风中嗅到了烟气,但它没有一丝反应,反而大摇大摆地来到路中心靠近了塔克。
塔克知道那只黑母熊的威力和分量,是图尔巴斯山中最狰狞最凶猛的一只母熊,图尔巴斯的马曾被它吃的所剩无几;是一只苍宗苍毛的黑母熊,它的鬃毛像一根根细长的绳子拖到地下,又随着烈烈的劲风甩在刀一样的脊梁上,像雄性的狮子迎风而逝。它和褐色公熊走路在一起,捕猎同时行动,从不单独捕猎,偶尔和其它黑熊在血红的皂荚树林里撞一撞,但它们互不干扰,也互不撕咬,碰见时也不呲牙咧嘴,相互僵持的对视几分钟,又毫无回头径直地各自走去。
图尔巴斯山上的所有猎物都好像没有防备,像他背着空洞洞的猎枪,若无所思的只是不停的巡回,不停的望眼四方。那天的黑母熊也好像意识到,塔克不是来捕猎的,是寻找那只它们曾在一起的褐色公熊,因为在塔克走来的一路上,听不到砰砰地枪声,也嗅不到火药和烟气味,更看不到峰峦上飞旋的秃鹫和黑鸟,也听不到乌鸦和喜鹊的鸣叫。褐色公熊和黑母熊也不在乎塔克背的是空洞洞的猎枪,骑的是如风的白玉肚马,莫非给图尔巴斯山又雄风来了。所以,公熊和黑母熊对塔克毫无防备和畏惧。依塔克的个性和母性的善良,始终不想伤害那么多的生灵,和往常一样,背着一只带枪叉子的没有火药没有子弹塞紧枪口的火枪,既使有火药有子弹,他也不会放一枪。
那天,他的目标只对准一个,想看看黑母熊新产的幼崽,他不想跟任何猎物发生冲突和纠缠,尤其是那只黑母熊,虽然那年塔克的银鬃白马在一场大雪中被它咬伤,如今,在通往那片血红的皂荚树林的路途和它相遇,他依然会放下自己的猎枪,让开通行道走自己的路。
塔克和黑母熊对视了几十分钟后,它又嗷嗷地嗥叫起来,好似向塔克和白玉肚马实施它的神力和威风。塔克知道黑母熊是不会让开通行的道路,似乎两眼发出蓝幽幽的环光,被呼呼的风吹起绒绒的苍宗苍毛,落在平直的脊梁上又吹落在银白的地下,毛茸茸的舌头耷拉在下颚上呼出白露露的哈气。此时的塔克无可奈何,只能勒马向后移动,向左侧指示着马让开了一条通行的路。黑母熊也好像挪动了身体,抬起厚重的眼皮从右面慢慢闪开。
四
塔克心急如火地直奔那片皂荚林子,这是黑母熊失踪了几个月后,塔克独自一人去寻找,锐利的眼神只看着前方的皑皑雪地,风中的白玉肚马打着惊天的喷嚏。那一片曾经是血性的土地,是那头公熊和黑母熊的天然巢窝,是他们相互依存的藏身之地,多少年来无论是雄鹿鸣叫的时刻,还是大雁飞鸣的风吹飘零时节,血红的皂荚树林依然是公熊和黑母熊的出没之地,它们依赖于下大雪吹着烈烈的风,依赖于呼啦啦的风把皂荚树吹的东倒西倾,一次又一次吹落了红红的叶子,在莹莹雪花的娇容下吹红了野果。公熊和黑母熊不停地食着红彤彤的野果,捕捉着金黄的像野草一样的旱獭,才默默无闻的进入了冬眠。
塔克依然怀旧的走近那片血红的皂荚林,仔细观察着黑母熊的动静。但他看见的是被白雪覆盖下的、像穿着厚茸茸的皮袄式的皂荚树。皂荚树血红的叶子虽然被风吹落,但红彤彤的果实依然枯萎在分叉的枝丫上,像披着飘乎乎的纱巾一样随风摇曳,银白的雪花唰唰的打在地上。塔克痴呆呆的望着又蹁跚走进林子里,从上到下仔细的搜寻着黑母熊,也许黑母熊已经出眠了,有踏破积雪和撕碎树皮的痕迹,还有新产的粪便,但一一被皑皑的积雪淹没了。在塔克看来这里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也没有动物走动的痕迹,连飞鸟落下的痕迹和鸣声也没有,这可能是一次又一次雪落的缘故吧。哎,塔克,突然想起来了,除了黑母熊,还不是有一只小熊吗?自从公熊被那些可恶的猎人们捕杀后,他一直心里焦虑不安,愤愤不平。无论是骑马奔向山岗,还是徒步走进雪地,他无时无刻的寻找那帮无耻的猎人,想寻找他们的下落和部族,以及射杀公熊的那支猎枪,茫然给老公熊讨回一个不明不白死去的公道。
在塔克的狩猎营生中,他从来没有和猎物敌对过,也没有把猎物当做某一次狩猎的战利品,而是把自己放在天籁的竞争中,和猎物在等同的条件下展开公平的搏杀,是一次天性智慧的较量,在一次冥冥搏斗中增加勇气和野心。塔克之所以和公熊、黑母熊以及所有黑熊从出其不意的搏杀,一次次狩猎场风吹雪落似的咆哮和嚎叫,最后化为冥冥之中的好朋友,都是图尔巴斯那座天籁的山峰和静静的沟壑赋予了他们的天性,让塔克和它们在风雪交加的季节里,和迷失方向的雁叫声融为一体。塔克憎恨那帮可恶的猎人的原因,是用不正当的狩猎手段捕杀了老公熊,这对老公熊是惨烈的,不公平的。
塔克仔细地搜寻了那一片皂荚林,就连每一个猫耳洞,每一棵树底都没有放过。塔克埋怨自己,怨自己在捕杀老公熊时,黑母熊嗷嗷地嗥叫过,在飕飕的风中带着被折断的枝丫和碎柴片,皑皑雪地里声嘶力竭的打着惊天的嗥叫,呼出白雾一样的哈气,嗅着惨烈的血腥的老公熊,又慢慢的靠着浑厚的内力和野性十足地气力返回卧地。但塔克没有留心没有去追寻,他不会畏惧也不会胆怯,只是想给黑母熊一个平静而又庄重的归宿,让它暂时避免一场血淋淋的杀戮。塔克恨自己当时没有跟着黑母熊的血腥足迹寻踪它的卧地,今天他也没有理由不去寻找黑母熊的下落,更没有理由放弃其它黑熊的挑衅,既是背着空洞洞的没有火药没有子弹的火枪,也要跟它们周旋到底。但他寻找怀崽的黑母熊,失去了一次做猎人的机会,那个柔性怀旧的怜悯油然而生,像骨子里永恒的铁青血迹,流穿了塔克忧郁的心灵。突然,塔克在茫然中发现了一丝丝踪迹,他仔细一揣摩是一只小熊的点点爪印,在被白雪覆盖着血红皂荚林中显现得足以清晰。塔克在想,它们也和他一样焦虑不安,苦苦的等待积雪融化的时机,很可能嗅到了一股土黄色的气味,也可能在飕飕的风中听到了黑母熊浑厚的鼻鼾声,也许跟皑皑的大地有关,和云雾一样的呼呼哈气相随,那一股气味又无声无息的扑面而来。也许黑母熊已经到了产崽的季节,它从湿气泛滥的洞穴中蹒跚而出,是前所未有的难产之祸,向空旷的图尔巴斯山脉嚎叫,向沟壑深深处呜咽它的痛楚。
塔克依然循着小熊的足迹在苦苦的寻找母熊,他知道黑母熊是不寻常的,是独立不羁的,是图尔巴斯山脉中任何一只熊也无法比试,它在塔克的心里是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自从失去了老公熊后,塔克变的极为孤独和忧虑,那种忧虑深深的缠绕着他,这是他的天性。
一股呼呼的风打破了他冥冥中苦苦寻找的思路,他茫然发现在离他不远的一棵颇大的皂荚树下,呈现了一口黑魆魆的洞穴。一霎那,那个洞口里有母熊踩踏的踪迹。塔克谨慎的向洞穴走去,走着走着在他的脑海了出现一股魔幻般的映像。那一年的黑母熊在老公熊的怀抱里依偎着,在风雪打落枝叶的那一刻,黑母熊厚重的头皮耷拉在黑绒绒的眼睛上,浑身散发着雌性的土气味和臊腥气,伸展着笔直的前臂,白花花的窝腋柔软而富有弹性,大部分地方没有绒毛,它在呼呼的风中呼出白气。那一次,黑母熊在声嘶力竭的产仔,没有嚎啕声只有吱吱的呻吟。突然,他看见白皑皑的洞口里,被乱纷纷的枝条封着的缝隙中呼出白露露的一股哈气,风中飘来一股强烈的骚气味,发出一丝血腥和肚粪味。塔克知道,黑母熊也许已临产了,好像在他的耳际传来吱吱吱吱的声音,是从那片苍郁的皂荚林中传来,声音愈传愈大,让塔克感觉到从没有过的陌生,他胆怯黑母熊有窒息和生死未卜的恐怖,扑面而来的风冷飕飕的,让他忐忑不安。
塔克不停地在寻找黑母熊的下落,他在雪地里迎着风打着喷嚏,有气无力的低着头向图尔巴斯的顶峰径直地走去。
五
在他的脑海里依然是那只孤零零的最后一只母熊,它是图尔巴斯山上唯一存活下来的母熊,在塔克忧郁的目光里是一只勇猛的公熊。自从老公熊被捕杀后,那块铺满芳草的旧营地的厥麻荡然无存,没有一丝被挖破的痕迹。在夜里,只有吹呼的风和落地的雪,听到的只是群牛喘长气的声音,偶尔有一两次牧羊犬的吠叫。塔克觉得旧营地无比宁静,无比荒凉,听不到野狼的嗥叫,听不到黑母熊呼呼的鼾声和随风传来的响鼻声。夜半,塔克盖着冰凉的皮被,扑哧扑哧地抽着鹰翅骨烟锅,冒着青青的烟雾,仿佛在等待黑母熊的到来,然而,等待他的只是宁静的夜和寒气通没的旧营地。昨天,他发现黑母熊和公熊在没有落雪和风吹的地方活动的踪迹,有黑母熊踏破掌心的血流痕迹,有枝丫被折断和它的绒毛被缠绕的踪迹,有母熊和公熊的粪便,这些都是往年出没的痕迹。塔克记忆犹新,他从小就跟随祖父经历了狩猎的场面,了解过好多黑熊的来龙去脉。在他的记忆里那对强悍的母熊和公熊没有那么恐怖和令人畏惧,在它们出没的范围内,塔克和邻居的畜群始终没有受到侵害。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那就是黑母熊雄踞多年的那片火红的皂荚林,一年四季,青了又红,红了又黄,从来没有听到过黑母熊和狼厮杀羊群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