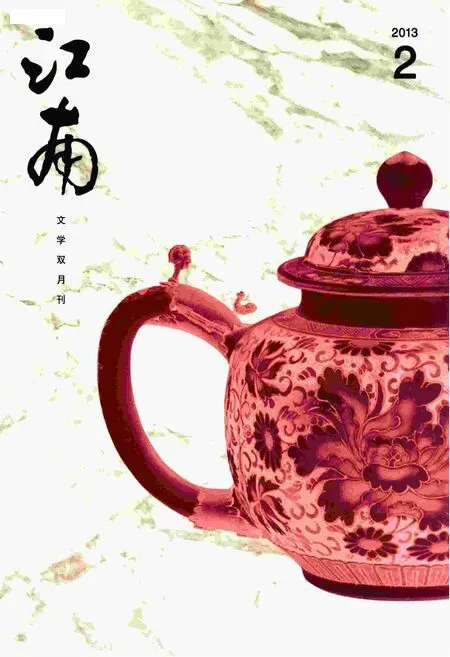文学与远方——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宁 肯
【近日,复旦大学举行了宁肯作品学术研讨会,京沪两地学者批评家针对宁肯新世纪来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就独特性、城市、感性与智性等一些话题进行了研讨。宁肯早年在“朦胧诗”影响下写诗,1982年上大学期间在上海发表了处女作,后转入散文创作,系上世纪九十年代“新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新世纪以来,宁肯一系列长篇小说的问世,给强大的“乡土文学”占主导的文坛吹来一股都市与异域交互写作的异质之风。
讨论会上所有批评家都谈到了宁肯的独特性,认为宁肯的创作虽然一直在文学主潮之外,但内在气质与异质风格让人感到他越来越强大地存在。复旦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称宁肯是一个介入精神痛苦的作家,“小说里的人物对历史的剧痛守口如瓶,却五内俱焚。正是这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导致了整个小说叙事十分特别,与众不同,读起来就像是一场巨大的梦魇,似真似幻,闪烁其词,构成猜谜似的叙事特点。”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则用了“文坛的刺客”形容宁肯,“他的小说太特殊了,和谁都不一样,他的东西都有鲜明的自己的印记,就像刺客一样。他用刀雕刻了我们这一代人骨髓的感觉,那种痛感,为汉语小说提供了高度和境界,提供了很多前卫的经验,同时留给我们很多的问题,城市怎么书写?刺客式的写法无疑是一种。”《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用“孤岛写作”一词形容宁肯,“他的写作太特殊了,他的每一部作品读过之后还想再读第二遍,读完感觉还很不同,是一种典型的智性写作。通过写作他构成了自己的巨大的建筑,某种意义,他在孤岛上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立他的玛雅预言。”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惊异于宁肯把北京话写得像诗一样,“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宁肯其实还是一个诗人,不过是一个躲在小说背后的诗人。这里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主体的东西、语言的东西、作家和时代的东西。”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发现,“宁肯的小说世界总是大于他自己,因此他的小说空间显得特别的大,《天·藏》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无限的小说。叙述上既使你要读下去,又使你要停下来,这是读别的小说所没有的,这也是智性写作的特征之一。”
批评家也有交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提醒宁肯,精神体的长篇小说往往具有危险性,会沉溺于理性。而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则认为宁肯智性得还不够,在字里行间可以呼吸到,但还不够强大,不够饱满,还有现实泥泞的纠缠。
按照复旦大学的传统,研讨前一天宁肯做了《文学与远方》的讲演。】
诗人杨炼写过一首诗,在大海停止之处,眺望自己出海。这两句诗很有意思,什么是大海停止之处?大海会停止吗?毫无疑问,世界任何一个海边,哪怕是一个伸向内陆的小小的港湾,都可看作是大海的停止之处。为什么不说海边,非说停止之处,这就是诗的表达。诗歌的语言是一种增殖的语言,停止一词使海边这个词动起来,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反向的意义,即开始。也就是说,当它说出大海停止之处的时候,也说出大海开始之处。这就是语言的增殖。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要站在“大海开始之处”呢?当然是为了眺望。
眺望自己出海,虽然只有六个字,含义却越发丰富。眺望是一个很普通的词,眺望远方,眺望大海,这都很好理解,很常见,但眺望自己,而且还眺望自己出海,这可能吗?眺望是主体,自己也是主体,一个人能眺望自己吗?当然能,当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客体的时候,一个他者的时候。把自己当成一个客体是心理常有的现象,这时自己和大海都成了客体,同时大海也就有了主体的意义。这里的海当然不仅仅是实有的海,它还指代了远方,象征了希望、未来。它是想象与幻想的平台,诗与白日梦的平台。某种意义你站在大海边上,当你意识到大海既是结束也是开始时,当你把自己当作他者的时候,就是在书写,就是在叙事,就是讲述自己。
就像停止就是开始一样,眺望自己出海实际也隐含眺望自己归来。当你是一个少年,你眺望的是自己出海,憧憬自己人生的开始,走向远方,这时未来什么样只能幻想,一切都还未知,但是当你眺望自己归来,你已经历了许多,你年近中年,百感交集,这时你再站在大海边上是什么心情?这时你虽然还不是作家,但已是一个隐含的作家,这就是文学与远方的内在关系。
下面我就讲讲我的出发与我的归来,从中你们可以看出文学与远方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我是何时出发的?或者说一个人是何时出发?某种意义,人从他一降生就是一种出发,所以我有一个观点,童年也是一个人的远方,当你回忆你就是在眺望远方。因此即使你从未离开过故土,你同样也有一个远方,这个我后面可能还要讲到。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北京,生活在胡同里,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要想走出我们的那条胡同都是一件不容易事,我记得那条胡同的尽头是琉璃厂胡同,琉璃厂胡同又分为西琉璃厂与东琉璃厂,中间隔着一条南北方向的新华街,东琉璃厂胡同的尽头是大栅栏,大栅栏的尽头是另一条南北向的前门大街,这一连串的胡同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是相当漫长而又迷人的,我记得大概是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才第一次走完了它。
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对胡同远方的穿越有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每次归来我都像是一个从远方归来的人。我看熟悉的街巷越来越近,就像游泳者看到了桅杆,船上的人看到陆地,那种激动深深沉淀在我的记忆里,让我从小就对远方有一种特别的快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远方越来越近,那事实上很近的远方已远远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记得就在我刚上初中不久的某个寒假,我专门打了一张月票,开始了我独自的乘公共汽车的旅行。那是一种美妙的心理活动异常丰富的旅程,首先因为免除买票,想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我有一种特别的骄傲与放松,快到总站查票时我甚至装作是一个逃票者,结果最后我神奇地变出了一张月票,我喜欢售票员大妈那恼火的一瞪,我觉得特别满足。另外,相对于以往徒步穿越胡同,汽车带给我的远方完全不同,胡同消失了,我到了宽广的大街上,看到高大陌生的建筑,穿过市中心,到了这个城真正的远方。那时北京出了二环路差不多就是郊外景象,我看到了河流、庄稼地、地平线上的远山,我非常恐惧,尽管理智上知道是安全的,我坐到头后也就是坐到总站后可以再坐回来,我有月票,这毫无问题。这是理智,但情感决不会因为理智存在就不滋生恐惧或恐惧性的想象,我不知道公共汽车会把我带向何方,它有没有尽头,它的尽头也许是悬崖,也许是一条大河,也许一下开到地底下去。恐惧的战栗让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场本来是好奇的旅行变成了一场越来越惊恐的旅行,但是售票员一查票我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知道要到站了,我要返回了,立刻装作没票,上演恶作剧,转换之快如同故事、戏剧。
这是七十年代一个十五岁少年真实的故事,这个乘公共汽车旅行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旅行的过程是一个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他者关系的过程,而这种关系正是文学的诞生地。西班牙哲学家奥德嘉·嘉塞曾经说过:“告诉我你关注的地方,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往往是通过自己关注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不论我们将注意力投向何方,我们都会被它塑造。你关注远方,远方必定会塑造你;你关注旅行,旅行必定会塑造你。在这个意义上,奥德嘉·嘉塞进一步说,“人的生命本身就是有诗意的工作,人是他自己的小说家,因此生命事实上就是一种文学形式。”
然而,旅行和远方还是有些差别,远方不仅仅是行走,还是停下,是居住在一个你想居住的地方,或者你想探索的地方,甚至是被迫居住的地方。这时的变化就不再仅仅是空间的,更是时间的。这时候,你在一个陌生之地一住就是几个月,几年,甚至一生都是可能的。故乡是怎么产生的?就是由远方产生的。没有远方就没有故乡,而故乡一旦产生,便也产生了双方面的远方,即:你去的地方是远方,当你到了那里,住下来,一住就是几年,甚至一生,你的故乡也变成了远方。故乡对写作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强大的乡土文学中的乡土作家,像鲁迅,像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哪一个不是在异地写作的乡土作家?哪一个不是在远方抒写故乡?还有被迫走向远方的知青文学,像韩少功、王安忆、张承志;还有右派作家,像王蒙、张贤亮、从维熙,写了狱中,写了流放地;还有因求学由小城镇来到大城市的作家,像余华、苏童、格非,数不胜数。
我的远方和上述这些我尊敬的同行还不尽相同,我没有一个生活上的理由,也没有一个求学的理由,也没工作上的理由,更没时代的理由。我只有一个个人的理由,就是想离开。我那时渴望远方,渴望陌生,渴望一个不同的自己,渴望一个故乡,但我知道如果不离开我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故乡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单一的人,一个从不知道镜子为何物的人。我觉得故乡是一面人生的镜子,故乡与远方互为镜子,在这样的镜子中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你,还有世界;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你。你和世界隔着遥远的距离,但你和世界又是同一的。这是我当时想到的,所以我必须离开。这时已到了1984年,这种内心需求终于导致了行动。
这一年我在北京近郊的一所中学已任教了一年,学校宿舍后面是一条铁道,每个夜晚都有火车经过的声音,每次经过都提示着远方。我开始给远方写信,最远考虑到了新疆,正当我费尽周折,与新疆奎屯农屯建设兵团一所中学取得了工作上的联系,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北京组建援藏教师队,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就在这年我跳出了牢笼般的北京,飞向了无比陌生的青藏高原。这样的远方,这样的空间,超出了我的想象。巨大的陌生,巨大的遥远,可以说是登峰造极。那么,巨大的陌生,巨大的遥远,会不会创造一个巨大的我呢?或“他”呢?我当时憧憬着自己,也眺望着自己,我那时已知道了高更,知道塔希堤岛,知道高更一到陌生的塔希堤岛便画出了惊人之作。此外,八十年代知青作家非常活跃,他们为什么成功?很显然就因为他们曾有一个远方。他们的经历令人羡慕,他们的作品尽管描写的是苦难,但当苦难一旦化为文学的诗意,无形中再次让远方成为了召唤。那时我虽然已发表了一点诗歌,但感到自己生活贫瘠,我觉得到了西藏会完全不同。我觉得既然西藏不同凡响,也会让我写出不同凡响的作品,甚至是一鸣惊人的作品。我的想法应该说不错,是一个年轻人正常的想法,并且从现在来看我也确实得到了这个结果,但当初让我绝没想到的是,这一结果将要延迟了差不多二十年之久。
二十年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由少年变成中年,甚至走向老年的概念,是个眺望自己归来的概念。有人确实在出海之初,也就是一到西藏,就写出了不同凡响作品,像马丽华、马原,但我不行。艺术面对生活往往不是正面进攻,但我却是一个接受正面挑战的人。我觉得西藏高原既然是以正面的全景的方式震撼了我,我就要表达这种震撼。我希望自己像镜子那样映现出内心的持久的震撼,结果我完全消失在自己的震撼中。有时候我一时激动写出了什么,表达的只是心灵的震撼,我好像一切都写出了,但就在我落笔的时候,就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一切又都神奇地消失了。文字,刚刚还像蜜蜂一样飞舞,落在纸上却像是尸横遍野,全成了死的,干的。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直到许多年后当我听到朱哲琴的《阿姐鼓》时才明白了一道理。什么道理?就是西藏给人的震撼很像音乐给人的震憾,我们知道音乐是抽象的,诉诸感觉的,模糊的,心灵的,隐秘的,非叙事的,而西藏恰好全部有这些特征。然而,当时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我非常固执,我认为是西藏的难度导致了我内心的巨大的难度,而我又是一个不习惯绕过困难的人。我写得少,非常困难,完全停顿了,我对困难有一种执迷不悟画地为牢的精神,我非要走通困难不可,非常固执,固执到了愚笨程度。我到西藏是为写作,结果西藏反而制约了我的写作,我差不多被西藏囚禁起来。
这一囚禁就是许多年,差不多有十年,我几乎放弃了写作,放弃了西藏,但西藏却没放弃我。我记得奇迹发生在1997年的一天,那时我在北京中央一家部委报纸所办的广告公司任总经理,这家公司叫北京绿广告公司,你们上网查查现在还能查到这家公司。那天我驱车去一家饭店与一家企业老板谈一笔广告生意,车堵在了东单的银街,北京最繁华之地。我驾驶的是一辆法国雪铁龙,原是为越野的,现在却陷入泥淖。饭店已近在咫尺,可我却无法抵达。事情就发生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我的车经过一家装潢考究的音像店,附近还有一两家,同时放着嚎叫混乱的歌唱。正在这时,我在交通噪声和混乱歌唱中听到了一脉高原的清音,我当时不知是《阿姐鼓》,但是非常亲切,感到恍惚,感到一种迷失——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在我记事的那年她离开了家/从此我就天天天天地想/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我突然间懂得了她。这歌当时听得我可以说魂飞魄散,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觉得遥远的我要呼唤我。西藏,我曾经为了诗歌一直追寻到那里,在西藏高原整整隐居了两年。那儿的巨大的孤独和自然界的伟岸曾经塑造过我,那儿的雪山和河流磨洗过我的眼睛,二十五岁的我像淬火一样身体发蓝定型在那里,十几年来虽在商海人潮中,一切却都不曾忘记,事实上一切都魂牵梦萦。《阿姐鼓》穿越时空,十分偶然地在商海人潮中一举照亮我,我觉得身体透明,闪闪发光。
我决定回到文学上来,我像梦游一样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广告公司的职务,将账目、车钥匙以及一切的方便全部放弃。我在文字中重新回到远方,这时候再写西藏我发现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当年的写作困难奇迹般的消失了,往事纷至沓来,西藏纷至沓来。这时我再次眺望自己,已不是眺望自己出海而归来,这时大海已不再单纯,而是像3D一般有无限丰富变幻的空间。所有的鱼都向我游来,一切都身临其境,一切都信笔拈来。《阿姐鼓》专辑有七支曲子,我用感觉对位写出了七篇散文。我把它命名为《沉默的彼岸》,发表在1998年《大家》杂志的“新散文”栏目上,此前我已有六年没发表一字作品。这组散文我是亲手交给《大家》杂志编辑海男的,我清楚地记得这位另类的女诗人、小说家只是翻了翻,闻了闻,当即拍板,立刻编发。这里我把这组散文的开头几段读读,你们听听是一种什么感觉,是否我有一种刑满释放的感觉,一种归来的感觉。
这篇散文叫《漂泊》:
从无雨之河开始的漂泊与沉思,到了雪线之上突然中止了,鼓声从那里传来。正午时分,火山灰还在纷扬,鼓声已穿透阳光,布满天空,沿着所有可能的河流进入了牧场,村庄。所有的阴影都消失了,鹰从不在这时候出现,一群野鸽子正沿着河流飞翔。闭上眼,静静地躺在湿地和沼泽之中,面对天空,鼓声,阳光的羽毛。大片的鸥群从你身体上掠过,你摆着手,示意它们不要离你太近。但你的周围还是站满了鸟群,它们看着你,看着湖水,看着湖水流线型从草丛和你的身体上滑过。
一个人,躺在隆起的天地之间,有时也在刺破青天的山峰上,就像雪豹那样。那时积雪在你的体温下融化,阳光普照,原野的亮草弥漫了雪水。这些浅浅的像无数面小镜子的雪水汇成了网状的溪流,它们打着旋儿,流向不同,不断重复,随便指认一条,都可能是某条大江的源头。
不,不是所有的源头都荒凉,没有人烟。
在我的行迹中,生长着岩石,冰川,咕咕的泉水,同样,也生长出了帐篷,村庄,正午的炊烟。村庄或石头房子几乎是从岩石上发育出来的,经幡在屋脊上飘扬,风尘久远,昭示着时间之外的生命与神话,存在与昂扬。村子太旷远了,以致溪水择地而出,从许多方向穿过村庄,流向远方。桑尼的弟弟,一个三岁的男孩,站在时间之外,在没有姐姐的牵引下,那时候正走在正午的阳光里。
这是个没有方向的孩子,只是走着,时而注视一会太阳。
后面我就不读了,我简单讲一下这个三岁的男孩。来到门前一条小溪旁,小溪不过一尺宽,但自然界的提示还是不能过去,他站住了,他一无所有,于是蹲下来玩水。他没有任何玩具,手伸到小溪里,小溪流速很快,水就顺胳膊涌上身来,自然界的力量一下让他跌倒了。他的鞋湿了,他脱下了鞋,于是发现了鞋。他用小鞋舀水,站起来,倒下,就像他的姐姐汲水的情景。玩了一会或许是累了,小鞋不慎落入水中,一下顺流而下漂走了。他没有追,只是望着,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待小鞋子漂远看不见了,他蹲下来拿起另一只再次放到水上。小鞋再次漂浮,像船一样行,男孩跟着跑了几步摔倒了,再爬起来小鞋已远去。男孩看看地面,再没什么了,又看看远方,这时他简直就像一尊小铜像。男孩眼里没有迷茫,只是直瞪着,只是不解,并且无法越过的不解。他还不能思考,但思考已经孕育。
这是我住的西藏那个村子发生的一件真事,这个村子与我教书的学校一墙之隔,那所学校在拉萨的西郊,有一个倾斜的操场,几排石头房子构成的教室,周边有田野、牧场、沼泽,穿过村子和一大片山脚下的卵石滩,就到了山上的哲蚌寺。站在村子的高处或卵石滩一块高大的飞来石上可以看见拉萨河天空一样的波光。我经常在村子在寺院里面散步,远一点我会走到拉萨河的几个小支流上,或者干脆走到拉萨河边,河边有许多大大小小像浴盆一样的水湾,有时我会脱光衣服躺到里面,任水鸟鸣叫着围绕着我飞翔。
在这样的回忆中,或者说在这样的眺望中,一个漂泊者流浪者的形象已在我心中孕育成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什么样的人才能承载我感觉到的西藏?我心中的西藏?我想到了罗丹著名的雕塑作品《青铜时代》,一个走向原野瞻望未来的形象,一个人类意识初醒的形象,或者像老子所说的赤子,即婴儿之心,我觉得只有这些具有人类学形象的人才能承载我心目中的西藏。西藏是开始的地方,这个人要有开始的味道。我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我塑造了一个叫马格的人,一个来自大城市的人,一个从中心走向边缘的人,一个家境殷实却选择了流浪的人,一个拒绝一切现存秩序的人。这里我想读一下马格刚刚来到拉萨对拉萨的印象,你们看看是否和别人描述的拉萨有什么不同。这是马格经过多年流浪,初到拉萨看到拉萨的情景:
马格站在拉萨河桥上。四月,流域沉落,残雪如镜。城市在右岸上,白色的石头建筑反射着高原的强光,一直抵达北部山脉。布达拉宫幻影一样至高无上,神秘的排窗整齐而深邃,仿佛阳光中整齐的黑键,而它水中的幻影更接音乐性,更像一架管风琴的倒影。窗洞被风穿过,阳光潮水般波动,能听到它内部幽深而恢弘的蜂鸣。拉萨河静静流淌,波光潋影如一张印象派的海报。是的,这是个音乐般的城市,静物般的城市。
除了一些寺院呈出着绛红色调子,这个城市几乎是白色的,高音般的白,但细部,比如雕窗则是鲜明的黑,整个看上去明快,抒情,单纯,单纯色构成不同的色块,简单,迷人。在马格看来,这是个童年的城市,积木般的城市,他想起小时曾搭建的那些好看的城堡,想起他在钢琴上幻想的一个积木城市。但那时他无论如何没考虑过这么亮的阳光,因此这甚至是一个孩子也无法想象的城市。但白色的拉萨,又的确是一个孩子的城市,多漂亮的阳光,全世界的孩子都应在这里与阳光相聚,与河流相聚,以决定他们的城市和未来。可以有一些白发老人,比如轮椅上的老人,推婴儿车的母亲,然后全是孩子。
西藏需要一颗赤子之心、婴儿之心呈现。因为两者都是干净的,我觉得只有干净才能呈现干净,只有水才能呈现水。这部小说叫《蒙面之城》,问世于2001年,2002年获得了老舍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会上,我在简短的获奖感言上说,除了这部《蒙面之城》,我所有发表的作品加起来不过几万字。会后记者采访,为什么写得那么少?我讲了我被西藏囚禁的情况。我说我得感谢这种囚禁,没这种囚禁我不会获得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罗丹雕塑那样的形象。
《蒙面之城》问世五年之后,我又投入了另一场大规模的有关西藏的写作,再次眺望自己,眺望西藏,这就是2010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天·藏》,这部小说为我第二次获得了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如果说《蒙面之城》中的西藏还是一个局部的印象的西藏,那么《天·藏》就是一个全景式的西藏,一个音乐般的西藏,就像我刚到西藏被震撼当时却无法言说的西藏。现在我把这个小说的开头读一读,你们听听是否有全景的效果,是否有类似音乐的效果?在这个演讲即将结束之际,是否接近了西藏的本体?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开头是这样的:
我的朋友王摩看到马丁格的时候,雪已飘过那个午后。那时漫山皆白,视野干净,空无一物。在高原,我的朋友王摩说,你不知道一场雪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也许整个拉萨河都在雪中,也许还包括了部分的雅鲁藏布江,但不会再大了。一场雪覆盖不了整个高原,我的朋友王摩说,就算阳光也做不到这点,马丁格那会儿或许正看着远方或山后更远的阳光呢。事实好像的确如此,马丁格的红氆氇尽管那会儿已为大雪覆盖,尽管褶皱深处也覆满了雪,可看上去他并不在雪中。
从不同角度看,马丁格是雕塑,沉思者,他的背后是浩瀚的白色的寺院,雪,仿佛就是从那里源源不断涌出。寺院年代久远,曾盛极一时,它如此庞大地存在于同样庞大的自身的废墟中,并与废墟一同退居为色调单纯的背景。不,不是历史背景,甚至不是时间背景,仅仅是背景,正如山峰随时成为鸟儿的背景。
马丁格沉思的东西不涉及过去,或者也不指向未来,他因静止甚至使时间的钟摆停下来。他从不拥有时间,却也因此获得了无限的时间。他坐在一块凸兀的王摩曾过的飞来石上,面对山下的雪,谷地,冬天沉降的河流,草,沙洲,对岸应有的群山,山后或更远处的阳光,他在那所有的地方。
这部小说长达近四十万字,有兴趣的同学可找来读一读。
以上是我离开西藏许多年所描绘的西藏,当年我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时间。我刚才前面也提到了时间的参与,许多处也都谈到了时间。这里我想说,远方,绝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还是一个时间概念。没有时间参与的远方是一个没有生命沉淀的远方,一个走马观花的远方。为什么旅游文字通常写不好?也是因为这点。所以,我前面说我是被西藏囚禁起来,某种意义不如说是被时间囚禁起来。囚禁的意义我前面也说了,它使我的西藏变成了一个3D的西藏,立体的西藏,变成西藏本身,使我获得了一颗西藏之心,赤子之心,婴儿之心。我为远方所塑造,为时间所塑造。当年,在大海停止之处,眺望自己出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年,当我眺望自己归来时,我已是一个中年,这里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而时间与空间,毫无疑问是文学永恒的对象,是最终要抵达的那个地方。
关于我所描写的西藏,是否和别人不同,我想引用一下上海著名的批评家程德培先生一段话,他在评论《天·藏》时曾这样说道:“《天·藏》的叙述者是一位形而上的思考者。他聪明而饶舌,但给我们讲述的却是沉默的内涵;他处理过去仿佛它就是现在,处理那些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故事,好像它就在眼前。对宁肯来说‘空间’总是慷慨和仁慈的,而‘时间’总是一种不祥的情况。小说力图向我们展示一种文化的全貌,这种展示既面向我们,也面向与世隔绝的人。无论如何,《天·藏》让涉足西藏这块土地的其他作品显得颇为小家子气。”程先生这段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这也正是我所要表现的,我觉得表现西藏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慷慨的空间和一个不详的时间之中。至于说到别人的“小家子气”,我觉得似乎不该这么说,别人有别人的特点,但我理解我所追求的那种正面地全景地表达西藏的努力,程先生体会到了,我也觉得特别欣慰。我想,我得特别感谢时间,感谢时间对远方的参与,没有时间远方难以成为文学的表达。
最后我想再次提到杨炼的诗,并把这首诗送给大家:
在大海停止之处,眺望自己出海
在大海开始之处,眺望自己归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