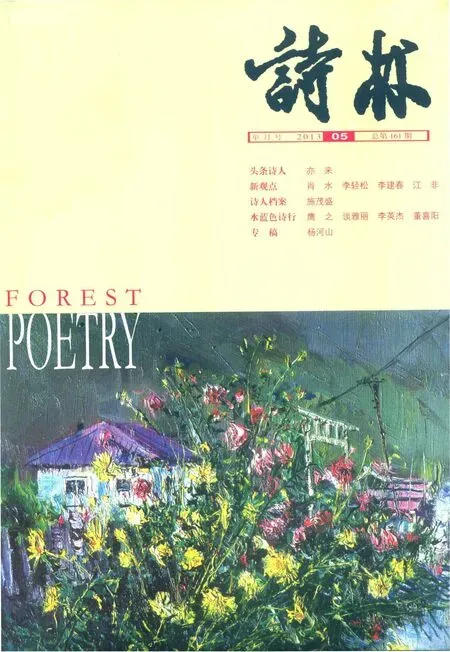辩诗录
施茂盛
玄思,令一首诗结实。
写诗用以养性。
在每首诗中,你要尽量让遐思擦亮词语,尽量让日常用语化腐朽为神奇。你要努力为词语带来冷静的旁观者,用他的眼睛看见词语的清澈。你要珍惜词语经过的歧途,它没有抵达你目力所及之处,但它的前方或许也有茂密的森林。最后,你决不能让词语陷入“正确性”的泥沼,因为,“正确性”往往就是一具僵尸。
或许有某刻的断流。但若枯竭了,他便不应算是个彻底的诗人。诗人,是在死亡降临时,仍在用诗说话的人。
庞德称他的诗篇形式是“Ideogrammic method”,译之为“意象”。我以为它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闪之念”,类似于绘画中“一个明亮的细部”。这“一闪之念”的跳跃或流动之处,又会有另一个意象出现。而我们,在阅读的联想与跳跃之中,会发现那些意象之间的联系,即诗意。日常语言之于诗歌,我以为应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若这“化腐朽”只有间离与反讽效果,而从未为我们提供过附在语言身上的本义、歧义和多义所带来的开阔与广袤空间,便无神奇可言。因这空间,正是诗之栖息地。
庞德《诗章》的独特之处是,处处皆可看出他用粗糙接近美的勇气。诗歌赖以存活的元素之一是想象力,但想象力并不是非得清澈、澄明得像雨后的空气。有时,如庞德般粗糙,更接近滂沱与磅礴的“诗歌的真实”。因为我们所耳闻目睹的“真实”,本就是混沌懵懂、泥沙俱下的。
一个人一生最有意味的工作就是拆除捆住自己的建筑,因为建筑的本质就是让人卑微。比如那位打洞的卡夫卡,他建起的堡垒是为了居守与退却,为了不至于精疲力竭地与他者对峙。所以,里尔克说得对。他说:谁现在没有房屋就别再建筑。
诗歌为我带来的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觉与立场,这是独立的,也是唯我的。我坚持在每首诗中用一个旁观者的沉潜之目和沸腾之心,去觅得这尘世仍有的情怀与悲悯。我愿意用这情怀与悲悯,收留经过我的每一座废墟。
蔬菜因自身的绝望而变得新鲜,像极了一首诗。
有时你会觉着吊诡:一首诗的来到是多么的可遇而不可求。此刻,你显得散淡得很,又为日常里的琐碎缠身。但那不可知的下一首,却突然就真的从你的呼吸里出现了。后来你看出了一点端倪,你的身体、你的感知、你的魂魄,时时被一种“诗意的觉醒”浸泡着,他们潜伏在某个角落里,随时在你停顿之处涌出。
我惧于因而很少对一首诗歌进行解读,我只表示喜欢或不喜欢。因为对一首诗歌的解读,往往是对诗人的哲学影响、文化底蕴和现实思想的解读。你不能进入诗人精神的这些层面,或者说进入不了诗人的这个精神综合体,你的解读只能是带着个人印痕的解读,是自取其乐或者又是自取其辱的解读。
本意的简洁在诗歌是毒瘤,因为诗歌的本质是繁复的、多义的,甚至是歧义的。我想,写作者的身体,四分之三是一个逃亡者的身体。剩下的四分之一,刚好让他度完漫漫一生。
诗在心灰意懒处。一首单单依赖身体而存在的诗是腐朽的。要有意绕开身体,决然向文本自身永无止境地靠近与抵达。诗歌真是个美妙的东西,它帮我抹掉了哲学与蹉跎学的界线。
一首诗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的宽容。无论它有时多么叫嚣,无论它有时多么哀怨,它甚至偶尔还有点戾气,但你都得设法让它的翅膀合拢在它的宽容之处。诗的宽容是诗的一种内力,它安抚每一个词,甚至可以让任何一个突然闯进来的词安静下来。
诗歌写作本身无关乎政治性,因为纯粹是诗人个体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诗歌需要处理它与伦理道德、美学观念、时代事件等之间的关系,所以政治性无处不在。但,若预先设置一个政治准确性的东西在,倒是另一种对这个世界丧失质疑立场和否定力量的表现了,它必然同样会造成对诗歌精神的削弱。
无论你主观上赋予诗歌多少道义,客观上它仍是一件充满着私密性的个人事件。理论上讲,躲在一座壳中写诗,与赤膊躺在青石板上写诗是一样的。外界任何响动,都不能构成一首诗偏离轨道的理由。唯有诗人自己才能阻止它前行。更多时候,连诗人都没有这种权利和能力。
一首诗最接近理想的状态是:永无边界。
我看到一些诗删去了“可能性”,而另一些诗又被“可能性”消耗殆尽。这两类诗都是缺少想象力的结果。而正是想象力,才令一首诗饱满,且有序。
只有神怪出没的乡村才是我的乡村,就像只有神明居住的诗歌才是我偏爱的诗歌一样。
整个上午,我一直想碰碰运气,能与一首诗相遇。哪怕是一首诗的一个句子,只要这个句子是能穿透我的身体并最终在我身体里住下来的。有时会想,对一首诗的遐想是要承担着消耗一生的想象力和思想之耐力的风险的。这正是诗歌对于诗人的巨大伤害,好比如时时处在“在油锅里被炸”的状态
埋伏在诗歌中精准的对峙,正是诗歌自身的平衡术。有时候,一首诗歌它最大的任务就是为了平息来自它自身的对峙,或曰敌意。唯有这“对峙”令诗歌扎实落地,否则它往往会成为飘浮在半空的气球。
口讷使我以为,诗用来默读最佳。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写诗的趣味。为了应付我口讷这个顽疾,我总是喜欢让每首诗的节奏尽量慢一点、再慢一点。
对于诗,神秘性如骰子的第七面般不可多得。
来自于长喉的“果子熟了”,仍是词语之间妥协而形成的秩序。某一时刻,词语之间的妥协将远大于万有引力。我找到一个词最能体现诗歌美学的词,它叫“厌倦”。
一首诗完成时,它背后那个不确定的读者也便从乌有中完成。我猜想他应该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触角与嗅觉的读者,所以我尽管放心让他对一首诗用他的方式读完它,直至完成“他的诗”。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必吝啬这一点,任何一个作者也都应该相信那个不确定的读者。
保持汉语的尊严仍是一个诗人的本能连这一本能都被耗尽了,那么,这个诗人离“死去”不远了。若说活着已被苍生宽恕,那是在盖上棺木那刻,听得有人在我耳旁喃喃自语:你已写出静美、大爱的诗。
每次暮晚散步,令我最为担心的是,出门后便再也记不起回来的路。这种对“是否迷路”的焦虑,一如我在每首诗中所质疑的:语言出发后,真还能返回它的源头吗?
在诗中,我看见我的思想随着诗的行进,是如此一而再地快速消逝着。而这消逝,也正是我在消逝。
大无畏的诗,它的语言必如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诗中所看到的,是从未受过逻辑与道德污染的。何为诗人?便是那个从故乡往他乡而去的人。诗人何为?便是用自故乡向他乡的长跑赢得身沾乡愁而不止。
诗人对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性。但太过信任语言甚至盲信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往往会无视“趣味”设置的陷阱。“趣味”至于诗歌,或许会带来灵性的脚步,但不提供广阔的天空与翅膀。偶尔为之可,以为常道不可。
习诗以来,最大的幸运是诗为我于尘世言不可言之处,最大的不幸是令我无限接近神迹却又永不可得。奥登说:牛顿将科学引向了迷途。这话说得饶有趣味:苹果在万有引力下不再有其他命名的可能,或者说,在万有引力下苹果进入了恒定的正道。这句话,奥登是否也表明,偶然性和神秘性才是诗歌诞生的万有引力,因为正是它们,为诗歌命名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的所有所谓的恒定的“律”,皆将诗歌引向反面。
现在,还能让我保持读一首诗的耐心的,是这首诗本身所具有的不可知性和这首诗背后的语气、脸庞和环境。我们活着时,语言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熏风用以轻拂湖面的那柳枝,还是熏风本身?是柳枝轻拂下的那湖面,还是湖面本身?或者,语言即轻拂,以示我们的活着?诗人在文本上的多种历练是必要的。就像一个诗人从青年、中年乃至晩年的写作充满了各种变化,一个诗人甚至在同一时期也需要至少在技术上的这一丰富性。能为大家者,必在技术上拥有了这一丰富性的。有例外,如兰波、海子等,那便是天才。
我们所说的“湖面正在腐烂”或者“腐烂着的湖面”,只有在语言内才可能出现和成立。语言是有神性的,当语言用于玄思,这神性就会显迹。是语言内的神性,赋予每个不可能的词以自身的逻辑和方法论。
诗歌的神秘性有二:一是指文本意义上的,即不可解;二是就技艺而言,属技术性目标。张枣曾言及他的《早晨的风暴》一诗说,那是可遇不可求的诗,以后他也未必再写得出来了。这“可遇不可求”大概即是技艺上无懈可击之诗歌的神秘性吧。
当下,诗界的异质更多时候表现在诗人之间已缺乏基本的信任、尊重,以及妥帖与深入的相互阅读。我们难见奥登之于叶芝的离去所感受的“生命的水银柱一下子跌入最低谷的哀痛之情”,难见“将诅咒变成葡萄园”的勇气。每一首诗皆在我们尚未说出它之前已在一个未知的地方了,我们只是用语言经过它。凡语言经过之处,诗的明亮就被说出。它黑暗的部分,正是我们的语言未行至的地方。尽量让每个词语拉长它们的能指,尽量让每一首诗歌保持它们新鲜的未知,就像每天多活一点,尽量在生活的坟墓里掘出更多的可能性。给语言建一座寺庙,心怀敬畏地说出它的秘密。暗径重叠。柳暗花明。樱桃树上结石榴。日常中我所厌倦的这些,诗中却是我最为醉心的。好比刚才我路过的娱乐城所在之处,百年前或许正是我在县志中一直寻找的那座叫做“吃素庵”的旧址。
一首诗之所以失败,有时常常是因为它太过贪大。贪大,甚至会使一个不错的诗人迅疾堕落。有时,一首轻盈之作经过脑海,将会带来负离子充沛的空气。一首诗之所以产生轻盈之感,是因为写作者是提着重心在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