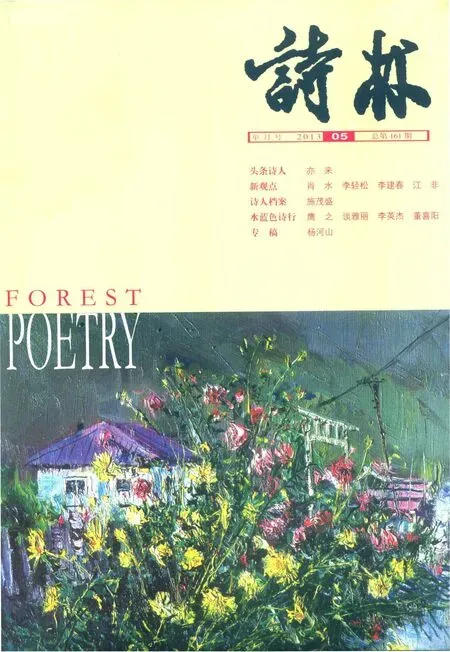施茂盛自选诗
劈材记
清晨。起身。打了个幌子
接着又在院子里劈柴
“嘭嘭嘭”,爆出的几排声响
令懵懂的身体,瘫痪在
一分为二的自在与喜悦里
我不得不描绘远处的鸡鸣犬吠
是它们把我的身体抬得更远
草垛上,涧谷中,晨钟暮鼓之间
我有无数分散于四处的形骸
看似无穷,其实每日都在减去
又不得不惊讶于窗外
新枝抽出悲喜,黄鹂声张了虚势
泥土里,我已不足一人
向下的坠落半枯半荣地映照着
墙角那把披头散发的斧子
地 下
我在宅后的菜地里,
收集池中的涟漪、露水里的
灰尘,和枝头的鸟鸣。
而地下我曾生活的居所,
四壁可供无数个自己奔跑。
在它隔壁的仓库里,
储藏的春天卡在门缝里。
有人喜欢如此轻唤它:
涟漪。灰尘。哦,鸟鸣。
行 乞
我提着水桶里的如来四处乞讨
我欢快地去云端乞讨
水桶里装着雨水、游尘和自我散去的夜晚
夜晚储存的盐,微微有些发甜
它们更喜欢在我篮子里
化作一片汪洋,拼命跨出空宅的门槛
我也提着篮子里四处施粥的基督
追逐云端的祖父。我绕过高坠的星子和村庄
在菜园的那头把他的摇椅悬起
我还要在如来和基督不便深入的地方
掘一口枯井披于身上。我告诉他
现在,我是你的物种,我愿替你在草间烂去
池 荷
聆听波光向湖面散开,
涟漪一圈一圈添加她思春的重量。
一小撮思春的重量
用于轻弹。
柳暗花明的轻弹赋池荷以形骸
有时,我整日望着湖面出神,
以为总有一条小径将会从塘底引我回来。
回来,是为了被再次忘却?
忘却枯荷的斜茎里还藏着鸟头;
忘却鸟头染上的荷色苦难般深重。
是一只鹪鹩,
出生入死捎来被锯去的池塘一角,
顺便将池荷的细骨装进体内。
而我正轻轻收拾亲人们散落湖面的小碎步,
与轻弹的涟漪一起折进木盒内。
我曾目睹他们背着塘底孤坟,
沿一枝池荷攀上琉璃界。
但他们于顷刻间
又化身为涟漪里一小撮思春的重量。
入秋,有所念
早晨有半刻假寐,闭目听
风绕过枝头的呜呜声。
入秋以来,这已是我每日所遇。
这些不易辨认的呜呜声,
仿佛旧相片上斑驳的光影。
我自囚于伏向窗台的光影,
如一只节食的斑鸠,
小心应付忙乱的日子。
“但,这又会是谁最为熟稔的,
从此后的蹉跎中,觅得佳句?”
“我配有这突如其来的
念想吗?”每日,闲适得可以反复自省,
反复照见诟脸迎向
铺张的寂寥,而寂寥
却仍是铁锈锁着的语调。
我算是爱过这寂寥的既往的。
友人曾隔三岔五登门寒暄,
在院子里摘豆、锄笋、诵经。
对我所患之疾,
他们早已知觉与了然。
而醒着,是午后的蹉跎。
我折下一枝案头假的桃花,它递来一瓣
两不相干的枯荣。
仿佛信中所言:
“我随你来到,却一直隐身不及。”
入秋以来,此类念想更像是我
没落的诗学;更像是铁锈里长出的檀木香。
窗外,风正绕过枝头。
飘浮的光影里,
我念想这个午后又会与谁相遇?
还时不时念想隔壁的她终将有些厌倦,
把思暖的身子
一段段灌进清凉。
随手将信札束之高阁。
她以为他已读到她的杳无音信。
C城
空客昂首将我们送上云端。
在云端,想象力为我们陪葬。
多余的灵魂溢出身体;可是,
我们真的有多余的灵魂吗?
在去C城的半刻假寐里,
我们捕捉到闲思和它刚吐出的骨头。
我们各自用当日的报纸,
遮住即将被它辨认出的旧脸。
而我仍不知我们下一站将落脚何处。
在C城尚未抵达之前,在云端,
我早早念及另一个目的地,
对同行的你们,是否有些不吉利?
此刻的C城或许已涌出山雾,把我们
多年前的踪迹抹平。我们将去
再次拜访的诗人,已在云端化鹤。
他的诗句,曾让我们误解他在晚霞里隐居。
我们始终需要有那么点错觉,
这样我们的迷路才可不被叫做迷路。
在去C城的空客上,我想,
在云端是否也会有谁误入歧途?
同理:我们还会出其他一些
不值一提的错。譬如,
我们没有一点多余的灵魂,
但灵魂里,却有多余的灰和丧歌。
木狐狸
弃子不算缴械,算捕风捉影。
也可看做为后一手播下危言;
危言,从来不会仅用以耸听。
“嗯,高招!”你送来喋喋不休,
又乘势在输赢里鲤鱼打滚。
满盘行云流水却仍是假技艺。
其实我后一手已露端倪——
手缚不如脚踢,不辩甚于穷究。
黑白两道,无关乎明暗人性。
也有例外:一把妖刀上的政治,
轻似天鹅绒,重过落子无悔。
“这回,我说的是狐狸而非鹤。”
小微漾
我已经触摸到了。它几乎就是。
比如短裙内的小微漾。
比如死者嘴角煮透的寡味。
多么淘气啊两倍大的小宇宙。
玲珑剔透里隐藏的恍惚无边,
如囫囵,吞下枣模样的褶皱。
而,一半的昏眩仍在。
它却又潦草得揪心。
一颗颠倒的轻率,实属意外。
意外这缓解的色情来得猛,
抵消我不懂赞美的亏欠。
我几乎触摸到了,但它又不是。
煞风景
试问:如何掸去沾满身的迷乱?
线头里埋着不可多得的隐秘,
借一路愁山苦水我忙着数欢愉。
来得及撒野,却来不及止渴。
这浮夸的郊游受哪阵睡意相邀,
身心脱离于凭空一跃的归途中?
但见,远眺成就了近视——
有庞然大物春眠里虚位以待,
因为懵懂,她说没便没了。
更多剖析将来自唠叨后的忽略。
我不认为草鹅经过的就是小径;
她也无意把半幅风景看做风景。
佛简:涅槃
壁上的画中人,自觉满身
清凉,隔空抓一把灰烬
抓一把骨头里的黄沙与宗教
他在丹田附近,有意种月光
砌长廊。抱着一口枯井
口占一绝,问天堂为何物
欢喜中我借他的身子
往里面搬木柴和稻草
把它固有的炉火点旺
因这灌顶的空明,我在壁上
沉于画中灰烬。而他撒开
四蹄狂奔,形骸散了一地
佛简:般若
早晨起来,在菜畦里小坐。
那已成形的菠菜,借自身的丰沛与圆润,
荡漾着无以名状的翠绿。
柳枝间,稀松的鸟鸣远而未远。
有犀利的曦光各自来到我的身旁。
在我身上,刨出层层木花。
我因此可以脱得清浊相间,脱得越来越无形
只剩一副打了补丁的膝盖,
供悬而未决的自己,驻心向外。
我也借膝盖里的笔墨,
画垮掉的杯盏,和杯盏里泼出去的山水。
我画的菜畦,有菠菜可以映照。
而那小坐的人,
得意中已离地而去。
我见他后脑勺凿有呼吸的缺口,
缺口旁,结着的是般若一样的树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