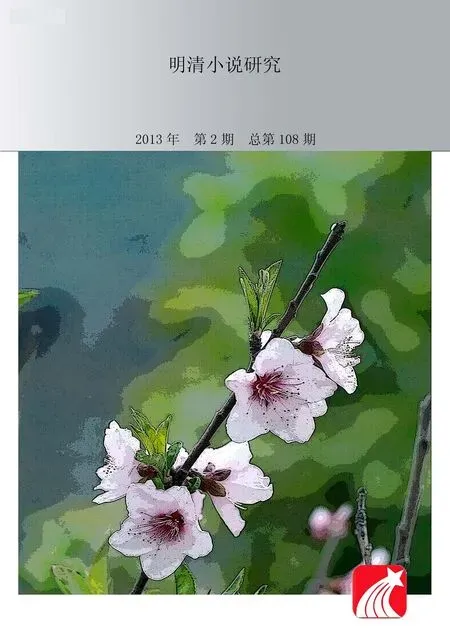宝黛悲剧存在之源辩析
· ·
“根据”者,指存在者存在的依据,有无根据,既关系到存在者之此种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又关系到存在者在此种存在之中是何种命运。根据本身的意义内涵,则关乎此存在者当下如此这般地存在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和最高价值。根据本身的存在如果仅仅依据的是一种特定的文化逻辑,而不能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得到实证,不能在客观的层面还原为一种人生现实,则这根据虽然是根据,但却是一种无根据的根据。另有一种无根据的根据,则是这根据本身虽然看上去是确凿的,但它为存在者限定的存在却是具有漂泊性质的,它从根本上让存者在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一种客居,存在者当下的存在成为无根的状态,结果是存在的根据即是存在者的无根据。我们认为,根据的无根据的两种情况都出现在《红楼梦》的叙述中,理解这根据的无根据,实际上是理解《红楼梦》莫测之味的关键之钥。
宝、黛是小说《红楼梦》中的男女主人公,《红楼梦》第一回专门建构二人存在之根据,本文要探究的是,这根据有样的内涵?其本质特性是什么?依这样的根据,宝、黛被给予了怎样的存在处境和情态?曹雪芹在其中究竟搁放了怎样的辛酸泪?对此我们从宝玉之根据、黛玉之根据和根据之本质特性、作用、意义和价值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一、宝玉生命的无根性
小说《红楼梦》在书写贾宝玉的人间生活之前,就其作为存在者的根据,在第一回中先行给予了构筑。如果我们说《红楼梦》在总的创作方法方面属于现实型作品,那么,这根据的构筑使用的显然主要不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材料。这个根据究竟是什么?它有何特点?这一根据把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先行赋予了这两个人物?此一构筑把一种怎样的悲剧情调先行设定为《红楼梦》全书的语境?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本节文字要给予讨论的对象。
《红楼梦》第一回为贾宝玉构筑的存在之根据,其物化形态就是无用的石头。清人尤夙真说:“如《红楼梦》之因则,无非为青梗山下女娲氏炼剩之一石,僧道等欲扶持其下凡历劫,既上古经女娲炼就之石,非若血气修炼所成,有违天地生意,致必须历劫者。”石头在下凡历劫的状态而能成为贾宝玉这位贵家公子存在之根据,这从经验的生活事实层面讲固然匪夷所思,但曹雪芹确实是如此写来的。那么,这块石头在曹雪芹的笔下究竟被给予了怎样的特性?它又是如何被构筑为小说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存在之根据的呢?
就前一个问题言,我们认为这块石头在原初的层面上乃是一块货真价实的石头,具有物性。故渺渺真人见茫茫大士携了石头而说“携了此物”。但这块石头如果只是一块自然且朴实之“物”,它的在场与一个在当下境域之中现身为主体的存在者无关,即它的在场与消失,都不会出自石头作为存在者主动的意愿。
能够成为文学小说之艺术形象的都不再会是纯然自然之物,都不可能只具有让物成其为物的单一的物性。即使这形象的外观乃花草林木,它也已经具有了意志、情感,具有主观的存在姿态。作为文学形象的花草林木总是人的对象化形式。因此,《红楼梦》第一回郑重其事地给予叙述的这块石头虽然是石头,但它既在小说中作为该小说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形象,它就绝不同于一般的石头。其与一般石头不同的本质,始让它能是小说男主人公贾宝玉存在的根据,始让它能作为《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的人物形象贾宝玉生命中之重要部分而现身于、活跃于小说故事之中。
这块石头本质上同一般石头的不同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从石头的来历讲,它是经由女娲神圣之心与手冶炼出来的,创世女神的特殊神性就是此顽石存在的根据,这根据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块石头的存在历程,存在之命运与处境。
此顽石作为创世大神亲创之物,命定地带着创世大神的神性,它因此是秉赋神性而能灵异的石头。此石头乃“灵物”,其灵性让它能在此刻让自身显形出优美的外在形式。此玉石且已经将自己的审美品性向一僧一道、向小说之读者尽情地炫耀出来。这审美的品性也就是此石头的无用性与小而可爱的优美形态的结合。此一僧一道给顽石镌上“通灵宝玉”四字,“宝玉”即是玉中之玉。玉在古代中国的文化体系里,以玉石的特殊物性,被人化为人生命的或美或善的象征形式,这方面典型的情况,就是儒家著名的“比德于玉”的思想话语。然而,曹雪芹在小说中针对这块顽石而塑造的“通灵宝玉”虽被抛置于“诗礼簮缨之族”,它却并不属于儒家用于比德之玉,因为“通灵宝玉”是由女娲神力所造就、由警幻仙子之女仙力量所培育的,它属于中国原始的女性文化,而不属于先秦始创的儒家那样的男权文化。正是因为此“通灵宝玉”与儒家之玉既同又不同,才导致了这玉在以贾政为代表的、奉儒家文化(我们可称之为儒家之玉)为家族精神的贾家文化语境中,会从一开始就被人们误读,才令贾家的家长们对由这块玉石支撑其内在生命的家族传人贾宝玉始而充满希望,继而归于失望。在小说《红楼梦》中,这“通灵宝玉”成了直指人的灵魂、标示人的命运和处境的物化形式,小说告诉我们,这玉标示着贾宝玉作为人的来处,又暗喻着贾宝玉人生道路可能去往的方向,决定着贾宝玉人生是幸福的喜剧还是泣血的悲剧。玉始让石头有可能与贾宝玉融为一体,让贾宝玉兼石性与玉性于一身,而且能成为小说的男主人公。
其次,《红楼梦》第一回讲到的这块神圣的顽石,在其根据之处,就被给定了一个不幸的命运:神创造了它,神又抛弃了它。经由创造和抛弃两个事件,女娲大神因此既让这石头得到根据,成为石头,又让这石头在成为石头的那一瞬间,立即处在永远的无根的状态之中。在强烈的失根痛苦中,石头有了两种基本的存在情态:一是自怨自怜,悲己之不遇:它“因见众石皆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二是逍遥自在:“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曹雪芹筑造此两种存在情态的哲学材料主要是庄子的思想,又杂糅了汉代诗学中士悲不遇的文化情结:庄子讲存在者不处身于材,即处身于不材。庄子认为一个人无论处身于材还是处身于不材,利弊都不能调和,因而主张人最理想的是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曹雪芹用庄子的哲思来写石头被抛之后的存在情态,亦未言涉在材与不材之间这一存在之难题,但却写到石头有了逍遥自得的存在情状,这表明这块石头久历岁月之后,虽不能完全从自我怨伤之中解脱出来,但已经有能力将此巨大的伤痛感转化为逍遥自得的诗意栖居情态。
曹雪芹在小说之第一回就预先设定了贾宝玉一生的悲剧主要的内涵构成:这一悲剧主要的内涵就是生命根据之不可凭依,且这一生命存在的无根状态纵贯神凡二界,是不可解脱的命运。作为贾宝玉前世要素的这块石头植根于神界的被抛的命运,以及伴随这命运而来的悲剧当事人对自己“无才”的体认和“不遇”的疼痛感。这一悲剧内涵显然不会随贾宝玉最终还玉出家而随之尽数归于无形。依《红楼梦》第一回贾宝玉存在之根据来看,他的出家,一方面是出离世俗之家,挣脱了在人世漂泊无根的存在状态,但是,出家并不能导致贾宝玉得到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当他回到青梗峰下,赤霞宫中,他所回到的不过是在神界的无根状,而不仅是再次得到了生命的“逍遥自在”。
总之,作为贾宝玉存在之根据创世女神女娲所造的这块石头,是神圣而高贵的,但高贵长久地保存下来,幸运却很快戛然而止,它毕竟很快被创造它的同一神祗抛弃了。对于这块石头而言,被抛是它来到世间最初的痛,又是它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最大的痛。这一疼痛在小说中被反复陈述为“无才补天”之痛,此处的“无才补天”有两方面的内容是必须要看到的:
第一、女娲补天是一个修补宇宙和世界的宏大工程,此工程涉及到宇宙和世界的三个存在情态:1、曾经完好的宇宙和世界;2、一度破碎的宇宙和世界;3、修补后完好如初的宇宙和世界。顽石被女娲炼制意味着它得到了参与修补和重构宇宙和世界的机会,然而它因“无才”还是被抛弃不用了。相对于被用的那些石头而言,它是无用的零余者;相对于在修补过程中的宇宙和世界,以及相对于补好的宇宙和世界而言,它是居于其外者。这种对家园疼彻心扉的疼痛且渗透到小说全部文字里,化做了无人能知其具体滋味的辛酸之泪。在甄士隐的梦中,茫茫大士提到此石头被警幻仙子收留,然而石头之居于赤霞宫,只是在常态化的无所居停中暂时得到的寄居。在寄居中,其自怨自愧可以得到一点缓解,但无根之痛却不会终止。
第二、这块石头不同于一般石头的地方在于,它是可以随意地走动和变化自身外形的灵异的石头,是一块有意志、有情感的石头。这块石头还可以到处“游玩”,“常在西方灵河岸上行走”,爱怜那株绛珠仙草,时时为之浇洒“甘露”。由此看来此石头灵异到握有生命神水甘露,已可助本质低下之草木升至人阶,在在世时间上超凡入圣,也可看出它自己实已灵异到具有男人之形体,而能引发仙草用泪水还它甘露的念想。曹雪芹在这里给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神造出一块石头,神抛弃了一块石头,石头成了玉,玉成了仙界小吏,而有男人形体,玉石被带到凡间而与贾宝玉灵与肉融为一体。这一线索也即是文学形象贾宝玉存在根据的阶梯。
二、黛玉存在的别样悲苦
林黛玉作为《红楼梦》的另一主人公,其存在之根据也是在小说第一回即得到构筑的。其存在根据之物化形态,即那株生息于西方灵河岸边的绛珠仙草。
依曹雪芹的叙述,林黛玉的存在根据,可大致分为两截,一截与神瑛待者原本没有关联,立基为凡俗草本,尚未有变化自身形体之灵力,秉性脆弱、生命短暂,属于必死者之列。此时,这株小草是具有物性之草,在严格的意义上,尚不能称为仙草;另一截则与贾宝玉存在之根据即那块神圣的石头或神瑛待者发生关联,此仙草从神瑛待者处得到仙界之生命圣水甘露的时时浇灌,从而改变了自身作为凡物的存在根性。改变之后的草始能真正称为绛珠仙草,真正有了“仙”性。“仙”之性具体表现为:原本属于凡俗的草真正变成了“仙草”,在世的岁月得到“久延”,在久居的日子里有了变化自身形体,而且是向上提升性质的变化之能力,修练成了女人的身体,仙草因此实际转形为仙女。由于绛珠仙草因甘露而由凡成仙,而甘露系得自于神瑛侍者,所以,神瑛侍者,即石头实际成为绛珠仙草存在之根据。
我们若把林黛玉存在之根据绛珠仙草同贾宝玉存在的根据神圣石头相比较,则二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自具特征。相似之处,在于绛珠仙草自其根本之处,同样是作为一个忧愁满怀的存在者,这仙草即使修成了人之女形,却依然“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从情理上讲,这仙草居然脱离草本,而具人形,本是应该高兴之事,然而小说并没有写她的高兴,反而写了她身具人之女形之后,却更日常、更自觉、更深切地活在忧伤愁怨的感觉之中。这忧愁是此草生发于她生命根本上的直指死亡的脆弱和敏感,这种生存的巨大痛感在此草成为仙草之后,犹如胎记,永存于仙草的生命感觉之中,又如她生命之无意识,驱动着已具人之女形的她向“愁”而生,即使绛珠仙草步入人世,化形为林黛玉,这直指自身生命的巨大痛感也依然时时显现为林黛玉日常的处身情态。从彼岸到此岸,从前世的记忆到当下的体验,从绛珠仙草到林黛玉,形体、世界、时空、家园都在变,但直指生死的忧伤却一直不变。
显然,宝、黛在其存在的根据之处同是忧伤的存在者,只是他们各自忧伤的内容又有所不同。林黛玉存在之根据不同于贾宝玉存在根据的地方在于,在生命的来处,她所属于的那草,在仙界原本就是卑微的、无庇护的孤零之草,生存对于她来说是严峻的、冷酷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林黛玉寄居于贾家的这一日常生存感受,应该说早在她的存在根据,即那株小草生息于西方灵河之时,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在灵河岸边之小草感受到的纯是自然的严酷与无情,当其化身为林黛玉时,她所感受到的乃是用自然的严酷无情来喻指的人间风霜。在这样的生存艰危之际,一旦有人助她生存,这人即成为她心中最大的恩主。
神瑛侍者的生命来自女娲,生存似乎从来不曾成为他的问题。他的苦恼在于存在的层面,即他被抛的事实和被抛的理由。尤其是他被抛的理由:无才,最终成了属于他的“自我与他者”的共识。如果说林黛玉所属于的那草整日吟唱的是指向自我生存窘困的呻吟之声,那么,那块神圣的宝玉在青梗峰下发出的就是关于他之存在的苦痛的叫唤,且这叫唤总是为作为他者之“天”而发出的。属于仙草的是她的生存之痛,属于石头的是他的存在之苦。
贾宝玉和林黛玉存在根据之不同则在于,首先,在中国古代文化设置的生命阶梯上,绛珠仙草所在的位置一开始就低于那块神圣的石头。那石头因来处的高华而自己就能支撑自己神性而灵异的生存,石头相对于小草因此是自由的和主动的,它不完全是命运的玩物,它甚至强大到有神力成为其他生命体之恩主。与之相关联的绛珠仙草则被作者写定为是弱不禁风的、被动的、不自由的,自我的生死自己决定不了,要由他人来决定。于是,宝玉注定是小草的施恩者,小草注定是受恩者和思图报恩者。其次,石头被曹雪芹设定为男性,小草被设定为女性。由于石头让小草变为仙草,石头就是仙草存在之根据,结果是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里认可男性为女性存在之根据。曹雪芹的这一思想,显然来自于《易》学,这一思想与他小说在后面高扬女性价值,贬低男性的做法并不完全一致。
来自于女娲的神圣石头与生长于灵河岸边的小草,原本各自有自己的来处,有自己存在的根据,但二者在小说叙事中却最终走到了一处,彼此在存在的根据处最终发生了骨肉精血相连的关联,在初始处决定了宝、黛情事必然的生发、发展与结局。那么,二者之间因何而发生了存在根据的关联呢?
赤霞宫附近,西方灵河岸边有株小草“十分娇娜可爱”,已经达到极致,神瑛侍者见草可爱而做出用甘露浇灌的行动,这是典型的由爱生怜。“娇娜可爱”,用美学的眼光看,属于优美的范畴,石头见草可爱,是对美的自然物的审美观照,在审美观照中,石头获得了高度的审美愉悦。但石头接下来对小草浇灌的行为,却不再属于审美的领域,而是对一个弱小生命的援救。连接石头对小草审美与援救两种不同性质之行为的要素,是神瑛侍者对“十分娇娜可爱”之草的怜惜。怜惜一头来自于神瑛侍者对小草之美的珍惜,一头来自于神瑛侍者对小草生命脆弱,朝不虞夕的悲悯。因为有后者,所以,神瑛侍者的浇灌行为意在让小草长存;因为前者,所以,神瑛侍者有意用了仙界神圣之生命甘露浇灌之,意在让小草审美地,尤其是最终神圣地生存。石头对小草因怜惜而施以甘露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审美之物的呵护与养育,是将凡俗之自然物转化为神圣之物。由此我们可以知神瑛侍者对西方灵河岸边的这株小草原初的态度是审美的态度,由此态度引发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之间从生存到存在两个维度的关联,这关联涉及生与死、存在者之生命感受中时间的长与短、受溉与施恩、欠与还等内涵。红学研究者一般更重视欠与还的内涵,而对另外的内涵则轻易看过,这是不尽妥当的。
三、结语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贾宝玉和林黛玉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根据,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已经先行给予了构筑。
所谓根据的无根据,首先是说这根据之为根据,本身是无法用人生经验或科学试验加以实证的,它纯然地是人想象或信仰之物。其次,是说这根据是存在者无法凭依的。就前者而言,贾宝玉作为存在者之存在根据,它及它所处身的神界,首先是神话之境。女娲补天的故事是创自中国原始初民的神话,曹雪芹借用女娲补天神话安放贾宝玉最原初之“来处”,此“来处”有两大特点,一是神话时代是民族言语形式之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开端,女娲补天又是神话世界存在的开端,在中国古代所有久远的历史时空中,这“来处”是最久远的,具有崇高的价值。这“来处”因此让贾宝玉在其存在的根性上是纯然中国的。二是贾宝玉的这一“来处”是曹雪芹用神话虚构而成,此“来处”所指涉的形象,事件等因此都是不可实证的。“来处”的无法实证,乃因为“来处”是原始神话之境,原始神话是人类想象之物。也就是说,曹雪芹在构筑贾宝玉存在之根据时是用想象的思维和材料来进行的,其结果就必然是,贾宝玉在存在的根性上,是来自中国历史开始之处的想象之象,因此,这一“来处”让贾宝玉事实上成为中国人关于自身神话时代的集体记忆,成为中国人在以类相生层面之生命最深长的绵延。这一“来处”在本质上是贾宝玉存在的巨大的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
其次,作为贾宝玉和林黛玉存在根据的神圣石头、绛珠仙草是在佛、道宗教信仰之境中现身的,在青梗峰初见石头,携之入于红尘的是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茫茫大士,当是佛教中人,渺渺真人,则当是道教中人。至于关系到绛珠仙草的西方灵河、甘露等则是佛教之话语。古代中国两大宗教在中国原始神话的神圣之地一齐现身,这表明曹雪芹所体认的信仰之境,是佛道二教与中国原始神话、原始巫术合为一体的。在此信仰之境中,石头不再保有自身本己的形态,不再是物性之石头,而成了一个见证古代中国人在宗教信仰层面之存在根据的符号。宗教信仰符号在本质上是神秘的、荒谬的,此石头作为这样一种性质的符号在小说中出场。因此,《红楼梦》第一回说到的这块石头,就是荒谬(或荒唐)之物。
就曹雪芹为贾宝玉和林黛玉构筑的存在根据是不可凭依的根据而言,不可凭依的性质主要表现为石头被抛的处境和绛珠仙草即使在“久延岁月”之后依然终有一死,依然走不出对自身之死的忧恐感觉。贾宝玉出家,林黛玉香消玉殒是离开“去处”而回到其所从“来处”,但二人回到“来处”就有了坚实稳靠的存在地基了吗?即使宝玉和仙草到红尘走了一遭,当它们回到“来处”,大概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原先在“来处”中的处境,被抛的依然会永在被抛的状态,在“离恨天”的依然会日常地居于“离恨天”。清人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说:
汤临川先生云:“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宝玉悬崖撒手,宝玉之梦觉矣,宝玉之情了矣。吾不知其了情了之后,为佛耶?为石耶?为神瑛侍者耶?抑乃返灵河岸上浇灌其绛珠仙草耶?迷离惝怳,信乎欲辩已忘言矣。
二知道人就贾宝玉出家之事本质上即宝玉回归“来处”事,设想回到“来处”的贾宝玉究竟回到什么样的存在处境。
“为佛”是一种结果。石头走下红尘一番,对人情整体了然,并因而最终能对一切人情不再执着,不执着,即到无情无欲或不以一切人之情欲为羁绊的境界。这种结果最不靠谱,一则成佛即放弃了成人,这意味着贾宝玉作为人的一切存在根据也失云了意义和价值。二则,成佛即意味着可与女娲大神平起平坐,这意味着不仅人,就是石头也可以通过历劫而僭越到神佛的位置。石头成佛,是人生的一种提升或圆满,《红楼梦》所讲故事因此实际成了人存在之喜剧,而这与曹雪芹意在将《红楼梦》写成彻底的悲剧故事的创作动机就相左了。
“为石”是二知道人设想的第二种结果。这结果大致可以分两种情况来看:第一、意味着石头的历劫是石头原样离去,又原样回来,终只是石头。第二、去了又回的石头与历劫之前的石头表面虽然彼此一致,但二者内在的生命感受已经大有不同,历劫之前的石头本不在情中,所以,无所谓情了还是情不了。石头历劫,是陷入情中,由此才有情了还是情不了的问题。去而复还的石头,其回归靠的是此石头终于勘破情关,情了证空。这意味着历劫之前的石头至少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情在面前时,它难免会陷入其中。但情了返回的石头对于情而言,则已修成金刚不坏之身。如果石头回归结果真是这样的,石头原来的存在根据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即使它在人的情感方面已经是金刚不坏之身,它在青梗峰下,将依然处在永远的被抛状态之中。
二知道人设想贾宝玉返回“来处”的第三种结果是重新做赤霞宫中的神瑛侍者,回到天天在灵河岸浇灌绛珠仙草的旧日状态。当贾宝玉回复其灵异石头之本相,重作神瑛侍者时,只能是因为此刻那仙草又处在生命朝不保夕的脆弱状态中。而这恰恰表明绛珠仙草下到红尘悲苦一场,这段爱恨情伤的经历并未丝毫改变她存在的原有根据,她始终是一个挣扎于生死之间,且深切地自我意识到自己的死的存在者。而重回“来处”的神瑛侍者作为情了之石,他其实已经不是原来从未下过红尘的那位神瑛侍者,而是以“情了”为底基。绛珠仙草也许又会重陷以泪还债的旧轨,然而神瑛侍者将不再会为这一还债之情与行为所打动。二人将在神灵佛道之乡,各自永远伤愧自己存在之无根据性。
曹雪芹通过对石头和仙草根据的无根据的描述,传达出他关于人生就是彻底的悲剧,就是荒诞的体认、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人生无论是去还是来,其实都没有从根本上得救的可能。
注
:① 尤夙真:《瑶华传序》,《古本小说集成〈瑶华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涛音书屋本。
② [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女娲所弃之石,谅因其炼之示就也。乃遇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之到花柳繁华之都、温柔富贵乡,殆以繁华富贵为炉,加之百炼乎!今而知宝玉之性情温婉化为绕指柔也。终焉决绝直化作切梦刀矣,宝玉入则金钗十二,兰麝生心;出则裘马甚都,仆从如虎,翩翩然佳公子也,被人看煞矣。而孰知其真面目乃大荒山之一块石哉?咄咄怪事!”《八家评批红楼梦·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二知道人这里说到作为小说《红楼梦》中一个文学人物形象的贾宝玉和大荒山的那块石头是一体之两面,二知道人甚怪读者但见其作为文学人物形象一面,而不见其作为大荒山之石头一面,其甚怪的念头处,已经隐含有石头因何而能成为文学人物形象的问题,只是可惜二知道人终究没有把这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并给予解决。
③ 《葬花吟》,《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第二十七回,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④ 笔者认为,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其实亦指谓“满纸荒唐物”,因为,文学之言的荒唐从来不是语言本身的荒唐,而是语言指谓或指喻之物、之象的荒唐。
⑤ [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八家评批红楼梦·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