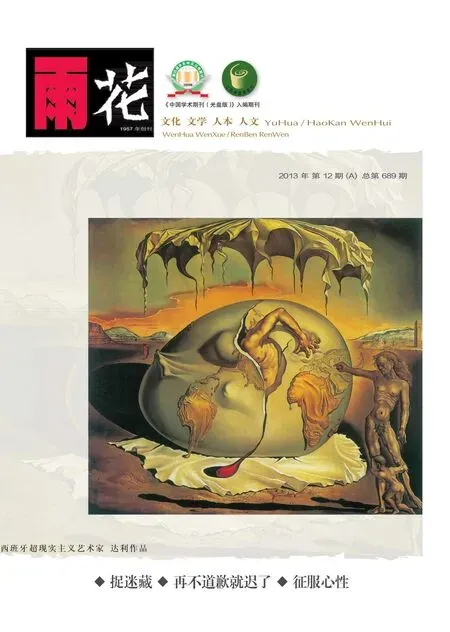浴锅承载的光阴
●皇甫卫明
长大后我才知道,铁锅洗浴只在望虞河两岸不太大的地方盛行,同是常熟的高乡也拿我们锅浴当笑料的。
村里有两口浴锅,桥东桥西各一口,分别置于两任队长落脚屋。与他们场角的两口公井,与穿村而过的小河,同属公共资源。有浴锅是方便,但一般农户置不起,铁锅、砖块、人工,而且毕竟要占据一些地方。有了借口,队长家的下屋理所当然比别家大一些,下屋兼作柴房,还养着牲口。
三面墙,围一口铁锅,铁锅支在正方形的凹宕里。浴锅支在墙角,占地少,也借助房子的两面墙壁,再砌一面半墙,半墙不到顶,但能遮挡视线,半墙下方必是一个灶口,添柴、退灰。一方没有墙壁的豁口供浴者出入,浴锅就隐秘了。
入秋,被小河冷落了几个月的浴锅开始有人光顾。秋收时节,洗浴者更是拥挤。母亲一直埋怨我跑得慢,总被人捷足先登。捷足者全家拥有优先权,一家老少浴完,才轮得上后来者,而且往往排着长长的队。浴者排队,无须像市场上一个挨一个站着,或坐或站或蹲,或斜靠在猪栏,也有随便找个地方,用带来的柴把随处一放,席地坐着。按照先来后到,秩序一般不会遭到破坏,但队长或者队长老婆一露脸,总有一个或几个提议让他们插队,他们故作谦让一番,回屋去取换洗的干净衣服。你道每个人都乐意?本来沉默的以更沉默把不满闷在心里。有的一脸堆笑嘴上附和,心里责骂拍马屁者拿大伙的时间充好人。也有确实由衷的谦让,多是老人,他们觉得早早摆在床上也睡不着,多等一会也无所谓。能轮到加塞的不光队长一家,在外当干部的偶尔光顾也能享受村民谦让的殊荣。父母没这个资格,我把排好的位置让给他们,把自己换到队伍后面。
浴汤不可太满,六七成正好,否则人一下锅,水就溢出来。大半锅的水,也不更换,几个人一洗,水浑浊到发稠,升腾的水汽中隐隐有臭味,但还有人接二连三赴汤蹈火。浴者一边直呼水脏,一边拿一句俗语自慰——浑水里洗出白萝卜。也有直摇头而打退堂鼓,回家将就弄弄。有的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于心不甘,于是洘出脏水,重新提水烧热。每逢此时,母亲嚷嚷道,就让我钻一下,钻字极言洗浴之快,很形象。她一面自嘲末汤葆元气,一边麻利地脱衣服。浴伴嘻嘻哈哈笑着。母亲舍不得浪费柴草,也想早些回家做些家务。
也有我抢了先机的时候。母亲笑着对我说,试试水温怎么样?你烧的就让你浴头汤,头汤水清澈得冒着香气。我可以随意招呼母亲添火,母亲窸窸窣窣在灶前忙乎。半躺在浴锅里,热气从锅底冒上来,浑身惬意。锅底烫人,拿“乌龟板”垫在屁股底下。陆陆续续有人来排队,母亲催我快起。不等我坐起,兄弟已经脱得赤条条地挤过来,兄弟浑身冒着热气从浴锅下来,父亲就跟着下去了,最后轮到母亲。排在母亲后面的浴客坐在灶门口的小凳子上为我母亲添火,嘴里兴奋地唠叨着,称赞我们一家的高效,懂得照顾后来者。母亲喊停火,烧火的站起身准备脱衣服。排她后面的接着坐到凳子上,准备烧火。
候浴的心里着急,嘴不闲着,都是家长里短。谁家的闺女相中了哪里的后生,家里不同意。哪个村寨的分红好,村上没光棍。说着说着,说到锅浴。二嫂是出名的老汤,也就是耐热,排在她后面的遭罪了。三婶不够麻利,她坐在浴锅里没一点声息,连带脱衣穿衣,半个小时都不够。德胜爷抠门,总不带柴禾。有一个上海女插青刚来时,人家给她烧好浴汤,她就疑心会把她煮熟了,死也不肯脱衣服。她说屁股底下就是火,隔了一层铁皮,不煮熟也会漏下去,吓煞人。长大后我才知道,铁锅洗浴只在望虞河两岸不太大的地方盛行,同是常熟的高乡也拿我们锅浴当笑料的。
收获时节,烧浴汤的可以堂而皇之到队里打谷场抱柴草,从队长到村民都默认这种公款消费。过了这个时节,柴草分到各户,场角仅有的柴垛留作牛料,谁都不敢碰。我生性邋遢,觉得几个小时受罪换来几分钟的享受,不值。轮到我烧火了,却给人加塞。妇人们陪着笑脸招呼我,一个挨一个过去,我又不好意思跟女人挤。有的招呼都不打,忽略我的存在。我气不打一处来,狠命地往灶膛添火,浴锅里的女人嚷嚷别烧了,我兀自把一大捆柴禾叉进去,女人终于逃也似地从浴锅里爬起来,作势拧我耳朵,她大概忘了此时赤条条的没了隐私。小屋里仅一盏15瓦的电灯,十分幽暗。半屋子的人,凭声音很清楚浴客在干什么,浴客贴墙站在豁口,别人是看不到的。也有大大咧咧的男女不注意,从他背转的身子能给人一个囫囵的后背。也许他们觉得,背后又没长什么重要物件,曝光也无所谓。
三婶家率先自支了一口浴锅。她家条件好,老头和两个儿子做手工业。她人前人后炫耀。三婶的浴锅分流了不少浴客,她不太在意浴客带多少柴禾,只要每次让她头汤。她坐在浴锅,时而精工细作,时而在锅里窜动,嘴里嗤嗤地低吟,很享受的低吟。有一阵子,母亲不再去三婶家,也吩咐全家别去。母亲为了一点小事和三婶有了抵牾,好一阵子互不理睬。过年前,三婶特地差小儿子来我家,说喊我母亲去沐浴。母亲有点犹豫,父亲说去吧,还要三婶亲自来请你么。三婶破例让我母亲头汤,还亲自添火。说说笑笑间,恩怨烟消云散。黄昏,三婶的小屋又聚了一大帮女人,她们是来乘汤的。
没几年,家家户户陆续支了浴锅。我家小屋里支不下,就在小屋边搭一间,仅能容一口浴锅。洗浴是方便了,但母亲不是每天升火。晚饭后,还是抱着干净衣裤满村转悠。今天谁家烧了浴汤,老妇们都知晓。就像轮着请客,那帮老妇隔一阵也光顾我家,年轻人不再去凑这个热闹。
队长家的浴锅早被冷落。一次看见他家在宰羊,宰杀后把羊拖到浴锅里浸泡去毛。母亲说,宰过羊的浴锅都是骚味,想着就恶心。我说,那时队里杀了猪不都在浴锅里刮毛,那两口锅少说也接待了几十头猪,猪没骚味?宰牛时桥东的浴锅里还煮过牛头呢,牛没膻味?母亲语塞,狠狠白了我一眼,只是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