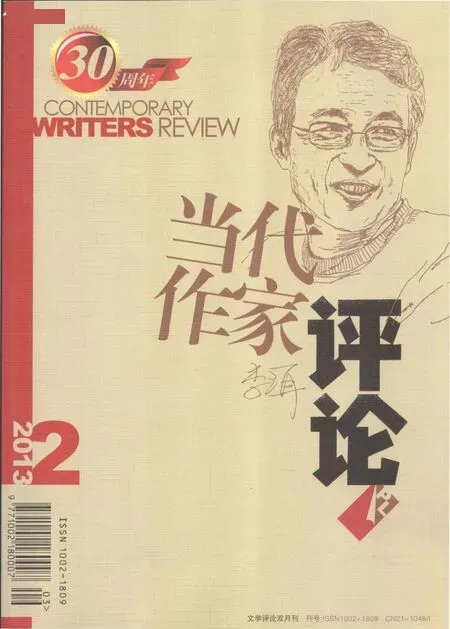不可探查的“关系”与“坏乡村”的秘密——关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
周景雷
《生死十日谈》是作家孙慧芬用了五天时间,利用调查与访谈的形式,参与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农村自杀遗族的调查与研究”后的一个“不期然”的创作(孙惠芬语),作品真实地记录和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某些“凛冽”和“刺骨”的内涵。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二〇一二年的第十一期上,列在“非虚构”项下,这似乎是突出了其纪实性的品质。但作者说:“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的现场,都是为了造成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切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而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不管怎样,在我心里,它是一部小说。”这坚定了我把《生死十日谈》当作一部小说来看待的信念。一方面,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来自于生活和经验,而且即便如此,一个作家也未必能够将全部的经验和记忆纳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全视角的写作,它永远超越于作家自身的单一视角。所谓全方位,也只是站在作家自身立场上的全方位,而不是站在社会之上的全方位。由于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以,对于作家来讲,他就可能去放大一些细节,因而也就可能凸显了这种写作上的纪实品格;另一方面,作家所呈现的全部经验和记忆都是被赋予了作家个人写作品格的。在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中,他可能有诸多的变化,但基本保持不变的是个人品格。个人写作品格包含了作家的全部写作素养、胸怀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认。这种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的品格成为一个写作者区别于另一个写作者根本性标志。因此,凡是经过作家个人整理过的材料都带有作家个人的主观痕迹,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非虚构也变成了虚构。强调虚构的意义在于按照虚构的线索和面貌可以探查出作家是如何思考生活并将之赋予文学性的意义。对于《生死十日谈》而言,我想考察的是,在当下时代作者如何结构了乡村生活并由此探查其中的奥秘。
一
应该说,在中国,出身农村的作家,虽然后来多年身居城市,但并未割断与乡村的联系,或者说,他们通过往返城乡来获得精神资源和写作资源。城乡的互动和对照,也就是城与乡之间关系的纠葛成为他们的写作动力,这种情形在今天越来越鲜明,甚至成了某种定律。这种至为重要的关系包括空间上的存在状态,也包括时间上的前后分裂与衔接。就是说,一个作家要想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一个完整的乡村,那就不仅要看到城乡的对比,还要看到昨天与今天的承续。没有昨天与今天的比照,贾平凹就不能表达出《秦腔》里的悲凉,孙慧芬也就不能把“吉宽的马车”安放在城市当中。但他们对这种关系的审定,并不是包含了城乡间的所有方面,因为每一种关系都可以无限地向外延展。借用南帆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中的观点来总结,就是“除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永远可以扩张的相对于其他客体的关系网络以外,不存在关于它们的任何东西有待于被我们所认识。能够作为一条关系发生作用的每一个事物都能够被融入于另一组关系之中,以至于永远。所以可以这样说,存在着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向着所有的方向开放:你永远抵达不了没有处于彼此交叉关系之中的某个事物。”由此,南帆说:“一种事物存在于多种关系的交汇之中,并且分别显现出不同的层面,这是正常的状况。”南帆还说:“文学的特征取决于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一种关系决定。”《生死十日谈》的写作缘于一种社会学、心理学的调查,因此必然呈现着这种学科的特征,涉及到了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关系的角度考察《生死十日谈》的写作也许就是一个很恰当的选择。
孙惠芬虽然没有在审美层面对关系作深刻的考量,但她注意到了关系对她写作资源牵动和诱惑,甚至可以说,生活的关系成了她写作的动力。她曾写作了《致无尽关系》,并在《生死十日谈》中再次言及了这一命题。坦率地讲,一个作家如果不被各种复杂的关系所纠缠,不在这种纠缠中进行苦思冥想并试图通过写作的方式来予以摆脱,那么他的创作的可读性及张力就会大打折扣。
在《生死十日谈》中,作者所言及的最为根本的一种关系就是生死关系,并由生死关系衍生出各种生活及伦理关系,可以说是生死的问题考量了其他关系。也可以反过来说,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关系,最后总是归结为一种生死关系。自杀者之所以自杀,其原因就在于生死之间的平衡性被打破了。作者所要探究的就是到底打破了什么,是如何打破的。如果没有这些自杀者的死亡,就没有这些自杀者近亲属即自杀者遗族的对生的考问——这样的考问几乎布满了全篇。这不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为一个国家课题所要关注的内容,而当被一个文学写作者注意到,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学文本中的时候,它也便具有了文学性,从而成为了文学的审美对象。比如在“第十日”访谈中,目标人是一个无比热爱艺术并因此而无比热爱妻子的“小老头”,被访者是自杀者的妻子“大辫子”以及“大辫子”的父亲、母亲。“小老头”一辈子用爱付出,坚持为妻子梳辫子四十年,而妻子一生只专注于自己的剪纸,从未顾及丈夫和孩子。在这样一种夫妻间的爱与被爱关系中,一方只是付出,一方只是索取,最终平衡性被打破,“小老头”因干不动了,看不到希望了而自杀。由此牵涉出另外三种关系,即“大辫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大辫子”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大辫子”的父亲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这四种递进关系中,每一种关系平衡性的破坏,都导致另一种关系的失衡,其极端的结果导致自杀的发生。在这个案例中,它的线性逻辑是父亲年轻时因工作需要常年在外奔波,因而有了外遇。有了外遇,夫妻关系被破坏,经常吵架,大辫子便厌烦家庭,年纪很小便坚持下乡,与丈夫结婚,从此终生依赖,从不付出。这幅多米诺骨牌运行了四十年的时间,把前后诸种关系紧密地牵连在一起。再比如,在“第九日”访谈中,目标人是耿春江,被访者是耿春江的妻子于桂珍。耿春江的自杀直接源于和邻居打架,而这种打架又可追溯到许多年以前因爱生恨的追逐。随着访谈的深入,有几种关系相继出现并交织在一起,首先是兄弟关系,在城里当领导的大哥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到兄弟身上,令兄弟举债供孩子出国读书,造成贫困;其次是父子关系,儿子出国,父亲想念儿子;三是祖孙关系。对诸如此类关系的理顺和探寻成为孙惠芬在作品中分析案例、查找原因,并进行文学性组织的基本方式。
作者孙惠芬对“关系”进行探究进而追求真相的意识是很自觉的。在她二〇〇八年发表的《致无尽关系》中,以过年为契机,以自己的娘家和婆家为两个圆心,为我们梳理了两个以亲情为核心的关系之网。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曾经感慨道:“年,实在不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过是一张网的纲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就没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的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一有风吹草动,哪怕一个电话,都会让你惊慌失措。”“说到底,真正的纲绳不是年,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亲以及由他们延伸出的血脉。”在这种关系中,亲情因为这张关系网的覆盖和交织而变得沉重。而在《生死十日谈》中,这张关系之网则向外蔓延,深入到别人的亲情体系中,甚至覆盖到了亲情之外的诸种社会关系中。在这张网中,因为是以生死为起点,因此其中所包含的悲痛与沉重则又更进一层。在《生死十日谈》的“第四日访谈”中的第一节则直接以“关系”命名。在这一节中,她对此前三日的目标人和被访者都做了一种关系性的分析。她说:“那一天,因为‘关系’两个字一直缠绕心中,面对每一个现场,我都能拎出关系这条线,就像一只网的纲绳,纲举目张。”
话虽然可以这样说——“纲举目张”,这就算能够找到真相和告慰自杀者的在天之灵吗?显然,作者在这里有着很清醒的“不自信”。因为她认识到,不论出身和地位有如何的差异,每一个人都在这张网中奔向着自己的前程,但这个前程却未必就是确定的。她说:“我们一程程奔着的,是一个个地名涵盖下的虚妄的空间,向这个虚妄的空间一路拼搏。你也许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它和你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可是空间无限,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奔着的前方除了前方,没有实物,唯一的实物就是衰老和死亡。你和信念的关系发生了断裂,那你怎么办?”比如在“第三日”访谈中目标人耿小云,到底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交织中自杀的?她的“回乡A计划”到底是怎么中断的?在“第二日”访谈中的目标人张小栓的自杀到底是因为两口子打架还是因为重病在身?每一个自杀者的“往生”我们都能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明吗?也就是说,在由各种关系所确定的网格中或者坐标中,能够锁定那个有关真相的原点吗?这种考问,我以为是在《生死十日谈》中最深刻的思考。遗憾的是,当事人、作者和我们似乎都不能给出明晰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特别是在后几日的访谈中,作者在几处特别提到了乡村教堂。在第四日的访谈中,他们听到了教堂的钟声,也看到了教堂的红房子,但是山重水复,这一日终于没能找到教堂。一直到第八日,才与教堂真正不期而遇,而且在教堂里还看到了自杀者遗族数人。虽然在今天,乡村里的基督教堂随处可见,但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安排未必就不是作者潜心营造的结果。我宁愿相信,这是作者在面对诸种乡村关系时无法理清头绪时的一种安慰性的答案。
二
新世纪以来,面对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和诸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乡村更加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但整体来说,这种乡村书写与二十世纪相比,其色彩和基调却常常让人产生一种沉重的慨叹。这些创作聚焦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的种种困境,揭示了因苦难、贫困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多重现实和愿望挤压下的一个个扭曲的人生和麻木或者痛苦不堪的灵魂,并向现实社会秩序和新旧时代杂陈中的文化合理性发出了有担当的质疑。这种主题几乎在所有有影响的乡村书写中都能够得到程度相当的提炼。从贾平凹的《秦腔》到莫言的《蛙》,从阎连科的《受活》到李佩甫的《生命册》莫不如是。以贾平凹为例,我始终认为贾平凹就是一位进行全面质疑、抵抗和担当的作家,他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的创作对此作了非常好的诠释。《废都》是对现代化进程中都市文明的质疑,《怀念狼》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性的质疑,而《秦腔》则是对现代乡村文明的质疑。这三部作品提供了贾平凹最近二十多年来所有创作的基本线索,表达了他的全面思考。但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其他作家的努力。我想说的是,与前十几、二十年相比,关于乡村书写,我们正在逐渐丧失从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美好想象,经过了文人们漫长的抒情积累所建构起来的“好乡村”形象已经坍塌,今天的乡村在作家们的书写中已经变成了“坏乡村”。当然,这里的“坏”并不是“恶”,它仅仅代表了不美好。
应该说,《生死十日谈》是近期描写“坏乡村”的一部有力量的作品,与其他作品一样,这是一部“沉重而尖锐地承担”之作。但本文想讨论的是作者如何通过农村自杀这一现象来透视“坏乡村”的秘密。白烨说:《生死十日谈》“既有自杀者悬疑重重的追踪与剖解,又有与相关知情者的对话与互动,而一桩桩自杀事件的揭示,人们从中看到的,既有诱发事端的偶然性因素,更有酿成事件的必然性氛围,这便是急剧变革的农村在急速前进的同时,带给人们的无奈与失望,困顿与疲惫,以及在文化教育、家庭伦理、道德认同等方面的矛盾与问题。整个作品传带给人们的主要信息或巨大震撼,是农村问题不单是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与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白烨的点评已经接近了对秘密的探究。
在《生死十日谈》中,几乎所有的自杀者及其遗族都身陷一个遭到了破坏的乡村伦理,特别是家庭伦理之中。家庭伦理和乡村伦理的存在,不仅确定了中国乡村的秩序、格局,而且也通过这种伦理的运行保证了社会的整体性稳定,甚至在一些地方,对伦理的恐惧效应远远大于法律的强制性。我们常说,乡里人朴实、和善、热情,其实着眼的也是某种乡村伦理。美好的伦理秩序为人们对乡村的美好想象提供了文化和制度基础,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好乡村”。但在《生死十日谈》中,这种情况却有了尖锐的变化,比如婆媳间的伦理秩序,现在已经到了婆婆对儿媳逆来顺受的境地。作者说:“婆媳是天敌,这是千年古训,婆婆由媳妇熬成婆婆,生儿育女建立家庭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家庭秩序、生活习惯。媳妇由姑娘变成媳妇,把根从娘家拔出,移植到新的土壤的同时,旧有的生活习惯受到挑战,新的梦想也受到制约。”于是伦理冲突不可避免。在传统的社会中,这种伦理冲突总是以儿媳的归顺为结局,但在今天,举起了白旗的却是婆婆,甚至交出了生命。比如在“第一日”访谈中的于吉良的老伴儿就是死于对儿媳的恐惧。在“第五日”访谈中,周凡荣老伴儿跳了水塘也是缘于儿媳的跋扈和对未来生活的不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婆婆自杀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又都和儿媳无关,也就是说,她们在自杀之前都预设了自己自杀的另一个前提,以撇清和儿媳妇的关系,进而来维护这个家族的最后尊严。当然,作者也没有仅仅把这种伦理秩序的破坏停留在婆媳之间的关系上,像“第四日”访谈中的万家的三个儿子因共用妻子而自杀就涉及到了兄弟伦理,“第十日”访谈中的杨萍母亲的自杀、“第四日”访谈中,李琴、李燕母亲的自杀等涉及的都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伦理。应该说,伦理关系的变化和被破坏成了由“好乡村”变为“坏乡村”最大的秘密。
信念或者道德偏执成了“坏乡村”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乡村,对某种道德的恪守往往成为一些人一生最大的信念。在此情况下,信念与道德是合一的。特别是,当把愚昧也当作道德时,悲剧往往便会发生。在《生死十日谈》中,至少有一半目标人的死亡是缘于偏执的道德与信念的合一。而且问题的更为严重性还在于,他们的遗族虽然在亲人死亡后有所反省,但这种反省对他们接下来的人生仍然没有校正。比如,在“第二日”访谈中,徐大仙女儿赵凤的自杀就牵涉了多重的道德或者信念偏执。赵凤因丈夫杨柱在外打工,被抛弃十几年,偶然一次出轨却染上了性病。赵凤坚决不想离婚,她坚持的信念是“要人不要钱”,以至于自己最后走投无路,撒手西去。“要人不要钱”信念背后的道德理念是乡村中的“面子”和“不被人抛弃”要远远重于金钱所带来的实惠。可能赵凤自己也相信,只要在原来的信念上稍有放松,便会为自己带来更深刻的伤害。对这样的一个人物,作者感慨道:“一个留在乡村的孤独女子,在远离丈夫、一个人孤苦地打发日子的时光里,身体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和磨难。她不甘心痛苦,向自己的道德发起了挑战,最后却深受自己的不道德伤害。”我赞成作者的感慨,我想修正的是,赵凤并不是深受自己“不道德”的伤害,而是受到了“信念”与“道德”调整的伤害。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我们当下对“坏乡村”的想象并不一致,但实际上,只要站在一个有着深刻传统观念的女性立场上来体会,这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她的丈夫并没有因为赵凤之死而醒悟到什么。相反,他坚信人生的“狠毒”品性所带来的“豪情”和“仗义”,把“狠毒”看成了自己的优点。当然,赵凤也死于母亲徐大仙的愚昧。同样在“第九日”访谈中,成功的乡村女企业家杨萍坚信,替母亲看住父亲、去捉奸是为了这个家好,但却始终不承认正是这一道德偏执葬送了母亲的性命。其实,乡村剪纸艺术家大辫子丈夫“小老头”之死、大学生耿小云之死以及因与堂大伯哥“通奸”而导致丈夫自杀的“百草枯”的生存状况,无不是因为信念与道德的偏执所致。而当这种信念与道德关系稍一调整,这些人便会因为信念与道德坍塌或者走向死亡,或者自我封闭。这正是孙惠芬的追问“你和信念的关系发生了断裂,那你该怎么办”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当然,在“坏乡村”的秘密中,穷苦人对命运的顺从和无奈也是一条无法挣脱的绳索。命运既来自于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心理认知,同时也包含了因无法面对现实的物质条件而转化成的情感认知。 而后者又加剧了主体对所谓命运的顺从和无奈。在乡村,贫困和疾病往往是最主要的动因。在《生死十日谈》中,我们看到,至少有三人是因为疾病,为了不拖累子女和别人而选择自杀,也有多名受访者将亲人的自杀认为是命运所致,因相信“都是命”、“天就在上头”,所以“怎么办,没办法”。我们看到,在这些简短的慨叹和诘问中,包含了多么沉重的、无处诉说的痛苦啊!
《生死十日谈》中,始终穿插了现代化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我相信,这既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同时可能更是作者一种巧妙的穿插和结构。这样就使由对乡村自杀主题所带来的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和质疑变得更加有效和深入。但我要问的是,乡村变“坏”,自杀现象增多,是不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自杀者遗族的精神救赎,除了走进基督教堂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当然,这不是作者要回答的问题,而是需要“现代化”自身给出答案的。
———对话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