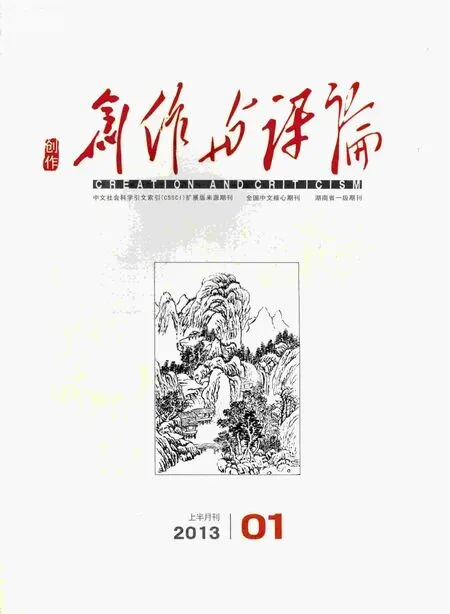小说三题(中篇小说)
○ 姜贻斌

大妹的鞋垫
大妹是想过我的。
大妹是队长的大女。
队长有高高矮矮四个女。
我插队住在队长的楼上,大妹常来楼上玩耍,这是自然不过的,不必担心有什么闲言碎语。她每回来楼上,总是一个人来,从不带妹妹们上楼。一上来就笑着说,小姜哎,你屋里像个牛栏屋哎。说罢,拿扫帚扫地,或是拿抹布这里抹抹,那里擦擦,好像她住在这楼上似的。有时候,弄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队里的人都叫我老姜,包括队长。
只有大妹叫我小姜,她说,哎呀,叫老姜难听死了,十六七岁人,哪里就老了呢?
我也不清楚是从哪天开始的,大妹对我就有点那个意思了。平心而论,大妹对我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除了打扫屋子,我每次换下的衣服,她就悄悄地拿去洗掉了。晒干之后,又叠得整整齐齐地送来,十分醒目地摆放在床铺中央。
我的楼房从来不锁门的,所以,她进进出出很方便。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弱点却很多,尤其是没有几斤狗力气,吃不得大苦,受不得大累。如果去河边的船上挑肥料,大妹自己挑一程,然后,又返回来帮我挑,她几乎是同时挑两担,工分却记在我的账上。望着她满身大汗,我很不好意思,有时拒绝她帮我挑,我说我慢慢挑就是了。大妹抢过我手中的扁担,直爽地说,你又挑不起,充什么卵狠呢?我来我来。挑起担子,匆匆地走。望着她的背影,我不由涌起一阵感动。总而言之,她好像是我的保护神,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劳动中,处处都帮着我,惟恐我吃不消。另外,我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最害怕蚂蝗了,如果腿上沾一条肉肉的棕色蚂蝗,我居然吓得抖抖地指着腿上,战战兢兢地说,大妹,快来。大妹一看,急忙弯下腰,一边说不要怕,一边将蚂蝗小心地从我腿上扯掉,扔得远远的,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这个该死的。
若是双抢季节,大妹去山上采金银花熬茶,然后,不厌其烦地将茶水送上楼来,灌入我的茶壶。我喜欢喝金银花茶,凉沁沁的,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茶壶是空着的。大妹还不时地叮嘱说,小姜,你要多喝茶嘞,鬼天气也太热了,容易发痧,茶水是解热的嘞。也多亏了大妹,双抢大忙,在火炉般的天气里劳动,我居然一次痧也没有发过。
有一回,队长叫我和大妹去县城买农药。平时,去县城买农药派一个人就行了,队长这次却派两个。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派两个,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走到半路上,看着走在前面的大妹,我才忽然明白,哦,这是队长故意安排的吧?他在利用手中小小的权力,为大妹和我制造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吧?
那天,大妹兴奋极了,挑着空箩筐,一路上滔滔不绝,忽而说小姜嘞,你看那座山像不像个菩萨?忽而说小姜嘞,你看那条河像不像一条腰带?忽而说小姜嘞,你看那片彩霞像不像一匹马?忽而说小姜嘞,那一丘田像不像个斗笠?
她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说实话,我心里并不是那么高兴的,又不愿意让她扫兴,就附和道,像,像,像,像。
到了县城,她并不急于买农药,叫我带着她到处看看。对于这个县城,我简直太熟悉了,我的家就在县城。县城其实很小,在大妹的眼里却很大,简直大得不可思议。为了满足她的心愿,我带着她去商店啦,电影院啦,造纸厂啦,磷肥厂啦。等等。其实,除了商店,其它的地方我们也没有进去看,只是站在大门口看看而已。大妹呢,却不时地发出惊叹,哎呀,这么多的人呀?哎呀,厂子这么大呀?哎呀,商店这么多东西呀?
大妹就是这样一路惊叹,让我感到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如果让熟人碰见,肯定会嘲笑这个妹子也太乡巴佬了。
幸亏没有碰上熟人。
走走停停,看过一些地方之后,我以为也差不多了。大妹似乎仍不满足,好像要把县城的角角落落看个遍,过一回足瘾。她不断地转过脸问我,反正时间还早,是不是还去哪里看看吧?
这时,我有些不耐烦了,看过这么多的地方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大妹今天格外缠人,难道要把县城的每一寸地方都看到吗?当然,我脸上没有流露出来,担心刺伤她的自尊心,所以,我漫不经心地敷衍说,哎呀,这个县城太小,没有什么地方好看的了。
她不相信,惊讶地说,难道没有地方好看了吗?难道就没有了吗?你再想想看?她张大眼睛望着我,提醒我。
我抓抓头发,装着绞尽脑汁的样子,然后,很无奈地说,真的,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好看的了。
大妹一听,情绪显得有些沮丧,不再说话了,极度的兴奋似乎猛地降到了冰点。
她忧郁地说,那……那我们去……买农药吧。
我带着她大步地朝农资商店走去,刚走到农资商店大门口,她竟然又转过脸问,小姜嘞,你再想想看,如果实在是没有什么地方好看了,我们就买农药好不?
我毫不犹豫地说,买吧,然后,回队里吧,还有几十里路呢。
大妹直直地望着我,好像一眼要将我的心脏穿透。她的嘴唇颤动着,欲言又止,似乎又不心甘,犹豫一下,最终还是说了出来,你……你难道不回家看看吗?
我一怔,恍然大悟。
哦,大妹其实一直在暗示我,其目的是要去我家看看。而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我不想带她去我家,即使我的父母没有意见,那些街坊也会有看法的,他们一定会嘲笑我,说我带一个乡下妹子来了。再者,我也不能让大妹去我家,这很容易让她想入非非,以为我对她的态度很明朗了。
我脑壳一转,赶紧撒个谎,说,哎呀,我爷娘上班去了,屋里没有人,再说,我也没有钥匙,进不去。
大妹疑疑地看我一眼,彻底失望了,眼神暗淡,二话没说,默默地走进农资商店,买了农药,挑着担子往回走。
在回去的路上,大妹不要我挑农药,也不跟我说话,闷头闷脑地走在前面,与来时的心态截然两样。我明白,她肯定是生气了,我也终于明白,她来县城的真实目的。她这次来县城,并不是想看什么造纸厂磷肥厂,她说要看那些地方,只是她一个巧妙的幌子罢了。其实,她最想去的就是我家,这是她的最终目的。我却像一桶冷水朝她泼去,残酷地让她的希望之火破灭,坚决地掐断了回家之路。我甚至怀疑,这很可能是队长夫妇与她共同酝酿的计谋,让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他们精心设计的圈套。
看见她老是一个人挑着担子,我也有些过意不去,这么远的路途,哪能让一个妹子老是挑着呢?再说,她平时都是帮我的。
所以,我试探地说,喂,大妹,我来挑一程吧?总是你一个人挑,要不得嘞。
她不理睬我,也不说话,仍然闷闷地走着。当然,让我放心的是,大妹的力气很大,丝毫也不比后生们差,这是有口皆碑的,她能够挑一百多斤,这点农药是不在话下的。也所以,我并不担心她挑不动,只是让路人看见,我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罢了。
大妹与她来的时候截然相反,一个是兴味盎然滔滔不绝,一个是郁郁不乐一言不发。
我默默地走在后面,心想,从现在起,她如果彻底地改变对我的态度,不理睬我了,那么,也是一件好事,这就怪不得我了,我也不必承担什么责任。
而事情的进展,谁又料得到呢?
那天,大妹看来真的生气了,一下都没有让我挑。当快走进村子时,听得见鸡叫狗吠了,大妹突然又兴奋起来,满脸笑容地说,小姜嘞,今晚你要来我家吃饭,我家还有一块腊牛肉嘞,我要我娘老子放点红辣椒粉,再放点大蒜,保证蛮好吃的。哎,你要陪我爷老倌喝一杯嘞。她闷闷不语的状态居然一扫而光,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我不由愕然。
其实,你们也能够看得出来,队长也是有这个意思的,想把大妹许配给我。当然,他还是比较含蓄的,讲究一些分寸。他肯定将我和大妹对比过的,觉得大妹比我差很多,如果万一谈不成,他这个做爷老倌的,还有一个体面的退路,不至于怎么尴尬。当然,他也清楚我家的情况不尽如人意,父母天天挨批斗,而我毕竟是县城的人,只是虎落平川罢了。
队长娘子的态度却很明显,丝毫也不掩饰对我的关心,一旦有了好菜,就派大妹叫我下楼来吃。这个时候,队长客气地说,你想喝酒,自己倒吧。队长娘子却不一样,满面春风,不仅亲手给我倒酒,还不断地叫我夹菜,甚至还亲自给我夹,夹得我碗里一堆的菜。我看得出来,大妹也想给我夹菜的,又有些不好意思,有点差涩,只是飞快地看我一眼,好像是鼓励我放肆吃。
有一天,我从家里回来,还没有走进队长家的门,在屋檐下,隐隐地听到大妹在大声骂人。我不明白她在骂谁,为什么骂人,大妹的脾气历来是很温和的。我没有立即走进去,赶紧刹住脚步,悄悄地站在门边听。
只听见大妹说,舅舅,你不要再说那个什么姓王的了,好不好?我是不会答应的。
她舅舅苦口婆心地说,大妹,我也是为你着想嘞,你也找得婆家了,小王的姑父还是公社干部,家庭条件不错的嘞。
大妹愤愤地说,他姑父哪怕是县里省里的干部,我也不愿意。语气十分的坚决,没有丝毫的余地。
说完,大妹忽然哭了起来,呜呜的哭声从屋里幽幽地传出来,湿淋淋地灌进我的耳朵。
我想,队长夫妇应该表态了吧?这是关系到大妹的终身大事。我却始终没有听到队长两口子说话,也许是他们不便说吧?舅舅毕竟是一番好意,做父母的如果表示反对,肯定会扫了舅舅的面子。当然,是否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已经在心里同意大妹跟我了吧?
此时,我倒是希望大妹能够答应下来,然后,选个好日子,让她舅舅带着那个姓王的后生来相亲,再然后,定亲结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轻松得多了,不必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顾虑了。这个大妹却非常固执,简直是寸土不让。她这种强硬的态度,很可能也惹火了她舅舅,后来,我很少看见她舅舅来了。
大妹不仅做得田土功夫,针线功夫也相当了得。像她这样的妹子,在乡村是很受男方欢迎的,如果嫁过去,肯定是个狠角色。平时,我的衣服破了,她就给我缝补。另外,她好像在不断地给我做鞋垫,我虽然穿着她的鞋垫,也只是一年两双而已。而我不明白的是,她哪里要做这么多的鞋垫呢?我看到她平时空闲了就不停地做,做得专心致志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问过她,她想做就让她做罢,也许,这是打发闲时的一种方式吧?大妹做的鞋垫,每一双的花纹都不一样,花样在不断地翻新,或是菱形的,或是波浪形的,或是长方形的,或是梅花,或是桃花,或是梨花,等等,可见她的手艺是相当不错的。
曾经有许多次,在楼上只有我和大妹。我们坐得很近,我记不得当时说过些什么话了,反正说得很开心。说着说着,只见大妹微微地闭上了眼睛,那种状态,很明显是让我在她的脸上打啵。当然,我很理智,不敢打啵,担心这一啵,会啵出许多的麻烦来,以后肯定难以脱身的。所以,我敷衍地说,大妹以后吧啊?我看得出来,大妹虽然感到十分失望,却也没有勉强我,她似乎同意我的意见,把打啵的浪漫放到以后,放到水到渠成之时。当时,我的确很胆小,甚至连大妹的手都不敢去摸,担心会摸出许多的麻烦来。
由此可见,我对大妹的态度是非常暧昧的,或者说,是很模糊的。其实,大妹并不明白我从心底里是不喜欢她的,对她没有一点感觉,而我又不敢说出来,倒不是担心说出来对于她来说过于残酷,而是担心我的态度如果过于明了——不论是迎合,还是拒绝——其结局都会令我不寒而栗。前者害怕到时甩不掉她,她会像蚂蝗死死地沾着我,后者是担心队长肯定不高兴,以后会想方设法地给我小鞋穿,更重要的是,他如果卡住我招工呢?
我不喜欢大妹的理由十分简单,她实在太矮了,一米五都不到,而且胖,胖得又不匀称。像这样的妹子,哪里会引起我的兴趣呢?我虽然是个知青,算个落难之人,而我的审美观和择偶标准,也不至于差到这种地步吧?其实,我喜欢的是另一个妹子,那个妹子叫李桃桃,李桃桃不仅读了高中,而且长得苗条,五官又十分的清秀。而李桃桃又不愿意跟我谈对象,她比大妹理性多了,她说我以后肯定会招工的,像我这种人是根本靠不住的,她说,她还是嫁给农村人比较现实。所以,李桃桃没有给我一丝希望。
总之,我和大妹这种含含糊糊浑浑沌沌的状态,保持了三年多,一直到我招工的那天。
招工对于每个知青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不论是去什么厂矿,毕竟是希望终于到来了,其兴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我到招工的那天,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和激动,我以为,队长一定会强迫我确定了与大妹的关系,才会放我走的。所以,我忐忑不安,十分紧张,以至于无法预料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
也就是那天,队长突然叫住了我。
当时,他坐在灶火边,火焰映在他的脸上,脸色很难看,似乎充满着怨恨矛盾和冷漠。他不说话,闷闷地抽着烟,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我吓得浑身起泡,意识到大事不妙。我晓得,招工的手续已经开始办理了,我这次能不能够招工,就是队长一句话,他如果不叫我去大队办手续,我又怎么敢去呢?我胆怯地坐在他的身边,一句话也不敢说,双手紧张地伸进大腿中间,不断默默地数着数,我不晓得要数到哪位数时,他才会张开尊口。我更不敢看他那难看的脸色,我的心高高地悬在广阔的天空上。
那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一刻,我却显得是那么的可怜和无奈。我默默地数着数,以此来分散自己紧张的心理。现在,我已经数到六千三百五十二了,队长还是没有表态,所以,我只好继续往下数。
我想,只要他不说话,我就一直往下数。
终于,漫长而沉默的过程结束了——当时,我默默地数到了九千五百六十二——队长终于说话了,他痛苦地咳了几下,口气非常冷漠,居然没有一丝祝贺的意味,好像是极不情愿地很快地把要说的话说完,所以,是一字一句地说的,他说,去—大—队—李—秘—书—那—里—办—手—续—吧。
我一听,赶紧站起来,压抑着满腔的喜悦,低声哎哎地应着,态度极其谦卑。然后,我真诚地说了一声谢谢,飞快地跑了出来。我似乎生怕队长反悔,然后,像一只快乐的小鸟,飞舞在一条条狭窄的田基上。我明白,这句话能够从队长嘴里说出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又是多么的艰难。
我走的头天晚上,大妹来到楼上,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流泪,一直流到深夜。如果不是我催她去睡觉,她一定会流到天亮的。她一定明白,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再也没有一丝希望了。望着大妹,当时,我是有一种冲动的,想在她的脸上啵一下,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而我又担心惹事生非,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
第二天,我以为她会来送我的,等了许久,却连她的人影子也没有看见。
在我的楼房门口,不晓得什么时候摆着一迭厚厚的鞋垫,整整齐齐的,摆在最上面的那双鞋垫,绣的是盛开的桃花。
默默地望着它们,我顿时明白了什么,也许,大妹早就预料到有这么一天了吧?
小英的婚事
小英这个妹子,性格非常固执,或者说非常要强。
下面顺便举两个例子——
其一,那年双抢,村里的几个妹子斗狠,小英也是其中之一。她们商量说,今天每人插一丘田,谁先插完秧谁先回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想想,还是有问题的,那些水田大小不一,面积不可能是一样的均匀,又不可能把那些水田用刀子划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再进行公平的比赛——那只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做法罢了。所以,她们采取了乡村最常见的办法——拈勾。谁拈到面积小的,就算她走运,谁拈到面积大的,只能说她背时。小英的手气不好,居然拈到了一丘最大的。对此,小英也默认了。然后,妹子们各自马不停蹄地插起秧来。她们的动作非常快迅,手像鸡啄米似的,将一蔸蔸绿色的秧苗插进浑浊的水田。隔远一看,那一行行绿色的秧苗,就像是从她们屁股里排出来的。她们争先恐后,从早晨一直插到太阳落山,那几个妹子的田都插满了,小英的那丘田呢,还远远地没有插完。其实,这个结局也完全在她们的意料之中的,小英插的那丘田面积大许多。别的妹子见天色不早了,终于心软了,站在田基上劝小英,小英小英算了,你那丘田本来就大些,我们还是回家吧。小英根本不理睬,翘着屁股继续插,一直插到午夜。
其二,队长有次说,你们这些妹子如果谁掮起了水车,我就给她加一分。那天,队长本来是嘴巴没有味了,分明是开玩笑的,他能够预料到,没有哪个妹子能够掮起水车的,掮水车的只有男劳力。那时,男劳力一天十分,女劳力一律六分。如果每天能够加一分,一年下来就很可观了。当时,小英认真地问队长,哎,队长你说话要算数嘞。队长听她一说,也认真起来,拍着汗毛胸部说,我几十岁的人了,哪里还哄过人呢?小英指指身边许多的人,说,这么多的人可以作证的,到时候,不要说没有听见队长说的话。众人说,这个我们能够作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嘞。小英果然也当真了。从那天起,只要有了空闲就练习掮水车。掮水车,也不是说掮就能够掮起来的,它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技巧。就说我吧,插队这么久了,也不敢掮水车,一是担心摔坏水车赔不起,二是没有力气,害怕闪伤了腰子,害了一辈子。小英却十分的要强,许多人劝她不要掮了,说如果摔坏了水车,或是伤了腰子,都是个大麻烦,再说,你屋里也不靠你加上那一分。她偏偏不听别人的劝说,硬要学着掮水车。所以,在那段时间里,一旦有了空闲,小英就站在保管室的屋檐下,咬着牙齿掮水车,还虚心地向男劳力请教,一招一势的,很有章法。其实,那些男劳力虽然也教她,心里却抱着一种看把戏的态度,背地里还说,小英如果把水车掮起来了,那狗都不吃屎了。小英却不服狠,还是咬紧牙关掮,后来,水车终于让她掮了起来。那天,她掮着水车,稳稳当当地走到队长的屋门前,大声叫喊,队长,你快出来看,我是不是把水车掮起来了?队长走出来一看,叹道,哎呀,你这个妹子真是的,太霸蛮了嘞。队长终于认了输,只好给她加了一分。
那年,小英已经不小了。
其实,乡下人说的不小,也就是十八九岁。按说,妹子一般在十五六岁就找婆家了,定亲了。家里人也先后给小英找了几个,她却一个都看不上,看不上也就不说了,甚至还没有好脸色给别人看,瞟着两道特务似的目光,冷冷地站着。为此,她娘老子只差点没有给她下跪了,求她说,小英嘞,人家来相亲,你要放客气一点嘞,何况,你给人家筛茶,人家还要放茶钱给你的嘞,至于谈不谈得成气,那是要看缘分的,而的你茶钱反正是到手了嘞。
小英却跟别的妹子大不一样,不想去贪人家的茶钱,她并不看重钱,而是看重人。如果相亲的后生来了,她不是大方地笑着跟人家见个面,打个招呼,试探着说些闲话,相互摸摸底细,然后,再从长计议。她却是躲在睡屋里面,偷偷地从门缝朝坐在堂屋的拘谨的后生看一眼,眉头忽地一皱,就皱出许多的不满意来,然后,干脆躲着不出来了。你说人家是来相亲的,妹子如果不出来,这又是哪里的规矩呢?难道让别人白走一趟吗?她的父母显然很尴尬,大声叫她,小英小英,快出来嘞。心想,她如果不出来,就要拖她出来,不信她今天不亮相。然后走过去,嘴里还在叫小英。谁知推开门一看,睡屋里面却是空空的,没有人影子了。原来,小英早已从窗户上逃走了。
对此,我疑惑不解,也曾经问过小英的。我说,你这个后生也不要,你那个后生也不要,你到底要嫁个什么样的后生?
小英也很直爽,毫不隐瞒地说,起码要嫁个吃国家粮的。
我觉得,小英是个心气很高的妹子。
后来,固执的小英却碰上了一个固执的后生。
那个后生是杨家坳上的,叫杨国生。杨家坳上离我们村子有八九里路,不远也不近。那个姓杨的后生我也看到过。实话说,长得还是蛮不错的,一头黑长发,多少像个有文化的。人也很拘谨,显得很忠厚,不像有些后生油腔滑调的,张扬得过分。当然,有句话我不便当着小英说,担心伤了她的自尊心。如果依我之见,那个姓杨的后生比小英强多了,我指的是各方面。仅仅说长相吧,小英的长相其实并不怎么出众,蒜头鼻子,脸皮又黑,嘴巴皮还有点厚,根本谈不上什么乖态。当时,我还怀疑,这个杨国生怎么这样愚蠢呢?那么多乖态的妹子不去找,怎么偏偏看中了小英呢?其实,他是完全能够找到比小英强两倍或是强五六倍的妹子。
而对于这门亲事,小英仍然不答应。
不答应的理由,居然是嫌姓杨的是农民。
这难道不是在说笑话吗?你小英不也是农民吗?你又有什么理由嫌弃人家呢?再说吧,找对象是要讲缘分的,也是要讲机会的,过了这座山,就没有那道坳了,盛开的花朵就会凋谢了,如果没有找到吃国家粮的,你小英是不是不嫁人了呢?
所以,我也十分着急,好像小英是我的亲妹妹,眼看着这朵鲜花快要凋谢了,我就耐心地劝她。我说那姓杨的后生蛮不错的嘞,又是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你如果嫁给他,肯定没有亏吃的。我还说,姓杨的后生看来有点文化嘞。小英听罢,仍然不愿意,耳朵根本不进油盐,居然信誓旦旦地说,老姜,我已经下了决心,如果不找个吃国家粮的,我绝不罢休。
小英不愿意谈这门亲事,她的父母却很愿意。她父母已经让小英气过许多回了,也难堪过许多回了,所以,这次也下了死决心,小英不愿意,他们做大人的愿意,如果继续任着妹子的脾气,一拖再拖,拖到年纪大了,拖到皮肉起霉了,那么,狗都不会来闻的。所以,她父母擅自做主,不管小英答不答应,杨国生他们是要定了的,甚至叫杨国生经常来走动,他们就不相信女儿永不回头。杨国生也就听了小英父母的话,虽然心里有点不舒服,大概觉得能够找到小英这样的妹子,也就很不错了。她虽然现在还不答应,他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人心是肉长的,他相信自己会慢慢地打动她。所以,杨国生经常来走动,并且使出了水滴石穿的功夫。
杨国生是很会做人的。
每次来,他要给小英家送些礼物,或是一条鱼,或是一只鸡,或是一刀肉,那些礼物上面还要贴上一小绺红纸条,以示郑重和客气。后来,他听小英的父母说过,说小英最喜欢吃虾米了,杨国生就不辞辛苦地去河里捞虾米,捞到虾米,马上提着篮子活蹦乱跳地送过来。
小英却很倔,晓得虾米是杨国生送来的,从来也不尝一口,筷子根本不往那个碗里伸,好像桌子上没有浑身通红的辣椒炒虾米。杨国生虽然愕然和尴尬,却不吱声,默默地忍受着,一口一口地吃饭。加之,有小英的父母在稳住他的心,他也就没有把愕然和尴尬流露出来,更不是一气之下走人。有小英的父母做他的坚强后盾,所以,他显得很有底气,竟然百折不挠,甚至一如既往地送虾米来,也不管小英吃不吃,反正,他的心意算是彻底地到位了。
杨国生这个人真是蛮不错的,不管小英松不松口,对他是什么态度,他甚至还不辞辛苦地帮着小英家做事,简直像个上门女婿。每回来,杨国生也不歇口气,进屋打个招呼,就扛起锄头,或是挑着粪水,去挖土,或淋肥,每回累得满头大汗。村里人谁不夸这个后生呢?他们都晓得,小英的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就纷纷说,像这样的后生,真是太少了嘞。甚至还指责小英太不懂事了,说她的心比铁还要硬。小英的父母亲,当然是非常满意杨国生的,每回看见他来了,就背着小英狠狠地恶骂小英,说她简直是瞎了眼睛,脾气像牛牯一样犟。杨国生听了,只是微笑,轻轻地说,不要骂她。好像心里早已有了底案,相信小英一定会慢慢地转变过来的。当然,小英父母还劝杨国生不必性急,说这样的事得慢慢来,性急吃不得热豆腐,他们一定会叫小英回心转意的。所以,杨国生也就铁了心,坚定不移地来,十分勤快地来,提礼带物地来,还笑着附和地说,对了,慢慢来吧。
小英好像有什么预感,因为杨国生每次来了,她基本上就不在屋里,也不回来。开始,她还在屋里吃饭睡觉,并不回避杨国生。现在呢,大约是看见杨国生的脸皮太厚了,他已经和自己父母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了,所以,她也采取了更为断然的措施。只要杨国生来了,小英就不再在屋里吃饭睡觉了,那到哪里吃呢?她不是在张家吃饭,就是在李家睡觉,总之,与杨国生避而不见,眼不见为净。她不担心没有地方吃饭,也不担心没有地方睡觉,她有一伙蛮好的女伴,女伴们都晓得她的心气很高,非一般人不嫁的,也就十分理解地接纳了她。
我经常看到杨国生在小英家的菜地忙碌,像愚公般的挥汗如雨,所以,心里也隐隐地生出一丝怜悯和同情。像杨国生这样提前为岳父母拼命卖力,真是可以作为一种典范的,难道小英的心是铁打钢铸的吗?看到杨国生这样年轻的活愚公,难道丝毫也不为之动心吗?当然,这本来也不关我的卵事,小英愿不愿意嫁人,需要她自己点头才算数的。我这是咸箩卜操空心,实在是看不过眼了。后来,我对小英感叹道,小英啊小英,像这样的后生,真是打起灯笼也难找的嘞。
小英却毫不领情,愤愤地说,累死活该。
当然,小英还算是不错的,她一直对杨国生采取回避态度,并没有直接跟杨国生发生过任何正面冲突,这就避免了许多的难堪,以及不必要的口舌。看起来没有硝烟弥漫,没有刀光剑影,双方都在以婚姻的名义,默默地打着一场坚韧之战。杨国生真是固执得可爱,仍然掉在未来婚姻的梦想之中不能自拔。他天真地以为,小英的脑子哪天一定会开窍的,就像阳光终会从层层乌云后面万丈光芒地照射下来。所以,他仍然照来不误,在那条八九里路的小道上来来回回,好像已经把这里当做第二个家了。
这一切,小英也随他去了,并不干涉这个顽固不化的后生,任他马不停蹄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任他挥汗如雨地像个活愚公,任他不断地来向自己的父母献殷勤,反正只要自己不松口,把嘴巴紧紧地守住,这桩婚姻肯定就没有戏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国生这个年轻的活愚公,在称呼上居然也起了变化,喊小英的父母不再叫伯伯伯母了,已经改叫爷娘了,竟然叫得大大方方,自自然然,一点也不生涩,或者害羞。小英的父母倒没有什么意见,咧开嘴巴,乐哈哈的,想来这种喊法,也只是迟早的事了,杨后生想喊,就让他喊吧。所以,不论是喊的还是跟应的,双方都高兴。当小英晓得这事之后,气愤极了,有一天等到杨国生走了,回来冲着父母大骂,是谁让他这么喊的?他凭什么这样喊?真是死不要脸,脸皮比牛皮还厚嘞。
骂得父母不敢做声。
她的父母一想,也是觉得有点亏理,他们毕竟还没有成亲,甚至连订婚也是遥遥无期,凭什么就喊爷娘呢?
那天晚上,小英骂过了,还砰地摔烂一个茶碗,粉碎的白瓷片绽放在地上,像一片雪花。
后来,小英终于忍无可忍了,不愿意让这种似是而非的局面继续下去了,也没有耐心打坚韧战了,她要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了。当然,她做得很沉着,并没有声张,更没有提前把这个消息发布出去。她悄悄地向那些女伴借了军装军帽和皮带,还借了一个红袖筒,红袖筒上印着红农兵三个黄色的大字。当时,这些行头并不难借,那个时候,每个村子都备有这些行头,演样板戏需要。女伴们问她借这些东西做什么,小英说,她要演一曲好戏。问她究竟要演一曲什么样的好戏,她又不说。
没过多久,杨国生又来了,汗水涔涔的,手里仍然提着鲜活的虾米。那天,小英的父母走亲戚去了,只有小英在屋里。杨国生哪里又晓得呢?一脚跨进门槛,就亲切地喊爷娘。谁料没有人应答,又高喊一句,小英的父母也没有出现,却把小英从睡屋里叫出来了。
杨国生抬头一看,呆住了。
只见小英一身军装,头上戴着军帽,腰里束着宽大的皮带,手臂上戴着红袖筒,英姿飒爽,且双眼怒瞪。她连招呼也没打,大声地喝道,姓杨的,你以后再也不要来我屋里了。
杨国生见小英这副严肃的打扮,又是这种愤怒的口气,一时胆怯起来,困惑地问,为什么?
小英继续愤怒着,说,你晓得你舅舅是什么人吗?哼,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你——她伸出一只手指向门外——现在,你赶快给我滚出去。声音铿锵有力,像铁锤一锤一锤地敲出来的,不容人有丝毫的迟疑。
这一番话,把杨国生吓得说不出话来,呆呆地望着冷漠愤怒的小英,提着的虾米叭地掉落在地,虾米们却全然不顾屋里紧张的气氛,一只只活蹦乱跳的。杨国生终于明白了什么,怔了怔,赶紧灰溜溜地逃走了。
再也没有来过。
小英的父母见未来的女婿没有来了,觉得很是奇怪,杨后生是不是生病了呢?想托人去问问,又没有人去杨家坳上,就很迷茫地问小英,国生怎么不来了?
小英心里很高兴,他娘的脚,这场坚韧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当然,她还是很沉得住气的,没有流露出一丝胜利的喜悦,只是不耐烦地说,我怎么晓得呢?
小英的父母觉得这件大事结束得有点奇怪,两人就去了一趟杨家坳上。在杨家的菜地,他们见到了仍然很愚公的杨国生,心想,呃,这个后生没有病么。然后,小英的父母担忧地问他为什么不来了,杨后生的态度仍然是很不错的,只是没有喊爷娘了。他抹了一把汗水,就很惭愧也很老实地把原因说了出来。
小英的父母听罢,也怔住了,半天没有说话。
小英虽然终于痛逐了杨国生,而当她与我说起这件不了了之的事情时,眼睛居然湿红了。她难过地说,老姜呀,其实呀,我也不是铁板一块呀,人心毕竟还是肉做的呀,对于他呀,我也不是没有动过一点心的呀,我也想过的呀,只要他对我好呀,不吃国家粮就不吃国家粮呀,而你不晓得呀,他舅舅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呀。
我猛然一惊,心想,哎呀,原来如此呀,且不说他舅舅曾经是国民党,就说我父亲吧,他老人家年轻时曾经稀里糊涂地参加过三青团,现在已经搞得惨兮兮的了。
问,你怎么晓得的呢?
小英很自信,言之凿凿地说,我早就调查过了的呀。
噢。
小青的假期
在村里,我虽然十分孤寂,也不去满五娘屋里,满五娘是个孤寡老人,去她屋里玩耍又有什么味道呢?想必也是冷冷清清的,一点闹热也没有。况且,我跟她年纪相差太大,几乎无话可说。再者,听说她的成分太高,过去是地主的三姨太,曾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所以,我也不想跟这样的人来往,以免引起别人不必要的猜疑。
那个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后来,我竟然去她的屋里玩耍了,而且去得很勤快,像泥鳅斗水,斗一回,又斗一回,似乎没有什么顾忌了。对于这个异常的情况,你一定会感到很奇怪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凡事都有它的起因。
满五娘屋里忽然来了一个妹子,叫小青。
小青大约十五六岁,是满五娘的小侄女,还在读书。每次到了假期,小青就背着书包,提着绿色的网袋子,来满五娘这里住个几天。原因很简单,小青的父母不想让满五娘太孤单,所以,叫小青来陪陪她。
小青看来是个心气很高的妹子,来了之后,似乎看不起村里人,好像跟村里人有某种隔阂吧,反正是不怎么来往的。她如果不跟大人们来往,我还是能够理解,一个小妹子,跟大人们又有什么话说呢?问题在于,她跟与年纪一般大的妹子也不来往,见面既不笑,也不打招呼,目不斜视,像一只高傲的天鹅,所以,对于那些雀鸟之类,就没有放在眼里了。惟独看见我,她的眼睛唰地亮了一下,像两只在黑夜中突然亮起的电灯。我的眼睛也唰地亮了一下,也像两只在黑夜中亮起的电灯。
那是在井边挑水时,她挑着水刚好离开,我挑着水桶往井边走。在狭窄的小路上,我们初次相见,所以,双方的目光碰上了,突然唰地亮了一下。当这个陌生的妹子与我擦肩而过时,我转过身子,望着她苗条的背影,很遗憾没有及时地赶来,如果赶来了,我可以帮她打水,跟她说说话,还可以帮她挑水回家。
所以,我非常明白,自己失去了一个接近她的最佳机会。
直到这时,我才晓得满五娘屋里来了一个很清秀的妹子。只是她从来不乱走动的,规规矩矩地呆在屋里,像个怕丑的妹子。我觉得这个妹子很不错,跟村里的那些妹子不一样,那些妹子的眼睛和脸上都是呆滞的,像刚病过的一样。她身上呢,却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脸色光泽,润滑,尤其是她的眼里,有两股水一般的灵气,显得透亮而聪明。
我很想接近接近她,跟她玩耍。
我又不便冒昧地去满五娘屋里,我以前根本不去的,也不想去,其中的原因,在前面已有了说明。如果我现在突然去,满五娘肯定对我很反感的,她会想,哦,你平时不来,或是不敢来,看见小青来了,你就来劲了哦。
所以,我心里还是有一定的障碍。
又很想跟小青玩耍,即使她比我小三两岁。
我认为,跟这样的妹子玩耍,心里头会感到十分的舒畅。我还觉得,她呆在屋里一定是不好玩耍的,陪着那个老妇人,玩什么耍什么呢?年龄相差也太大了。如果有我在的话,她肯定就好玩耍了,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许多的话说,也会想一些游戏玩耍的。我却没有更好的理由顺理成章地打进满五娘屋里,所以,我只好故意在她的屋门口走来走去,好像在散步,也好像在思考问题,当然,也好像是在看槐树上的喜鹊。总而言之,我出现在她的屋门口,是希望小青能够看见我,然后,叫我进去坐坐。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显得很自然了,没有尴尬,没有难堪,也没有拘谨。而让我感到特别失望的是,满五娘的那扇门,虽然是大打开的,却没有出现过小青那张青春的面孔,从外面看去,屋里面黑鸦鸦的,似乎弥漫着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迷雾和少有的空寂。
我不心甘。
我想,小青肯定会出现在门口的,或是看看外面的风景,或是出来透透气,她每天呆在空荡荡的屋里,一定是索然无味的。她耐不住那种清静,她不像她的姑妈。
有一天,我又故意走过满五娘屋子,碰见小青竟然站在门口,怔怔地看着那棵老槐树,她在用目光捕捉那只躲在树上唱歌的喜鹊,喜鹊清脆的叫声不绝于耳,像乡间一个充满山野之气的歌唱家,放肆而毫无顾及。这时,她往树上射去的目光忽然降了下来,不经意地落在我的脸上,目光中先有几许惊讶,然后,变成了一丝惊喜,还咧开小嘴对我微笑。我赶紧笑了笑,近乎于有点讨好的意思。我意识到自己的笑容很不自然,却的确是发自于内心的,只是不应该加上讨好的成分。让我感到微微恼火的是,她并没有说话,也没有示意我进屋里坐,然后,像一只鸟忽然消失了。
显而易见,她不便自作主张叫我进去吧。
这道门槛,分明成了阻碍我们来往的一堵隐形的墙。
第二天,我去井边挑水,看见小青站在路边歇气,桶里是满满的水,她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大胆地笑着说,哎,你挑不起吧?
小青轻轻地嗯一声,好像有点羞涩。
我没有犹豫,老子得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我马上放下肩上的水桶,拿过她手中的扁担——她并没有拒绝——挑起水往满五娘屋里走。她跟在我的后面,低着头,似乎害怕别人看见。我倒是没有什么顾虑,挑着水,悠悠晃晃地走进她屋里,利索地把水倒进了水缸。
这时,满五娘从猪栏里走出来,一眼看见我,有点惊讶,然后,满面笑容地说,呃,哪里还要麻烦你呢?她狐疑地看着小青,小青赶紧解释说,姑妈,我突然肚子痛,挑不动嘞。
我没有说什么,放下空水桶。
我明白,万事开头难,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此,我和小青的交往,将会徐徐地拉开序幕。满五娘没有叫我坐,小青也不便说,所以,我也没有停留,满怀信心地走出来,并不计较这一时的得失。
小青说,你要来耍呀。她站在门口,扬起舒展而光泽的脸,一点也不像肚子痛。
我顿时感到满身清爽,说,我明天会来的。心想,哎呀,小青真是一个鬼精精,她哪里肚子痛呢?她只是找个借口,制造一个机会留给我。
由此可见,她实在比我聪明多了。
从此,我就名正言顺地去满五娘屋里玩耍了。满五娘对我很好,每回看见我来,就叫小青,小青呀,老姜来了嘞。
小青还以为是谁来了,从睡屋出来一看,立即嗬嗬直笑,说,姑妈,人家才多大呀,你竟然叫他老姜,难听死了。小青笑得眼睛眯起来,像被强烈的阳光耀花了。
满五娘也笑,说,村里人都是这么叫的,我也改不了口。
小青撒娇地说,别人怎么叫我管不到,姑妈,你不能这么叫嘞。
满五娘让了步,说,好好好,叫小姜可以吧?
仅凭这一点,小青就足以让我感动,虽然男女老少都叫我老姜,甚至,连半大的细把戏也叫我老姜,我也不反感,早已习惯了。而小青这么说,的确让我很感动,她让我得到了我应当得到的恰如其分的称呼。
后来,小青只要见我来了,就大叫,姑妈,倒茶。或者说,姑妈,炒瓜子。或者说,姑妈,拿红薯丝来。看见她大大咧咧地指挥她的姑妈,我觉得非常好笑,小青真是来做客的,自己什么事也不做,把个老姑妈指挥来指挥去的,好像姑妈是她手下的兵喽喽。好在她姑妈并不跟她计较,小青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很顺着小青的。
我看得出来,满五娘没有崽女,很痛爱这个小侄女。
我经常来满五娘屋里玩耍,心里没有任何的顾虑了,我已经顺利地取得了通行证,满五娘那道高高的门槛已任我成功跨越。有时,小青居然叫我告诉她做作业——我明白,她这是不愿意冷落我——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我肚子里还有几滴残存的墨水,教她还是绰绰有余的吧。我每每帮她解开一道难题时,小青就要舒展微皱的眉头,高兴地惊叫起来,拍手称快,哈哈,又攻克了一座堡垒。小脸上兴奋地泛起淡淡的红晕,然后,竟然痴痴地看我。她的目光很清澈,十分单纯,又有几许迷离,像一把无形的鹅毛扇轻轻地拂在我的脸上。我当然喜欢她这样看我,这让我感到十分得意和满足。她并不是偷偷地看我一眼就马上把目光移开,居然是无所顾忌的,久久的,痴痴的,好像要将我脸上的细菌也一粒粒地查看出来。
每次,我都把脸乖朝着她,坦荡地微笑着,让她看个饱。
小青每次来她姑妈这里,一般只住几天,五六天,七八天不等。所以,我很珍惜小青在村子的那几天时间,我只要有了空闲,就往满五娘屋里钻。像这样钻进钻出的,你如果猜测我跟小青会发生什么故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什么故事也没有,两人就是说得来,我们在一起,都感到舒畅和愉悦,另外,还有一点小小的默契。她想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话,我想做的事,就是她想做的事。
对于这一点,我们暂时都无法解释,只是会心地笑笑。
小青每次离开村子时,都是依依不舍的,嘟着嘴巴咒道,这个鬼日子过得太快了,像飞一样的。
我也无奈地叹息说,是呀,太快了。
我总要默默地送她一程。此时,两人的心情已不太愉快了,黯然无光,好像是最后的诀别。
小青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幽幽地说,哎,我走了,你会想我吗?
我说,想。
我说,我希望你不要走,你多住几天吧。
我说,我希望你搬到你姑妈这里来。
我说,那我们每天能够在一起了。
小青听罢,情绪低落地说,那是不可能的嘞。
小青也舍不得走,脚步慢吞吞的,一步,一步,再一步,像在仔细地丈量弯曲的路程。她一直走到了桥头,才说,我走了。低着头,走几步,又转过身向我挥挥手,然后,向前走去。
我站在古老的小桥上,望着她背起书包,提着网袋子慢慢远去,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
所以,在下一个假期尚未到来之时,我的心情十分黯淡,几乎天天都在猜测,不晓得此时的小青在做什么,是在静静地看书?是在悠然地放牛?或是跟她的伙伴玩耍呢?她告诉过我,她家住在牛山河,离我的村子足足五十里路,没有车。其实,五十里路并不可怕,我是可以去看她的,即使我能够去看她,也令我感到十分为难,我难道走到她那里,看看她就马上离开吗?我怎么对她的父母解释我来看她的理由呢?凡此种种,让我踌躇再三,怎么也拿不定主意,惟有天天在心里数着那些漫长的日子,把厚厚的昼夜一页页地翻过去,翻着翻着,我居然一点耐心也没有了,翻得焦急而狂燥。而那些日子,偏偏跟我做对似的,我明明已经把它们翻过了许多,仔细查看,后面仍然堆积着厚厚的一沓。
惟有等到假期到来,小青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才清醒地明白,那些堆积着的厚厚的日子,终于被我又一次翻完了,我和小青高兴得跳跃起来,两人似乎很想拥抱,又顾忌什么,就激动地打着手板,显得极其兴奋。我们甚至忘记了问候,忘记了说话,像细把戏一般,响亮地拍打着手板,直到把对方的手板打得绯红,像两皮熟透的枫叶。
这就是我们相见时的方式,很有分寸,当然,也足以表达了我们快乐的心情。
满五娘不太管我们,任我们聊天,或是摆着算盘打九九归一,或是做作业,间或去山上玩耍,她忙着切猪草,喂猪,打鞋底,缝补衣服,淋菜,煮饭菜,或是做其它的杂事。她似乎并不反对我和小青的来往,有了我,她的侄女不至于寂寞和孤单了,有了我,她的侄女在学习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不遗余力地把肚子里那点残存的墨水泼撒出来,点点滴滴地泼撒在小青的头脑里,点点滴滴地泼撒在她的作业本上。
有一次,满五娘叉开双腿,坐在堂屋切猪草,嚓嚓的声音很有节奏,声音里含有青草嫩嫩的气味,不时扑面而来。我和小青坐在桌子边,我在教她做作业。我们跟满五娘相距不远,大概四五米远吧,她是面对着我们坐的。满五娘一直低着头切猪草,神情专注,好像在欣赏从刀下切出来的节节翠绿,也好像忘记了我们就坐在她的对面。所以,当满五娘于不经意间抬起脑壳时,眼睛随便扫了我们一眼,突然发现小青手里拿着笔,正在痴痴地看我——她这样看我已成了家常便饭,只是满五娘没有发现而已——满五娘忽然显得慌乱起来,甚至是不满,然后,故意将菜刀咣当地丢在脚盆里,似乎用这种特有的方式提醒小青,叫她不要用那种异样的目光看我。
小青却全然不顾,依然一动不动地痴看我。
其实,我也是于无意间才发现满五娘的目光的,那不满的目光陡地让我惊悚不已,像她手中的菜刀唰唰向我雪亮地飞来,我立即别过脸,故意看着空荡荡的门外,好像并没有接受小青的痴看。同时,我忽然有了不妙的预感,满五娘一定会阻止我与小青继续来往的。
当时,我想暗暗地扯一下小青,或在桌子底下踢她,提醒她不要继续痴看我了,而在满五娘那近乎于敌意的尖锐的目光下,我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都将彻底暴露。我心里的焦虑简直无法言说,我甚至想突然跑出去,暂时脱离这个窘境,又觉得过于突兀。小青呢,这个蠢妹子,似乎没有听见姑妈丢下菜刀的声音,也不在乎刀声为什么不继续响亮了,更没有注意姑妈那不满的眼光。
这时,我急中生智,马上抽身而出,说要去上茅室了。然后,赶快躲避这个无声而让人担忧的境地。
不出我意料,有了这一次,满五娘果然对我的态度冷淡起来,即便是笑,也是佯装出来的,不再是那种自然的微笑了。我呢,如果再来满五娘屋里,心里无端地生出了一种畏惧感,像个贼牯子似的缩手缩脚。与小青说话时,我十分的紧张和拘束,居然前言不搭后语,吞吞吐吐,好像害怕谁来抓我似的。
小青并不晓得其中的内幕——我也不便向她解释——她张着迷惑的眼睛看我,说,哎,你怎么啦?
我装着很平静地说,我没怎么呀?
小青嘀咕道,那你怎么像被鬼捉到的呢?
我没有回答,飞速地朝站在灶屋门口的满五娘瞟一眼,她的目光尖锐地朝我射来,让我不寒而栗。
小青显然看到了我的目光转向她的姑妈,还以为我是害怕她,转过脸说,姑妈,你不要站在那里看我们好啵?
满五娘没有说话,这才像幽灵般无声地消失,消失在挂满黑色灰线的灶屋。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够恢复到过去那种自然的状态。我明白,满五娘开始对我十分警惕了,误以为我居心不良,在悄悄地勾引小青——其实,是小青喜欢痴看我的。所以,我已经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担忧和害怕,又无法不去看小青,如果不看她,心里像有了一个空缺,似如一片翠绿的秧田扯走了一大块,而这空缺的一大块,是什么东西也不能够弥补的。
——我竟然也是这样的无可救药。
我晓得,这次离小青走的日子只有三天了。
那天晚上,我吃过饭,又去满五娘屋里。堂屋没有人,摆在桌子上的油灯,在透明洁净的灯罩里稳稳闪亮,并不害怕夜风鲁莽地干扰。我静静地站一阵子,想等着小青走出来,却没有见她出现在堂屋。
这时,我听见厢屋有人说话,侧耳一听,原来是满五娘在悄悄地对小青说话,她说,蠢崽,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老姜好嘞。
小青说,人家是小姜,姑妈你说吧,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好呢?
满五娘说,哦哦,是小姜,你问为什么?我告诉你,他出身也不好,是大地主嘞。
哦——小青长长地一声,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意味。
此时,我像被人揭穿了一个巨大而丑陋的秘密,浑身似乎长满了铁刺,刺得我疼痛难受,满面羞愧,我再也没有勇气呆下去,悄悄地溜了出来。
第二天,小青也没有叫我去玩耍了,即使在挑水时碰见,她竟然也不理睬我,眼皮怯怯地一耷,就匆忙地走开了,十分害怕我似的。这个巨大的变化,让我一时难以承受,想一想,又有几分理解。当然,我也没有叫她,默默地看着她的背影慢慢消失。
在我后来插队的日子里,不论是放寒假,还是放暑假,小青再也没有来满五娘这里了,好像在这个世上消失了。我不便问满五娘小青为何不来了,即便问她,她也未必回答我。后来,满五娘如果有了什么病痛,也只见小青的父母急匆匆地赶来。
小青呢,再也没有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