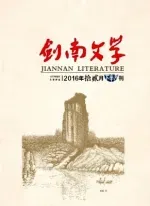杜甘反战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喻佩瑶
法兰西民族崇尚自由。为了自由,他们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尤其是在国家面临危难、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英勇的法国人民奋起反抗,众志成城,由此产生的反战小说熠熠生辉,璀璨夺目,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最为重要的部分。
法国的反战小说题材丰富,历史悠久。回顾这些反战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反战小说的形式虽然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从未中断。20世纪末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反战小说,其中马尔克·杜甘的作品不多,但成就突出,其风格独树一帜,尤其引人注目。为了表达对在战争中负伤而毁容的祖父的敬意,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发表了视角独特的处女作 《军官病房》,前所未有地把毁容军官这一特殊群体作为写作题材,探索战争带给个体从肉体到心理造成的巨大创伤。1998年这部小说在拉泰斯出版社出版,印了35万册,获得了书商奖、尼米埃奖和双猴奖等18项文学奖,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且被著名导演弗朗索瓦·杜贝隆搬上银幕。这部影片入围第54届戛纳电影节,“获第27届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男配角、摄影、服装等八项提名,获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奖”。总的来说,不管是小说还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杜甘的第三本小说《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于2002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更是一篇反战杰作。小说描写了一个普通青年的冒险经历和感情生活,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荒诞,表达了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出版后,评论界大声叫好,不少人甚至认为它肯定会赢得一项文学大奖”。或许这是因为这部作品触及了“合作分子”这一敏感话题,引起了争议,所以无缘法国文学奖。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这部小说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评选“2002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小说在国外获奖!”,杜甘在来京领奖时说道。 “在领奖后致的答词中,他动情地感谢中方授予他的这个奖项,使他能够在将近40年后实现他舅舅的遗愿,完成这次他们都极为向往的旅行”。
一位苏联作家曾说: “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的血腥和暴烈的确为柔弱的女性所不堪,但这就意味着战争完全是男人的事,与女性毫无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过。 “一次次的战争夺去了多少女性的生命?毁灭了多少女性的家庭?又有多少女性因为战争被迫拿起武器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女性从来没有摆脱过战争阴影的笼罩”。杜甘的小说《军官病房》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中,有着不少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为之动容。本文试图以杜甘这两部小说为蓝本,紧扣战争与女性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阐释战争对女性命运的影响,凸显反战这一主题。
(一)战争对女性命运的影响
战争是人类的灾难。古往今来,人类为了抢夺领土和自然资源等爆发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战争。这其中有正义的战争,也有非正义的战争,但不管是哪种,这些战争都使无数战士战死沙场,无数难民流离失所,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使人类遭受巨大损失和破坏。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了巨大的摧残,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
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历来被视为柔弱的象征,是被保护的对象。可战争却不会因此而格外眷顾她们,使她们免遭伤害和苦难。相反,无数女性以各种形式被迫卷入了战争当中,所受伤害相比男性更为严重。 “战争迫使男子上了前线,使妇女不得不忍受难以言说的相思煎熬的痛苦;战争不可避免地夺去了许多男子的生命,使妇女不得不经受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战争的不断继续、战场所需物资的不断增加,使妇女不得不承受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加上叛军的烧杀掳虐,使妇女身心遭受更大的摧残”。在杜甘的《军官病房》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这两部小说中,有不少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的是作为志愿者在后方担任护士抢救伤员,有的是参与抵抗运动中的情报工作。战争对她们的命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军官病房》这部小说中,美丽的女护士玛格丽特虽然是一个富有的金银器商人的女儿,她却主动要求作为当时紧缺的护士去前线的急救医疗队,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可就在她去医疗队的第四天,一颗德国炮弹落在帮伤员止血的玛格丽特的帐篷里,她被毁容了,耳朵也失聪了。从此,她的一生因为毁容而定格,决定了她在以后的人生当中的种种艰难。相比在战争中其他缺胳臂少腿的伤员,面部损伤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要大得多。断了四肢还可以装上义肢,穿上了衣服也不会把伤口赤裸裸地暴露在外。可是如果是面部毁容,该怎样示人?玛格丽特不仅要经受身体上的痛楚,还要备受世人冷漠的眼光,在社会生活中受挫,经受精神的折磨。她出院之后回到家中,女仆竟然不认识她,而正在参加晚会的父母和两个哥哥也没有流露出丝毫温情。直到最后她的几个男性同伴都成功地结了婚,她却仍然是个例外,“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一个被毁容的女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物”。就这样,她终身都未能享受到爱情和婚姻,把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他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伤害更加痛苦的吗?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中的米拉是一个西班牙犹太女人,是主人公加尔米埃的上级。作为情报人员,接头碰面、四处搜集消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得胆大心细,而且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要冷静果敢。米拉每次与加尔米尔接头时,都是那么冷漠,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不被人看出任何蛛丝马迹。可是后来她还是被抓捕了。她始终没有屈服,接着被流放,“他们在精神上要遭受甚于死亡的折磨、屈辱,否定自己的存在。纳粹分子将向人类表明,他们能够做出比使人们死亡更恐怖的事情,这就是他们所能留下的一切”。她在集中营所受的苦难必然是骇人听闻,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后她来到了以色列。最后,深爱她的加尔米尔在她定居的地方——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找到了她,而这时的她微笑着,热情、亲切,跟之前冷漠、高傲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米拉在加尔米埃的陪伴中于1964年3月去世,她就这样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人类永恒的事业——和平。
克洛狄娜是加尔米埃刚开始参加地下工作不久留宿过、掩护过他的战友,后来成为了他有名无实的妻子。加尔米埃并不喜欢她,只是因为觉得孤独才与她结合。战争结束以后,克洛狄娜仗着加尔米埃父母的善意在他家里住下,最后如愿和他结婚。可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我们很少说话,我们的共同生活的滋味就像煮过的生菜,我们结婚就像别人拿到了一张党证,以便确认一种立场”。这种无爱的婚姻就像一把枷锁把他们生硬地绑在一起,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但这又何尝不是克洛狄娜命运的悲剧?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中有一个刚满19岁的妓女叫阿特加,她的父亲从战争开始就被俘虏到德国,母亲抛下她跟人私奔了,留下她独自面对命运的无情摆弄。她善良单纯,毫不知情地成为了卧底,卷入了这场纷争。直到最后被捕,她也是 “目瞪口呆地跟在后面”。这样一个花季少女,本该在父母亲的庇佑下,幸福快乐、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可就是因为战争她不得不为了生活沦为妓女,陷入多么危险的境地而毫不自知。她的悲惨命运正是对残酷战争的无声控诉。
战争这个怪物给这些女性带来的苦难绝不比男性少,相反,她们的悲惨命运更是凸显了战争残忍的本质,发人深省。“对于那些仍然相信战争是一种偶然事件的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他们意识到一切冲突都只是人类新的失败,任何理由都不足以使人相互屠杀”。杜甘向我们展示了无情的战争对女性命运造成的巨大影响,从侧面凸显了反战这一主题,触动人心,引起了读者的共鸣。
(二)女性形象的塑造
杜甘的两部小说视角独特,题材新颖。他选择了细微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在战争这样的大背景下都显得平凡而微不足道,但是我们细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一些非类型化的人物。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形象更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军官病房》中美丽的女护士玛格丽特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女性。她有着美丽的长发,苗条的身材,蓝色的眼睛,甜美柔和的声音,热情的微笑。但这样一位美人儿却被毁了容,鼻子和颧骨被炸弹击中,姣好的面容当中有一个窟窿,耳朵也失聪了。她呆在巴黎荣誉军人医院这座白色监狱里,接受着魔鬼般的器械的折磨。这里的病人们面对着病友吓人的伤口,就像看到自己厄运的镜子,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这所医院里,有一个名叫路易·勒沃舍勒的毁容者,在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探望他之后,不能承受亲人们看到他被毁面容之后的反应而自杀。确实对于毁容者来说,面对生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坚强的内心,一个这样的大男人尚且不能做到,更何况是一位女性!可是玛格丽特却做到了,她没有选择自杀,而是毫不躲避,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当佩纳斯特出现在她的面前邀请她加入军官俱乐部时,“她的全部回答就是给了我们一个热情的微笑,一张像她的眼睛和前额一样未受损伤的嘴巴的纯洁的微笑”。但在获准休长假回家之后,等待玛格丽特的却是正在参加晚会的父母和哥哥们的惊慌失措和冷漠无情。都说家是温馨的港湾,即便受到再大的伤害,只要回家就能得到慰藉。像玛格丽特这种境地更是需要家人的关心和鼓励,可是她没有看到这些,相反还受到嫌弃。最后她毅然离开了家。作为一个女性毁容者,独自面对着自身的痛苦、他人的眼光、亲友的抛弃却依然顽强地生活下去,她的勇气和坚强令人折服。
更令人敬佩的是,在经过了这些苦难之后,她依然在儿童医院工作。后来除了在部里上班之外,还在一家精神病患者卫生院里工作。她终身未婚,把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他人。她的舍小我为大家的奉献精神让我们为之感动。此外,她与住院期间结识的三位病友之间建立了同甘苦、共患难的珍贵友谊。在医院那段难熬的日子里,他们相互扶持、鼓励。一直到最后出院,他们都是最亲密的朋友。玛格丽特虽然失去了亲情,也没有享受到爱情,但她收获了珍贵的友情,她的大爱精神赢得了他人对她的敬重,她的形象熠熠生辉。
《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中的女上级米拉有着茶色的皮肤,优雅、苗条、柔软,却一直对疯狂爱上她的加尔米埃保持着距离,故作冷漠和傲慢。或许这样一种冷峻的态度、有原则、有分寸的工作作风正是她的魅力所在,深深地吸引着加尔米埃陷入爱河不能自拔。米拉被捕之后,在三天的期限里,她并没有在严刑拷问下出卖加尔米埃,供出联络网。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她为了保护同伴和组织,以自己的柔弱之躯独自冒着生命危险,没有吐露半点消息,使得加尔米埃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最危险的几天。在这样危险、特殊的环境里,他们之间这种默契、信任岂是一般的情感所能承受的?
战争结束之后,加尔米埃对米拉日思夜想,千方百计地找到她之后,米拉与战时的态度截然相反——亲切、热情,带着开朗的微笑,努力打消加尔米尔的腼腆。像与多年的老朋友重逢一般,她说起了她的经历,却对被捕、被流放的日子避而不谈,这是她人生中灰暗的日子,足可见她当时受了多少苦难和折磨,她不想让加尔米埃难过。米拉还谈到了她毕业之后照顾精神病人、领导基金会、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等经历,这是一位有思想、有胆识、有信念的女性,她在战争中勇敢地站起来,主动地承担责任,为人类的幸福而贡献自己的力量。难怪加尔米尔说: “我很快明白了我永远有那么多理由爱她”。
在杜甘的这两部小说中,除了玛格丽特和米拉这两位主要的女性形象之外,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同样让我们为之动容。《军官病房》的克雷芒丝在战前送别她的情人后,显得迷人而忧伤,却与主人公阿德里安·富尔尼埃发生了关系,成为阿德里安魂牵梦萦的情人、煎熬岁月中的精神支柱。之后她拒绝了阿德里安却又抱怨他的沉默。给人以飘忽不定、茫然无知的感觉,这与战争时期人们心灵受到创伤,对未来感到迷茫、困惑是分不开的。战友雷米的母亲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美女”,目光坚定,也是一名抵抗运动成员,最后被抓到集中营里再也没有回来。作为一名老妇,她本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继续生活,不问世事。可她没有,她毅然地加入反抗的行列,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相比以前的反战小说,《军官病房》和《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两部小说中出现了更多个性鲜明、形象丰满的女性。杜甘把残酷无情的战争与女性的柔弱却又坚强的形象放在一起形成强烈的视觉效应,更能凸显反战的主题和赞美这些伟大光辉的女性。
老舍曾说,作家描写战争“不是为提倡战争,颂扬战争,而是为从战争中挖掘出真理,以消灭战争”,老舍先生这句话道出了作者写作战争小说的意义,这也是作家应有的一种博大情怀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杜甘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以这两部出色的小说从不同角度给我们展现了一战和二战的冰山一角,警醒着世人要防患于未然,远离万恶的战争,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