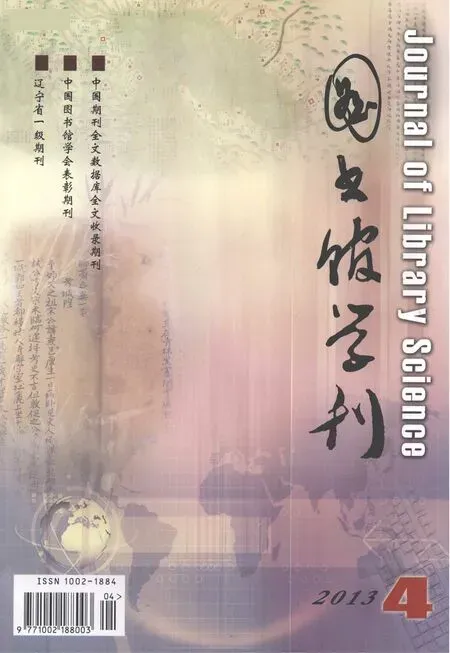我心中的图书馆
程显好
写下这个题目,心头忽一阵潮涌。图书馆对我一生影响巨大,绝非一篇2000字的短文所能承载。下面的零星回忆,记录着我和图书馆的多年渊源。
“掉根针都能听见”
第一次去图书馆是1959年,这年我13岁,读初一。当时,我哥在中国医大读书,暑假回鞍山,答应带我到新建的市图书馆看看。4站地的距离,哥要走着去,我正兴致勃勃,自然不敢反对。连跑带颠跟了足足半小时,终于来到胜利广场旁一座带院墙的4层灰楼,楼外铜牌上写着“鞍山市图书馆”。哥带我来到一楼阅览室,预先警告:“别说话,走路轻点!”阅览室好大,竖排几趟桌子,准能坐100人!那天是星期日,人很满。这么多人看书、看报,里面却十分安静。我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脑袋里忽然闪出不知在哪见过的一句话:“掉地一根针都能听见。”
回家路上,把这感觉描述给哥,他对我大加表扬,说我说得好,弄得我到现在都不忘。我还记得,那天我哥从一排架子上拿起的是一摞《内蒙古日报》,我当即想到姐姐从鞍钢调到内蒙“支援包钢”的事。我自己看了什么早已忘记,却始终忘不掉阅览室里那特有的安静带给我的初次震撼。
吴晗和鲁迅
1961年,我考进鞍山卫校药剂班。学校很宽松,入学就给办借书证。当时教我们政治的老师叫杨斯廷,山东人,高度近视。据说在陶铸手下做过随军记者,课堂上讲过“执两用中”、“君子慎独”,让我们佩服得一塌糊涂。忘了为什么,有天杨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和我谈起吴晗来,特别提到他的《投枪集》。第二天,我就去图书馆借出了这本暗红封面的“政论集”,通篇读过,脑袋里便常常出现“民盟”、“清华”、“胡适”这些字样。接着,我又陆续借来《灯下集》、《春天集》,一时俨然成了“吴晗专家”。
第二年,学校图书馆搬家,我们班被指派搬运图书。那天,我意外地看到一排《鲁迅全集》!有了读吴晗的底气,我忽生读鲁迅的冲动。问明“可以借”,我随即借了本《鲁迅全集》第三卷(图书管理员建议我先读此卷)。为了读“鲁迅”,我特地把家里的《新华字典》拿到学校,坚持一年,终于把十卷本的这套全集一字不落地读完。我说“坚持”,是因为读得很刻苦,一不能误了功课,二有许多文章看不懂,比如先生早年在日本写的3篇“古文”,我就是捧着字典一句句啃下来的,以致那阵子我自己也放胆写了好几篇“之乎者也”孤芳自赏;说“一字不落”,是指连篇后的注释我都全部看过。“18岁前读完了《鲁迅全集》”一直让我引以自豪,并成为我后来教育孩子的“法宝”之一。至于再后的认识萧军女儿萧玉、结识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北大教授钱理群,说来也都缘起于半个世纪前的这段读书经历。
妻子和“图书管理员”
1964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北镇县沟帮子地区医院工作。医院附近有个文化馆,馆内图书室每晚都开放。文革前,我在那里读了许多让我终生受用的好书。也是在那里,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
1970年,文化馆新来一位图书管理员。听说是“抚顺青年”,先就有了几分亲切,借书时,见她字写得很漂亮,又增几分好感;渐熟之后,我俩常会隔着桌子闲聊几句,但也仅止于此。
第二年,突然听说她被调到北镇县图书馆,我一下子涌上一股莫名的失落。几天后,止不住给她写了封信,表明心迹。此信成为我俩近百封“两地书”的开端。两年之后,我也调到北镇县医院,又成为县图书馆的“常客”。再后来,我俩结婚。婚后她又读了4年辽大图书馆学的函授,当了馆长……
娶了图书馆的老婆,看书自然更加方便,古今中外的书确也读了不少,而“图书馆”三字在我心里也有了非同寻常的含义。多年来,老婆不止一次问我:“当初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回答从来不变:“都喜欢!”不过,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推测,在我们的婚恋中,妻子的职业虽无“决定性”分量,但在我“潜意识”中肯定发挥过“锦上添花”的作用。如今妻子已成老伴,这番“分析”顶多挨两句骂,无所谓啦!
北海边的“北图”
1983年,我到北京进修,住在阜成路6号海军总医院。开始半年,我每周都去美术馆看展览,坐车经过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时,总要看一眼门前那对石狮子。有次夏天路过,见那里站着一堆人,大红门的铜钉上挂着许多书包,心生好奇,便下车走了过去。一问,原来是临近高考的学生,早早过